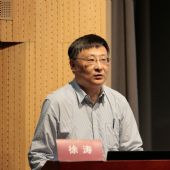按:2018年5月11日,金维诺先生家属鲁立稼先生找到人文学院图书馆副馆长王瑀,表示要将金先生现存的藏书和部分学术资料无偿捐赠给人文学院。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学院领导的重视,在原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教授的领导下,人文学院图书馆迅速成立整理小组,先后四次前往金先生家中开展整理工作,小组按线装书、平装书和期刊杂志等分列甲、乙、丙三等先后整理了图书三百余箱「1」。
2019年5月9日,金维诺先生捐赠文献整理成果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向公众开放,位于美院14号楼二层的人文学院图书馆,几米见方的专题展厅,陈列着金先生捐赠的部分旧藏图书和学术资料。尹吉男教授评价,这批捐赠见证了金先生生前学习、思考和著述的全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遗产「2」。
1953年,曾在中南工人日报社和中南工人出版社担任编辑的金维诺先生,被调往中央美术学院从事理论研究。这是金维诺先生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开始,同时也昭示着,不久,一位开拓创新的美术史教育家、美术史家、美术史学科主要创建人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
作为美术史教育家,金维诺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的主要创建人,是一位不负历史重任的开拓者。
“我认为自己能做个摆渡人、做块后来人的垫脚石就不错,通过我的工作,其它人能够继续向前走,我就尽到责任了,我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3」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界开始重视专业理论建设。中央美术学院在徐悲鸿和教务长吴作人的主持下建立研究部,后学院又建立了民族美术研究所和外国美术史研究室。在王朝闻、王曼硕的主持下,王逊先生开设中国美术史教师进修班;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许幸之组织青年教师担任外国美术史的备课和教学,并接受整理留法学者的大批珍藏图片。期间,一方面,中央美术学院在文化部的领导下参与并组织了美术史考察团,对麦积山、炳灵寺、敦煌莫高窟、永乐宫等历史遗迹进行了考察并收集资料;另一方面,外国学者来访交流美术史专业建设与教学的经验,等等。「4」这些理论工作的推进为美术史系的建立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1956年,在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先生的支持下,金维诺先生与王逊、许幸之、王琦等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草拟建系规划和教学方案,报送高等教育部和文化部,准备招生,招生计划人数15名,主要任务为培养美术史教学与研究人员,美术报刊编辑及博物馆工作人员等。「5」1957年,在王逊先生的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理论教研室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基础上调配师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美术史系。
1957年,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右”运动发起。美术史系9月开学,但这时候江丰、王逊「6」等多位美院老师被打成“右派”。老师和学生仅上一学期的课,美术史论就被迫停办,学生也不得不转系更校。「7」。金先生转而负责《美术研究》和院刊。
这场运动结束后,1960年,国家对各项工作提出“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美术史系恢复招生。这一时期,金维诺先生出任美术史系副主任,开始负责系里的实际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美术史的教学研究力量得到充实,人员配备齐全。此外,美术史系还规划出由中国美术史教研组、外国美术史教研组和理论教研组和资料室组成的三组一室的建制。美术史系一方面准备教材,一方面培养学生,60年代,美术史系先后培养了三批本科生与一期进修生。「8」“在这个中国跟国外没有形成一个非常通畅交流的情境下,如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美术史学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由于王逊先生打成右派以后不能过多地参与到学科的建设筹划当中去,这个重担更多的落在了金维诺先生的身上。”罗世平认为:“王逊先生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做出奠基之功,金先生在学科上的贡献最贴切则是‘开拓’。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美术史学科在那个年代建构起一个学科的面貌,他是不负历史重任的开拓者。”「9」
1976年,“文革”中被停滞的美术史系恢复招生,美术史系恢复三组一室的建制,并兼管《美术研究》与《世界美术》两刊。金维诺先生被任命为美术史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美术史系开始进入到恢复发展时期。
(二)
作为美术史家,金维诺先生是第一位从美术史角度讨论敦煌艺术的中国美术史学者。
“金维诺教授的每一次学术转向,不论是有关联的还是跳跃性的,也不论是主动选择还是邀请的,他都能认真对待,潜心研究,成果丰硕,并能惠赐于人。他就像一位不倦的拓荒者,在荆莽中开出大道,在荒原上建起楼台。”「10」
紧接在金维诺先生捐赠文献整理成果展开幕后一日,“传铎:纪念金维诺先生美术教育与学术成就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拉开帷幕。研讨会上,金维诺先生早期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罗世平教授、熊文彬教授、张鹏教授、邵军教授、贺西林教授分别介绍了金先生在汉传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绘画史与鉴定、书画史籍以及美术考古五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敦煌石窟艺术是金先生最早涉及的研究领域。”1955年8月,刚调任民族美术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不久的金维诺先生,随同研究所的西北考察团赴敦煌作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考察。期间,他系统收集和整理洞窟资料,后陆续发表《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佛本生图的内容与形式》《祇园记图考》《祇园记与变文》《敦煌晚期的维摩变》等数篇论文,引起敦煌学界关注。罗世平「11」教授在研讨会中谈,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到1930年陈寅恪提出敦煌学这个概念,直到建国初年这半个世纪中,敦煌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敦煌文书的研究上。尽管1944年敦煌成立了艺术研究院,但对敦煌石窟壁画、雕塑作为艺术史的研究未能跟得上国际敦煌学的进展。金先生1955年11月发表的《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一文,是中国美术史学者讨论敦煌艺术的第一篇美术史文献。「12」
从敦煌出发,金维诺先生又将研究视野放到西北和西南地区,藏传美术的调查研究也随之向外扩展。熊文彬教授回忆,1992年67岁高龄的金先生亲自到西藏对吐蕃最重要的美术遗存进行调查。而由金先生主编的图书《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卷》《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全六册),及《西藏早期的佛教艺术》《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等文章,今天仍是研究藏传佛教美术最重要的参考之一。熊文彬教授认为,金先生在充分利用汉藏文献基础上,运用艺术学、藏学、史学、考古学、图像学等交叉学科和理论的方法,对重要遗存年代、体裁、方法进行分析,同时对西藏本土与内地艺术交流和互动进行深入研讨,首次刻画了藏传美术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特点。
“50年代金先生在琉璃厂淘书并对古籍进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一些珍贵的稀有文献他还会动手抄录。”邵军教授曾有幸目睹金先生的手抄《成都志》和《蜀名画记》。70年代后期,金先生根据收集整理的这些材料,发表了《中国早期的绘画史籍》《宋元续编的绘画通史》等一系列文章。「13」他的研究涉及《画品》《历代名画记》《述画》《画断》《书断》《唐朝名画录》,以及北宋史籍《益州名画录》《圣朝名画评》和《图画见闻志》,后来又做了《画续》《续画继》以及《宣和画谱》等诸多研究。此外,金先生还展开了部分寺院艺术的史籍研究,以及对《十百斋书画录》和《清湘大涤子画法秘谈》两个手抄本展开了文献研究。邵军教授认为,金先生的研究并不是纯粹的史学或者是史料学研究,他在文献研究中看到的是古代绘画中的诸多关系问题。
60年代初,金维诺先生兴趣扩展至中国绘画史和鉴定研究领域。这期间他撰写了《<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张择端及其作品的时代》《<古帝王图>的时代与作者》等论文,对唐宋绘画的作者、流传及真伪等问题作出辨析。他对绘画史发展做出的系统性综合阐释,推动了传统书画鉴定的现代发展。张鹏教授发言时介绍,金先生在主持美术史系教学时十分重视书画鉴定。60年代金先生为美术史系开设了书画鉴定课;80年代他不仅请徐邦达等专家开设书画鉴定课程,还与杨仁凯先生合作培养研究生;90年代金先生提出要进一步拓展美术史系的人才培养方向,曾与薛永年一同努力发展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书画鉴定学科。
70年代中后期,全国多地涌现出重要的考古发现,金先生密切关注这些考古新动态,发表了关于新石器时代彩陶、马王堆汉墓帛画、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齐娄叡墓壁画、新疆吐鲁番唐墓遗存等重要考古材料的数篇研究文章。贺西林教授介绍,金维诺先生非常重视考古材料,注重考古材料与传世作品和文献的结合,《曹家样与杨子华风格》一文,是他用这一方法来研究美术史的重要代表作。在具体研究中,他既重视注重宏观把握,也注重局部探微,在面对考古材料时,他不孤立地看待这些材料,而是把它们放在美术史的大格局中综合审视。如,他以《北齐校书图》、娄睿墓壁画、《历代名画记杨子华传》相互比较印证,认为娄睿墓壁画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杨子华的风格,而杨子华的风格又代表了北齐绘画的时代风格;讨论唐代绘画时,他不仅使用文献和传世画作,还注意联系石窟墓室壁画以及建筑和碑刻装饰。
(三)
美术史系成立62年,看中国美术史和美术史教育的发展。
“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像一棵屹立在大地上的树,向着空中生长,但每一个人的头顶上,还有一棵从空中倒长的树——它是人的精神之树,扎根在观念的天空,它的枝叶向着地上迎风招展,引领者大地之上的我们。”「14」
中国最早的美术史写作要追溯至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全书十卷,一至三卷为专论,四至十卷为史论。书中辑录上古至唐画家三百七十余人姓名、事迹。余绍宋评,“是编为画史之祖”。但这种将偏重史料记载的书写方式停留在传统的美术史研究中,滕固认为,该书“当为贵重的史料是可以的,当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则是不可以的。”
19世纪,美术史最早在德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此时的中国大地还深陷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以及西方列强不断地割据蚕食的泥沼之中。直到20世纪,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精神高涨,新型的现代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旧有的治史模式产生冲击。中国学术开始向现代化转型。梁启超是这一时期史学模式转变的代表人物,他举起“新史学”大旗,先后写下《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这时,美术史正式列入中国政府的学科科目,发布在1912年教育部文件《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随后,美术史课程在美术院校相继开设,但一方面由于师资和教材的缺乏,美术史教学并未如期在诸学校开设,另一方面开设了美术史课程的学校,其教学任务也主要是由艺术家代为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些美术史图书开始陆续出版,如姜丹书《美术史》(1918年)、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25年)、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年)等。这些书籍的出版为当时的美术史教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主要由课程讲稿汇编而成,且有的书籍大量引用画论作为写作史料,写作方式仍未停留在传统美术史写作。「15」这一局面直到滕固留日归国,出版其流传后世的《中国美术小史》才被打破。受梁式启发,留日归国的滕固,用新的美术史观和文化思想于1926年写就该书。书中打破偏重史料记载和只重书画的传统艺术史写作模式,以更为全面的视角对包括书画、雕塑、壁画等在内艺术形式做出论述。滕固也因此被后世认定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史学的奠基者”。
彼时西方,自1833年朗朗茨•库格勒被柏林大学正式命名为艺术史教授,1913年德国哥根廷设立艺术史全职教授席位,此后德语国家先后出现艺术史的专职教席。1947年,清华大学陈梦家、邓以蛰、梁思成等人深感欧美大学开设有“中国艺术”课程,“反观国内大学,尚无一专系担任此重要工作者。清华同人……深感我校对此有创立风气之责,因此提请清华大学设立艺术史系”。1948年9月,清华大学呈请教育部增设艺术系并附具体建系计划。教育部同意该申请,要求“将学系名称改为美术学系,余照准”。「16」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十年后,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最终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成。「17」
随着时代发展,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一个由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进化之眼光、四十年代的唯物史观,过渡到八十年代的审美关系论、辨证论、接受美学论,以及后工业时代的新艺术史学、视觉文化理论等多元并存的美术史观。与之同时,国内的艺术史学科建设日益完备,80年代,浙江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相继成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新世纪以来,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开始涵盖全部的视觉对象,美术史系也开始在综合性大学开设。今天,在老一辈美术史家、美术史教育家的指引下,中国美术史和美术史教育的发展正迈向一段新的历史。
结束语
罗世平教授为金维诺先生的整场研讨会做总结时指出,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和美术史学科和研究和发展过程,做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活动,是以金维诺先生作为一个表率和话题,为我们呈现出来一个学术的面貌。在美术史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每一位美术史从业者做出的贡献,无不是以自己为“木铎”,金声玉振,必将传之久远而后已,这也正是薛永年先生为研讨会题词“传铎”之意。
文/杨钟慧
现场图/胡思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整理工作未完待续。
「2」引自尹吉男教授为金维诺先生捐赠文献整理成果展所撰前言。
「3」引自媒体刊载的金维诺先生访谈。
「4」薛永年、王宏建主编,《筚路蓝缕四十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论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页。
「5」相一,“中央美术学院筹建美术史系”,载《美术研究》1957年2期。
「6」“反右”运动中,王逊先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7」据范梦回忆:范曾,李西源二人转到国画系,周建夫、范梦祥二人转到版画系,张海峰转到油画系:转本校的共五人,转到外校的是七位:闫以平(女)转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史国明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吉宝航(女)转北大西语系,张中政转北大中文系,朱懋铎转北大历史系。刘瑜、夏振球记不清楚了。另两位年龄偏大的同学李松涛、奚传绩自愿放弃高等学历攻关,在本校当了行政人员。——范梦“《记忆一个特殊的班级——中央美术学院1957级美术史系第一班》”,载中央美术学院《校友通讯录》2013年12月。文中范梦提及如果他没有记错这个特殊班级共14人,但在1957年《美术研究》的刊文“中央美术学院筹建美术史系”中,美术史系计划招收第一批新生15人。另外一人是否实际被招收,待考。感谢校友会妙子提供范梦文章供笔者阅读。
「8」薛永年,“奠定、发展、开拓——美术史系三十年”,载《美术研究》1988年第3期。
「9」引自2019年5月10日,罗世平先生在“传铎:纪念金维诺先生美术教育与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发言。
「10」罗世平,“鉴古开今、永远进取——金维诺教授的学术人生”,载《美术研究》2018年第4期。
「11」罗世平是金维诺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12」引自罗世平先生在金维诺先生的研讨会发言,该论述同样见于罗世平,“鉴古开今 永远进取——金维诺教授的学术人生”,载《美术》2018年第4期。
「13」邵军教授介绍,金先生最初准备完成一部名为《中国绘画史籍概论》的专著,可惜这批文章未结集出版。
「14」研讨会上,李军教授援引中世纪的说法,认为尽管金维诺先生、汤池先生、薄松年先生相继离去,但以金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美术史家、美术史教育家,已经成为这样的精神之树,他们在空中向我们招展,成为我们仰望星空时的一个坐标。
「15」参考蒋英,《困境与出路——中国美术史课程研究》,2008年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16」转引自王逊著,《王逊<中国美术史>》,辽宁美术出版社,第15页,前言。
「17」薛永年曾在第十一届中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上回忆起高居翰先生的提问:世界上的美术史系普遍设在综合大学,为什么你们中国偏偏设在美术学院?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能离开画家而独立呢?对此,他专门访问了金维诺先生和其他老教师,了解到当时有两种考虑,其一是以江丰为代表,主张设在美院,其二是以北大的翦伯赞为代表,主张设在北大。薛永年认为这一结果说明决策者优先考虑的是美术史专业与培养美术人才的关系,与美术创作迫切期待理论指导的现实需要有关。这也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传统离不开,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和绘画史,绝大部分是为美术院校开设课程而写的通史,目的是为了在宏观叙事中阐述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探索中国美术前进的方向。参阅澎湃报道“邵大箴与薛永年:重新回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传统与思考”,2017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