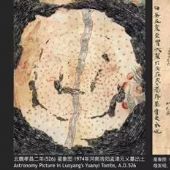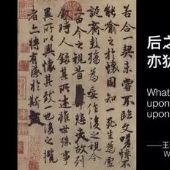演讲全程视频(或点击首页“视频”栏目观看):
「未•未来」演讲实录丨范迪安:全球艺术设计教育共同体
各位专家和朋友:把我的演讲安排在布鲁斯·茅和凯文·凯利先生两位嘉宾之后,对我来说既是荣幸,又是挑战。他们从社会学、文化学和设计学的角度,用大量的关键词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信息世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听众朋友都会感到我们就处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网络之中,难以逃离,当然唯一的做法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听完他们的演讲,我想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人孔子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关于学习,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在掌握知识之后去实践是愉快的事,也可以说,进行交流讨论的时候要努力言说,这两天演讲就是各位专家畅所欲言的一个场合。当然孔夫子还有第二句话,那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能够有这么多朋友前来中央美术学院参与如此盛大的圆桌讨论,的确让人感到无比的高兴与欣喜,因为这种头脑风暴和思想交汇毫无疑问会使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也就是从2017年的秋天开始。
孔夫子在说到知识和学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知识的交汇有时候没有距离,古代的“有朋自远方来”是真的“远”,而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远”严格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地理距离的概念,在座的专家来自世界各国,有的即使没有到现场也同样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智慧,因此“远”在今天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还有一种“远”值得我们讨论,那就是我们所经过的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这个时间的“远”有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因为正是这种时间的“远”才使得今天进入了加速度的时代。很显然,在今天简短的演讲中,我不能像前面各位专家那样给大家带来许多非常现代的信息,我想从中国文化的遥远开始谈一点我的体会。
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习近平主席前一段在北京故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结晶在今天都视为艺术品,在艺术作品的遗存中充满了中国人科学和艺术这两方面的智慧。早在公元前七千年就有了称之为绘画和雕塑的萌芽,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已经有了可以作为交往信息的文字,当然中国的青铜时代和西方的青铜时代都是人类儿童时代重要的产物,但是中国青铜时代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铸造技术、冶金技术的密码,很显然整整影响到了到工业革命为止一个漫长的时间。此外在两千年前的秦汉帝国和古罗马帝国时代,东方和西方已经不仅双峰壁立,遥遥相望,而且几乎差不多要实现真正的接触。当然,丝绸之路正式开启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商贸的交流,也是最早“走”出来的信息之路,不像今天是通过无线网络予以实现。东方的丝绸、瓷器、印刷术等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同样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来了西方的金属工艺、玻璃工艺,以及许多科技的发明,因此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往就构成了人类信息交流的一条雄厚的道路。在这样一个非常快速的阅览中,我们看到信息时代的到来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和长远的积累。
这次圆桌对话的主题是“未·未来”,是对未来的未知性、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做更多理性的讨论,这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种文化责任。我先从中国传统中的“未来观”讲起,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贤哲似乎就预见了今天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先人那么早就会说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这样的词,今天就称之为网络时代,而且这个网是在天空之中,在“空”里的有形之物而不可视之。
在中国古代智慧中有许多关于天的描述,在中国和东方许多国家的观念里,只有两个世界,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使得中国古代先人总是不断地投向深远的目光去认识天的世界,同时也努力认识人自身的世界,进而在天和人的两个世界中去寻找沟通与联系。我这里简要地把中国人关于天和人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描述分解成三个层次:
一、天圆地方
这是人站在一个共性的角度对天的认识。很早很早以前,中国就有关于天的畅想,有着最早关于宇宙星空方面的描述,尤其是用可视的图像记载下来。在古代的星空、星际图上,描绘了天圆地方的认知。实际上地球是圆的,这是人们后来才认识到的,但是更早的时候人们认为地是方的,天是圆的。为什么?因为地的方同时也代表着时间,因为只有在一个矩形空间里面才能了解自己所处的方位。从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零年这个时段里,中国的建筑布局、建筑造型和许多绘画作品都表达了天圆地方的景象,在关于天的描绘中,也描绘了太阳和月亮并存的景象以及它们的诞生,这些看上去是神话传说,但都是用形象的方式记录下来的。现在我们不能把这些简单看成是的神话传说,或许是人们曾经经历过的许多事物而形成的描绘。
比如在一座汉代的墓室里可以看到完整的天象图,它画在圆形的穹窿顶部,在用平面的方式复制下来之后,可以看到它表现的是一幅完整的星宿,这既是观天测象的一种科学的结果,其实更是中国人关于不可知事物的一种探究。这种探究也包括记录时间,只有当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完全叠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有了着落,这就是“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在 这样天圆地方的求索过程,实际上是古人的“未来观”。他们不满足于对现在时间的一个思考,而更多的是要思考更大的、更宽阔的空间和更遥远的事物。只有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开拓之后,从西方传来的有关地球和天空的学说才逐渐成为重要的替代。因为这些学说更加接近我们所处的实际,于是有了圆形的地球认知。但是在这样的时期,还仍然包含着中国人对天和地其他方式的探索,比如说地理学家都是走遍天下描写山川河流,画家也通过“行千里路”描绘广阔的自然山水,中国地理图志和山水画在对大自然认识上有一种共性的观念,这些表现山川河流的艺术看上去跟今天谈的设计并没有关系,但是其中所寄注的观念或者是很多对自然物象的观察与描写方式对后来的中国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比如中国人很早认为人这个“种类”并不仅仅是人自身的模样,他可以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合体,甚至是人与各种自然之物结合的产物,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甚至是对未来的想象。
二、天人感应
这是非常典型的东方意识。人和天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一定要形成某种通感,二者才具有生命力。在古代,人对自身的认识是有限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多的。人始终相信只有在与自然形成一种感应的时候,人才可以控制自然,或者反之人会被自然所控制。西方讲的是神与人的关系,中国讲的是天与人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认知系统。在天与人的“天”中,包括了自然万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或一组神。可以说,中国的“天”是人之外的全部。在我们今天面临着人工智能的世界的时候,可能要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样的道理,如何实现天和人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很多绘画里也表现出来,例如著名的马王堆帛画表现了天界、表现了人界、也表现了地下,类似这种图式,都试图在一个画面即一个可视的世界里把天和人的关系描述得更加清楚,而且还有对美好的向往,向往到一个更加充满幸福的彼岸世界,同时也要借助大自然的很多物体,例如动物、植物、风、云,当然还有太阳和月亮,还有其 他星系。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和画像砖上都有表现。比如一块画像砖的下方 画的一排人物都是古代的英雄和帝王,他们不仅作为肖像被陈列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未来都是要跟天际、星宇融合在一起。同样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经常也表达了人和物的关联,古代社会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人造物,但是在人的想象中,人可以和很多其他的物种形成关联,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因此在中国的绘画里看到了一种非常丰富的物象、物种结合。
在大量的艺术遗存之中,虽然只是看到古代人智慧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弥足珍贵。艺术创造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很早就已经不仅作为一种观念存在,而且是用艺术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也就成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艺术体系。中国人把绘画活动、宗教活动都放在大自然的山川之中,同时也摆在天空之下,人和大自然中的山川、河流、树木、花果等等都是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来深思的。所以中国人做学问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谓究天人之际是要把所有的工夫不仅摆在人的方面,同时要研究我们面对的对象,正是在天和人这两个交汇地带有着新知识增长的空间。
三、天人合一
这个层次更重要,这是升华的一种文化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前边说到天圆地方,在绘画中是试图用圆规和矩尺测量天地,女娲 和伏羲是创造人类的神,同时也创造天象学;第二个层次是试图找到天人之间的感应,产生一种神力,一种交互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仅在目的性上要形成一致,还要在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上形成一致,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目的性的层面,因为古往今来合目的性导致科技战胜了人文,而且有时候妨碍了人类的和平与和谐。
因此,“天人合一”首先要在“合目的性”的同时“合美学与伦理”,这也就是中国的真、善、美这三个概念的统一成为最高的精神追求的原因,也是现实生活的准则和规范。当然,反映在艺术上就是得到更深层次的体现,比如说天人合一在绘画上的表现是,要表现更多的大自然风貌,而且把人融入到自然之中,同时还形成中国人观察自然的独特方式,而不仅仅是像西方那样的焦点透视。前面有专家讲过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内勒斯基发明了透视法,乔托在绘画中运用了透视法,这都是基于一种定点观察世界的方式,就像打开眼前的窗户看世界一样,而中国人不仅是打开眼前的窗户,更重要的是投身到自然中去,做一种被称之为“游观”的体验。
刚才凯文·凯利先生谈到了体验的价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自然的体验就是最高的体验,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得到了实现的体验。由此由“游观”发展起来的中国绘画的透视法就和西方不一样,画家从时间的流线上可以从春天画到冬天,在一幅画里面可以同时表达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从更加纵向的一个空间进行表达,他既可以画眼前的景物,也可以画云天之上的景物,所谓“山不厌高”,像坐直升飞机一样可以从山脚直线飞到山顶,把这一切都描绘出来。某种程度上,中国画描写的是一个包括了时间概念的一个空间,在这里时间和空间是融为一体的。
这样的绘画观念在世界上非常独特,当然它也就成为很长时间在形制上变化缓慢的一种艺术方式,不过不管怎么样,中国先人早就提醒我们看待未来要像站在未来看今天一样,所以著名的王羲之《兰亭序》里面的这句话就有过提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的意思是,在古代所有的文化创造物上, 其实都包括了对未来的憧憬和预想,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问题是李约瑟提出来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有那么伟大杰出的科技发明和文化的创造,到近代不能率先迈进工业革命,这个“李约瑟之问”的确使我们要整体地反思中国文化的悠长和存在的局限,当然我只能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自身太自足了,它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视域,于是有超稳定的惯性,发展变化的速度很缓慢。但是,中国人又始终是意欲突破局限的,目光是投向未来的。古人讲“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就是要将古今中外、四面八方纳入一个容器里来看待,这也表明先人试图更清澈地看清世界。我们在三星堆发现了巨大的青铜面具,早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就有这样奇异的造型!这样的造型至今无法破译。这个造型意味着什么,它有非常长的耳朵,中国人向来说能够听到很遥远的声音需要这样的“顺风耳”,但是它更有一副从纵向突出来的眼睛,这个眼睛到今天大概能够找到答案,它就是中国古人的“VR眼镜”,当然,这是我在这样的场合下杜撰的。一方面看到古人对未来的畅想,特别是对未来的探索的思想锋芒,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其自身自足的特点使得我们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落后于整个西方科学技术的进程。
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全球时代、信息时代。这两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中国就有很多新闻在发生,都跟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有关,比如上一周中国已经有银行通过脸谱识别开展业务,说明这种新技术很快投入到应用,昨天又有非常重要的消息是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已经有了无人驾驶的公共汽车走向街头,而今天还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更是来了全球互联网的名人,像被称之为互联网之父的罗伯特·卡恩和苹果的CEO提姆·库克,这次互联网大会集中讨论的是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全世界这些大佬都带来很多话题并进行互动讨论,也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但是比较集中的还是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
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理想,我们一方面发展人工智能,而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使这样一种科学和技术的进展造福人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一样,我们在文明共建和文化交往中也有许多可以共同构建的文化共同体、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共同体。这里,我想提出的第一个小的看法是:在这样一个“类人”与“人类”的共生时代里,应该如何更多看重人的主体性。
“类人”与“人类”这两个词在中文中写起来很有意思,西文中没有这样的意味。中国的汉字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它的形象能够产生宽阔的联想。所谓“类人”就是人工智能,上个月被称为索非亚的机器人在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国籍,它拥有了公民权,由此人们开始兴奋地展望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人的前景。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挑战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人工智能第一步是跟人类比拼知识的储存,显然在这一步它赢了。第二步它有巨大的运算,它不仅能够快速的运算而且还有算法,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赢了。第三当然是它能够自我学习,这几乎是人类最为可怕的对手,就是它能不断地自我学习,而不断地成熟;到第四步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是它有感情,它不仅有智商还有情商,甚至还可能加上有艺术商AQ,这样,它就真正站到了人类的前面,和我们抗衡。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这两天这么多专家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将科技更多应用于设计,特别是能够改善生活的设计。我昨天刚从深圳回到北京,此次深圳之行是因为深圳作为中国的设计之都,新开了一家可以说中国第一个以设计为专题的艺术 博物馆,严格来说它叫做博物馆,因为它叫做“设计互联”,所谓互联似乎比一个博物馆的概念更加开放,更加是一个平台。建筑是日本著名建筑师槙文彦设计的,里面的展览展出了来自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设计,也有中国的新材料和新媒体艺术当代展,这样的展览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科技与设计结合的新事物,类似数字艺术、参数的建筑设计、会动的衣服、交互的游戏等,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整个中国设计与国际设计界之间相向平行的趋势。今年秋天以来在央美举办多场研讨会也以科技和艺术的关系为话题,在中国的设计界、艺术界、艺术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我也注意到这几天中国很多大学都在召开科技与艺术主题的讨论会,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新的状况、新的理念、新的设计等等。当然,我不能在这么多设计专家面前谈设计,我也不很了解设计,但有一个问题是我要在这里展开的,就是在科技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技术发展的时候纯的艺术,也就是所谓Fine Arts的艺术该怎么办?
在设计领域,设计保持着一种社会研究、文化批判乃至社会预警的姿态,这是设计师的一种责任,像刚才布鲁斯·茅讲的,设计不应以市场和经济价值为它的归属。对艺术来说也同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像1830年代照相术在欧洲发明一样,当时所有的画家都认为绘画要死亡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观念艺术、多媒体艺术出来之后,又有人惊呼“艺术要死亡了”,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画家更逃离不了“恢恢天网”,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和表现。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有智慧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勇敢地迎向新世纪的到来,另一方面又把新媒体、新方法、新技术、新发现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其实从人类艺术史来看,科技和艺术始终是有关联的,总体来说是人类文明的两个翅膀,但有时候这两个也是会打架的左右手,有时候科技占上风之后压抑了艺术,使得艺术变成仆人,有时候艺术以自己鲜明的人文思想冲破社会的思想束缚,而成为时代的呐喊者和先行者,它又推动了科技,所以科技和艺术两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其实就是今天要解决的“天人合一”的问题。我的同事刘小东毫无疑问是中国最优秀的画家之一,他有非常娴熟的绘画技巧,可是这两年他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和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进行类似于机械自动化的绘画,但是这种机械自动化不是20世纪中期的像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他是借助遥感技术和图像技术而形成的“绘画”,这同样也体现了他的一种社会关怀,比如他把摄像头放在几个城市的主要的十字街口,实时记录城市的动态,由此转为绘画的参数,进而形成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点儿回到中国古代的观念一样,不仅记录了当下的情境,同时记录了时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新绘画。
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家,例如也是我的同事——徐冰。他的展览前天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开幕,展出了他最新的作品,包括一部名为《蜻蜓之眼》的电影,这部电影是从无数的监视镜头里面截取出来的画面构成的,从而编制了一部没有演员的电影。没有演员的电影当然不是自动生成,它也是一种人为控制的结果,这里提示了一个我们在海量的信息中或者是信息的海洋里面如何选择编排和运用信息的观念,他这个片子暂时还没有获得公映权,因为还存在一些诸如著作权或隐私的社会问题。艺术家总是会做一些很先锋的探索,他们以艺术的方式角度介入今天的网络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反思。徐冰先生曾经用大量不可阅读的文字制成了他的《天书》,他也用大量数字时代的各种图形、图画去写小说、写诗歌、写故事,形成了他的一部部“地书”,可见一位富有理想的艺术家都努力把自己的作品跟天与地相连,他的电影大概也可以称之为一部“人书”,因为它是一部更加贴近今天生活的现实。信息时代都有着共同的感觉,信息就像空气和水分一样,但是有时候信息也像垃圾一样,所以如何能够比较理性地对待,就成为考验一个艺术家智慧的标尺。
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位艺术家李枪,他这些年做的一个工作是把许多书和杂志撕掉。我们都知道书和杂志显然是知识的一种象征,里面存在大量的信息,这位艺术家不是痛恨知识,而是他想探究在被称之为知识的载体的“内部”还有什么?所以他努力去深入知识的载体,结果当他把这些杂志无意中撕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了新的“世界”,他撕出了人的形象、树的形象、山的形象、海的形象。我看到他的作品时,一方面很感慨艺术家付出的巨大的努力,一方面在想我们所生产和创造的知识就是这么有趣,它不是一个固定态或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它还等待着人们在触及它的时候,在深入它的时候有新的发现,这也印证了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叫做“格物致知”。当你接触一个事物的时候,当你用新的角度和新的体验碰触它的时候,它能够让你获得新知。李枪这位艺术家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非常原始的,带有手工的活动,这是艺术家最基本、最诚实的劳动,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在知识的海洋深处还有许多可能和动能,这就使我想起超现实主义一位画家马格里特,大家记得马格里特曾经画过一幅画:一个孩子走到海边,把海洋的表面用手掀起来。谁能掀起海洋的表面?只有在艺术家的笔下,海洋的表面是可以掀起的。其实我们在面对信息时代的时候,面对图像时代的时候,也面对许许多多的表面,因此对表面的重新认知或者是试图穿越表面的努力,都可能达到知识新的隐藏之处。
我还想讲一下传统资源的当代转换。今天的信息时代带来全球贯通,人们对全球的信息非常了解,但是如何对自己的艺术传统有所重视并且把自身文化传统中关于宇宙、世界、社会和人本身的观念带入到今天的艺术创造中,就成为一个课题。前天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办了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试图向欧洲公众介绍中国的山水观,用了多重的屏幕展现对山水的远观和近看的不同体验,艺术家试图通过影像的叠印、不同大小的屏幕组成,展现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山水观念。
但是,用数字技术来体现似乎不能完全展现一个画家的主体性,因此许多画家追求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中国传统的“游观”观念,采取沉浸式的创作手法,甚至最后构筑成一种互动性的现场,这些都变成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徐龙森这位中国画家这些年来一直在利用单纯的颜色即中国的墨来进行大幅的水墨创作,他这样做的意图有两个:一个是要把原来摆在案头属于小众空间欣赏的中国画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去,甚至与不同的环境进行对话。几年前我主持了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高等法院的展览,我们策划这个展览是想表达:中国的山水也讲究“法”,但是自然之法,所以中国有“道法自然”之说,西方以现代的法律建设作为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民主,两种“法”之间可以形成对话。这些年来,他的展览办在许多西方重要的博物馆,比如在罗马市立博物馆,他巨幅的山水画和一个古罗马的城市对应;在伦敦大学,他使山水画能够转动起来,让人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到自然的空间里;他也在一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空间里举办展览,比如在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那里珍藏着中国一千年前的最重要的北宋时期的绘画,在那里他用自己新的作品与古代传统进行对话。他的作品尺幅巨大,但可以说这种很宽的画面也是受到今天讲的图像时代的影响,巨宽的银幕和巨型的奇观都是今天我们感知到的图像世界,山水画这样一种传统的方法如何与这样巨大的奇观世界相抗衡,变成出发点或者说动力,这就是新的课题。这些作品,要说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智能如何共生的问题。共生是前提,有了共生才有共享,在一个矛盾的纠结和紧张的张力关系中,不同的文化型态如何真正实现交流和互动,这也是一种共生。
还有艺术家愿意使用更加传统的做法,例如书法家王冬龄,他这些年不是在案头书法,而是在不同的公共空间中书法,因为书法这种艺术的形式,把文字作为艺术是中国相当独特的一种创造。书法表达能够寄注人的情感,尤其是书法的偶发性、即时性、当下性都是其他艺术所相形见绌的。书法在书写过程中的展开,是一种文化特征的表现,使得书法并不在于书写内容本身,而在于书写过程。就像刚才有专家谈到过程的价值。过程的价值不是说仅仅满足于过程本身,而是这个过程中可能生成一些不可料测的实际效果,当然对艺术家来说就是图像的痕迹,图像的影子或者是用哲学话来说叫做图像的踪迹,它是观念、情感,尤其是一种偶发的、爆发的情感的体现,在这个方面王冬龄先生做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把线条变成一种语言,运用线条干涩的、潮湿的、湿润的各种不同的可视的质感进行他的表达。这些活动发生在世界许多重要的博物馆、美术馆,带去的不仅是新的创作,更重要的是用书写充实了欧美博物馆中那部分中国艺术史的陈列。我们知道在大都会、大英博物馆等都有一部分关于东方特别是关于中国作品的陈列,它们记录了中国伟大的古代的传统,但是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如何基于自己传统资源的一种现代性的转换,这是需要让世界更多了解的。一个是设计、一个是艺术,这两个方面都联系着科学与艺术,都联系着今天讨论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艺术家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跟科学家是一样的,一方面宏观探向无穷遥远、无比深渊的宇宙;一方面微观探向许多精微的细节,这样才构成了一个创造性的具有张力的世界。
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一座百年艺术学府,已经积累了我们许多前辈为中国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作品都代表着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水平,中央美院的校训叫做“尽精微、致广大”,提示我们要探究的世界仍然是无边的包括未知的世界,也需要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的精微之处做好。
未·未来的“未”字在中国文字学里很有意思。中国有阐释文字来源的传统,中国文字最重要的价值是“象形”,即通过图像、形象可以猜出这个字的意思。未来的“未”字从甲骨文开始就是这么写的,它像一棵树,它有根系,因此它可以长大。在树木的枝桠上加上不同的枝桠,构成了“未”字,这种写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早在两千年前,人们就为它作了注释:“未,象木,重枝叶。”由此可见,未来虽然有许多难料的未测之处、未知之处,但是它终究像一棵有生命的树木,可以成为树林,还可以成为森林!因此“未”的未知性后面,蕴含着也预示着它未来的生命意义。
图、文/未·未来 官方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