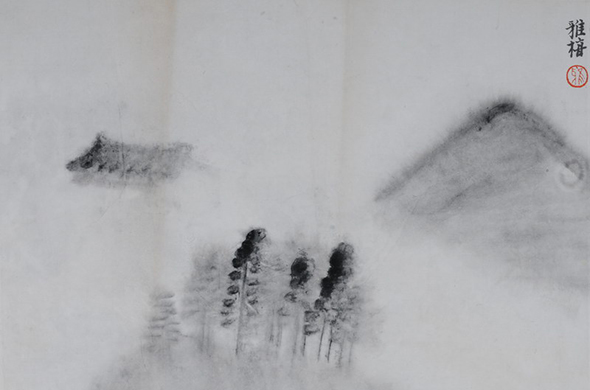
明代方瑞生在《墨海》中论及好墨的标准为:“黝如漆,轻如云,清如水,浑如岚。”具有“香如婕妤之体”,“光如玄妻之发”。这样的好墨哪里有?对于我们这代人似乎只听说过,但还未曾有幸见过。书架上曾有一本古人制墨的书,从旧书摊上买来时只是因为书中的插图,现在看其制墨工艺的繁杂,只有感叹古人做事的严谨和手艺的精良,这样制作出来的好东西,也只能在书中想往片刻而已。今人用墨多已从简,一盒墨汁既可写字又可画画,方便为上,好东西便也就失传了。
我对好墨的印象,是少年时父亲带我拜访一位老画家,画家住的房子又小又暗,房间里只摆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听他说,床也是他的画案,床边的桌子被挤在了墙边,上面的东西很乱,屋子里黑黑的,没有窗户,房顶有个天窗,天窗投下来的光线照在桌上包裹的一块红布上,那是屋子里最明亮的地方,我忍不住想看那红布里的东西,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颤巍巍的双手打开那块红布,那情景象电影镜头,当镜头展开时,我看到了一块用了一半的残墨,老人有些激动的一直在说这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并一再强调他的好多作品都是用它画出来的,他没有灵感时是舍不得用的。这位老人在我离别时送我一副对联——陶冶性情、变化气质。我一直记着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这段记忆因为那块被红布包着的墨锭在我心里一直十分明亮。
我自己一直未曾有幸得到块好墨,曾想往每日焚香弹琴,研墨画画。但现实与想象有差距,便也随遇而安,有什么家什便用什么家什。好画家拥有好文房,如同武士拥有一件好兵器,可寻不到好兵器时,找寻一个笤帚头能把它练得出神入化,那也算是个高手吧。画画的朋友聚在一起时也爱谈及笔啊墨啊的问题,有时会问起我用的墨,并觉得我的墨有“秘方”。其实哪有那么神秘,我用的墨其实再简单不过,有时都不好意思说,我虽对好墨心神往之,可现实却用着极普通极普通的墨,换言之也可称为“懒人墨”。每日里有练小楷的习惯,写完字的墨放在砚台里不舍得扔,时间久了变成了宿墨。再久而久之,旧墨、新墨、不小心泡软了的墨块,混合在了一起,越积越多,真的有点像“老汤”。这“老汤”幸好有个很深的砚台盛放,朋友来访总爱在这“老汤”前仔细观看,有时还凑上去闻闻,可那天长日久的味道总不够吸引人。除了这“老汤”,案头上倒是还有两锭墨块,一块是父亲送我的油烟墨,是文革时期的一块墨,一直舍不得用。还有一块是位上海朋友送给我的日本墨,叫清墨。这块墨因为太过精美,我也不曾用过。所以,除了这味道不佳的“老汤”和两块不舍得用的墨块,便再无特殊之处。可朋友问起我的墨来,要不说出个一二,似有小气之嫌,幸好我还有段制墨的小偏方,便赶快告知朋友们,请他们一试。记得在华侨大学时曾宓老师去教课,那时他常去我们家玩儿,他曾告诉我父亲关于他的墨的一些方法,过程是这样:找一块油烟墨敲碎后加水放锅中蒸,然后取出使它发酵,再放入甘油。这方法父亲告诉过许多朋友,但我却从未见他亲手做过此墨,听他讲述时我记住了几个关键词;油烟墨、蒸、甘油,但做此墨的前后顺序我却有些混乱,估计不管顺序如何终会制成不同寻常的墨吧。
关于墨的问题有时还会产生出些趣事,有一次去石家庄和韩羽老师一同吃饭,饭桌上韩老爷子突然问我,我用的墨中是否加了酒,我听了一愣,继而觉得这倒有趣,这墨中加酒是何反应,味道可闻,效果如何?此举一直未曾试过,不知是吝啬酒还是吝啬墨,是胆量不够该喝两杯,还是等年龄再大些来试,或许如此真的可写出个传世秘方来。
朱雅梅
2009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