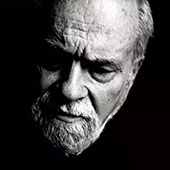王川的《燕京八景》是当代数码艺术的成果。从现象上看,它是一种摄影形式的外化,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与表现观念已不同于原有的机械取景和银盐成像。分析这一新的数码视像艺术,将揭示21世纪艺术创作与摄影观念的发展趋势。
一、方法与历史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数字化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全面普及到各种传媒、设计、图像制作等领域,成为20世纪末期对人类影响巨大的一项科技进步,其意义如同历史上的印刷术、摄影术的发明。在这种时代趋势之下,数字技术的潜在艺术价值便成为那些敏感的艺术家要孜孜以求的课题。每当一个时代出现新的技术进步或手段时,总会出现一些勇于探索和实验的艺术家,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因此构成了艺术历史进程的脉络和框架。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乌切罗(1397~1475,PaoloUccelo)是透视法发明者之一,他对这种新的绘画技术痴迷不已,大大推动了绘画艺术的进步;14世纪末,尼德兰画家凡•艾克兄弟发明了油脂颜料,让绘画更加细腻,光感的刻画更加逼真、传神,丰富了后来的油画语言的表现能力,成为西方艺术史的主体之一。摄影发明之后,它本身渐渐演变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各种各样的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格得以产生,也因此促使传统绘画向现代主义转换,从而改变了近代以来的艺术面貌。摄影对原有艺术的最大影响,莫过于一种新的艺术观念的出现:即艺术的真实性与仿真性以及艺术的表现性。它既影响着作为透视学关系中的真实世界的物理关系,同时也让绘画开始思考它自身的本体价值和依存方法。前者涉及到眼睛观看方式与世界的关系,后者则是艺术被促使拓展其领域、改变其观念并强化其主体性,因而从真实模仿世界的这个维度解放出来,将真实再现世界的课题交由摄影去完成,而自身向艺术本体与艺术家内心世界开进和挖掘,完成了现代艺术的转型革命。从此,真实性与再现性就成为摄影的功用之一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维度。
因此,在现代艺术历史上,摄影渐渐地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评价语汇,成为现代艺术门类中的重要一元。也因为摄影这种技术进步是与理性思维紧密相连的,极大地延展了艺术表现的工具性和表现能力,使得具有时代敏锐嗅觉的艺术家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实验和表现对象的拓展。在整个艺术体制中,摄影批评理论和话语也成为现代艺术哲学的组成部分。如本雅明对机器复制时代的作为光晕的摄影艺术的论断,影响了几代艺术家与理论家的思维和话语建构。真实性与复制性尽管争议很大,但还是在摄影理论中得到强调。所以,摄影才在时代的理论照映下,成为一门新的艺术类别,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数字与观念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来临,这就是数字化介质技术的出现。它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正日益进入到社会的不同领域和层面,改变、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同时,这一媒介方式所产生的虚拟化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引起理论界的争议,而艺术家则勇于探索它的新的潜力,挖掘它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自由能力。当理论家讨论虚拟的现实与现实的虚拟化时,艺术家则以艺术的行动来创造着数字化作品,既扩大表现领域,也尝试新的观念,用具体的艺术证明着数码艺术的诞生与发展。
新一代的数字化艺术的最大特点,是释放了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梦想,也创造了不可想象、不可言传的新的视觉景观。对这些特征,有很多学者、理论家都给予辨析、阐释或批评。数字化影像又重新引起真实性的讨论,因为虚拟的图像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视觉效果和程度。因此,一些人从原有的摄影理论角度出发,认为这样的数字化影像不足取,不可以与真实再现世界的传统摄影相比拟。其实,数字化作为手段释放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但更主要的是它本身具有充分的观念表达能力,它从技术层面上融合了观念艺术的观念性诉求,能够自如、自觉、主观地实施数码艺术的观念化。这就从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将数字化提升为更加独立的一门艺术,而不是原来的摄影。也就是说,数码影像天生具有了观念艺术的基因,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观念谱系决定了它不是传统摄影范畴,而是新型的艺术类别。但数码影像自身由于和传统摄影有着输出打印这样的联系,也和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有着相同的视觉构成关系,所以,它要在这样的粘连关系中成为自由的艺术,就需要建立另外的批评话语来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数码艺术涉及到的问题不仅是一种创作媒介的差异,而更深刻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现实形态与思维观念的出现,它们必然带来艺术方式的改变,也因此会改变着人们的接受习惯。从艺术家的角度,数码方式也挑战他们创造视觉形象的能力,也挑战着他们思考艺术的方式。因为数码是介入真实界之中的虚拟化镜像,是以数码的二元进制来编码现实世界的过程,它极大地对峙于物质世界的构成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数码方法才在艺术的现实中显示了它存在的理由,改写着当今的视觉文化,也改造了人们接受与阅读视觉形式的行为和观念。
三、王川的数码艺术与《燕京八景》
王川作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影像艺术家,用冷静的理性力量注视着发生在我们周边的图像世界和艺术语言的变化。他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影像创作,正好是数码艺术兴起于国际的时候,他敏锐地采取了这一方法,不断地应用到他的影像创作中。
首先,王川是以视觉艺术家的那种训练和敏感来认识和把握摄影与数码艺术的。他将当代影像艺术的多种创作方法放到艺术这个大的范畴里进行,为的是拓展影像艺术的领域和表现力。他先后经历了影像创作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前后衔接,努力形成自己的一条创作思路和线索。在这种多方位的影像语言的实践中,他逐渐明晰出当代影像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数码语言的功能化与现实性。这种思路来自于整体的艺术发展变化的脉络,不完全是摄影自身的变化,其逻辑是新的历史进步中的艺术变革趋势使然。
其次,王川不断思考影像艺术的语言方法,特别是思考数码语言的实践课题。数码语言有多种应用途径和手段,如虚拟构建、实拍加虚拟拼贴、摆拍加数码修饰等等。其中,对数码本体特质的探索也是有待于研究的一个方向。如德国的托马斯•鲁夫借用了数码的像素原理,试图揭示图像的内在结构与现实的关系。而王川也在同期尝试着这种像素结构的影像实验,其出发点不同于鲁夫。鲁夫是从网络上下载这些数码构成的图像来加以放大,在模糊与马赛克之间颠覆了图像的意义。王川则是思考像素本身所具有的表达特征和能力,是力图建构新的像素关系图像,而不是颠覆图像。他希望从这中数码的二元像素中探讨新的视觉语言关系,如何把像素概念置入到影像艺术的语言词汇表中。可以说,当代的影像艺术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如揉、折、戳、烧、撕;行为摆拍、情节摆拍、挪用摆拍、观念摆拍;纪实观念、行为观念、抽象观念;类型学拍摄与无表情美学影像;私密影像与社会政治影像,等等。而王川的像素数码作为方法是旨在确立它的独有价值。我们的习惯意识在识别和理解图像时,总是强调它的视觉清晰度,要求影像显示平滑过渡的整体图像。而像素语言则是建立在数码成像的原理上,将它的数码二元进制提升为独立的影像表达语言,从最微观的像素密码中发现图像成像的逻辑秘密。这种结构性的成像语言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本身将虚拟世界与视觉世界结合起来,在二元进制的体系之下还原了一种视觉印象。
所以,当王川应用这种像素数码原理去创作《燕京八景》时,他的思路和方法就渐渐成熟和明确。“燕京八景”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八个景点,人们给予它们许多传说和故事,是老北京的一种神话。当时光流转到数字化时代后,新北京跃然而出,这八个原来的场景都已物是人非,折射着太多的历史沧桑。当王川用数码的方式介入到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时,他就将现实虚拟化,在很平实的图像画面中嵌入了新的视觉阅读机制。在静态的数码图像中,经过计算机运算之后,像素构成的一幅幅“燕京八景”就呈现出历史的现实方位。因为像素的视觉效应,历史的远去和现实的景观才重叠在一起,暗含了图像语言转换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虚拟化的现实情景。这样,数码就不再单纯是技术手段,像素不再是孤立的数字演算,而是经过艺术家的观念运思之后转换为独特的视觉语言,在数码艺术的千枝竞放态势中卓尔不凡,自成一体。
实际上,在当前的现实格局面前,无论是传统媒介的艺术家,还是新媒介以及数码的艺术家,都面临着时代选择的问题。历史中的艺术家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选择历史、创造历史的结果。艺术史的构成是主动的行为,同样艺术的现实也是自觉的创造过程。当德波(Debord)以批判的姿态确认我们的世界已经处于景观社会中、并被物质化之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艺术的方式,通过艺术来确认现实的意义和非物质化。艺术的视角和艺术的在场使虚拟化的世界不被完全异化和对象化。王川探索像素的构成,即是力求赋予数字化以一种历史观照,将之视为历史的延续和艺术方法论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历史回应的《燕京八景》,就是显现了一种先锋姿态和艺术立场。
文/王春辰
(王辰春,美术史博士,美术批评家及策展人,现工作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从事美术史学方法论及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