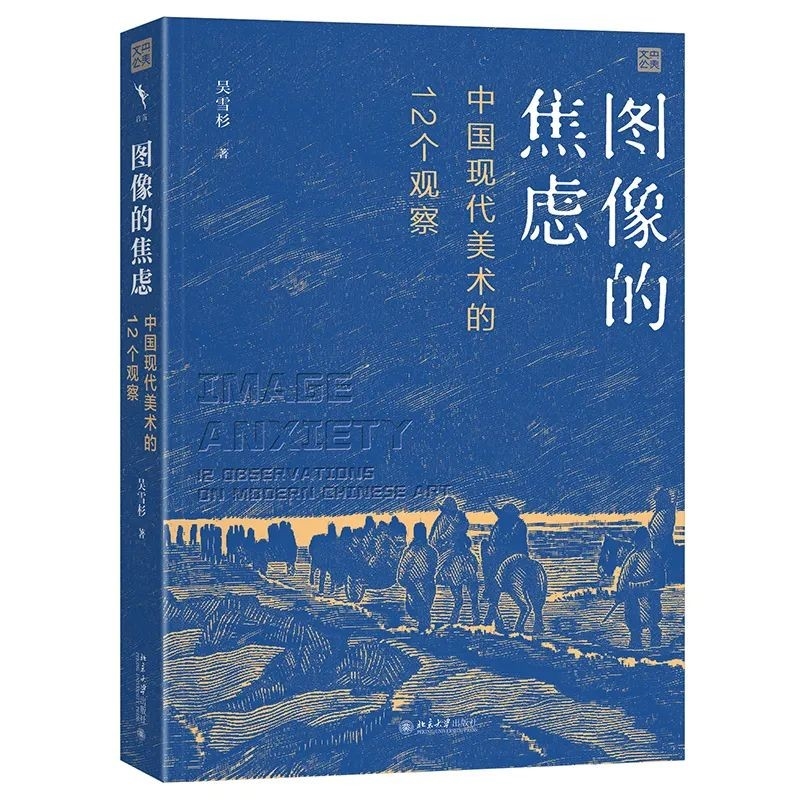【图书信息】
作者: [美] 乔迅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副标题: 明清的玩好之物
原作名: Sensuous Surfaces: 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
译者: 刘芝华 / 方慧
出版年: 2017-4-1
页数: 440
定价: 16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11732699
【内容简介】
在《魅感的表面》中,乔迅对明清时期中国的装饰艺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展示了明清时期中国装饰艺术从个人物品到整体住宅室内布置的各个层面,建立了在非宗教性的奢侈装饰背后一个松散变化的、不成文但仍不失连贯的体系。第一部分“玩好之物”,首先介绍了生产和消费奢侈物品的社会环境。第二部分“表域资源”,考察了单个器物所利用的表面处理的主要形式资源。第三部分“从表域到物境”,描绘了单个器物的表面组合在一起时营造出的室内整体物境。本书关注的时间段跨越了将近三个世纪,主要侧重于重建装饰艺术不断变化的、深层次的认知框架,同时也不会忽略讨论时代的差异。
奢侈物品物质地与我们同思,是为了让观者产生愉悦感,完成它们作为装饰的最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从视觉上和物理上将我们与周边的世界联系起来。意识反馈了感知的体验,如果读者观察得足够细致的话,将会从而获得对装饰品的崭新的、感官性的体验。当人们在装饰物品中获得愉悦时,到底与其发生了什么样的精神和身体的互动?本书有志于成为读者在体验明清时期的玩好之物时用来参考的系统工具书。书中约有280幅彩图,将带给任何对装饰艺术、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人士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体验。
【作者简介】
乔迅(Jonathan Hay) 1956年出生于苏格兰。197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考古学学士;1981年入美国耶鲁大学,随班宗华教授(Richard Barnhart)学习中国艺术史,专攻晚期中国绘画史、物质文化史。1989年以论文《石涛晚期的作品(1697-1707);一副主题的地图》]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研究所艾尔萨梅隆布鲁斯讲座教授,艺术史期刊《人类学与美学》特邀顾问(1990-1999)。乔迅的写作主要讨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主体性与世界性等问题;研究领域设计艺术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明清艺术、唐代墓室壁画、宋画及当代中国艺术。
【目录】
序言
部分玩好之物
1装饰就是奢侈
品位的政治
生产的地理
显示管侈
2与我们同思的器物
“器物—身体”和表域
超越结构—纹饰二元对立
装饰品如何与我们同思
关联的思考
3表面,触动,隐喻
表面的体验
触动和隐喻
【序言导读】
中国艺术品是西方收藏家最为熟悉的异域风情之一,上至稀有的成窑瓷,下至唐人街贩卖的造型陶器,都可以被涵盖在这一概念之内。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艺术品”并不具有历史性维度,他们所看到的每一件器物都代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中国。然而事实上,中国装饰品的基本模式进入西方视觉文化并不早,大约发生在1570年至1840年间。本书将主要讨论这一时期。在这绵延近三个世纪的时期内(直到1800年),中国是全球奢侈手工艺品进出口贸易的主导力量。这一过程也最终促成了西方所熟知的“中国装饰艺术”这一概念的形成。自17世纪早期开始,中国装饰品逐渐成为西方视觉文化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它们起初是进口的奢侈物品或少数访华者的旅行纪念品,在时移世易中慢慢变成了古董。18世纪,西方在“想象中的中国”的刺激下发展出了所谓的“中国风”这一艺术风格(chinoiserie,直到今天,中国风的装饰仍是西方室内装饰的标志性元素),再此之上加上对一些具体的中国装饰观念的借鉴,拓展了其装饰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然而,晚明(约1570—1644年)至清代早中期(1644—约1840年)中国的外销商品往往不同于面向本土市场的装饰艺术品。后者,即针对国内市场的产品是本书的讨论重点。当然,有一些外销产品与内销产品并无差异,这在18世纪以前尤为普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远销至西方、日本、南亚、东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装饰艺术品与内销的装饰艺术品在形制和表面处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特征。固然,我不会武断地认为只有内销产品才是正宗的“中国品位”,而外销的就是掺水的假货。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装饰艺术虽然与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装饰艺术有着部分重叠,但二者整体上是不同的。本书的、二部分指出,为中国本土消费者生产的物品遵循着约定俗成的装饰规则。这一套不断演变的规则制约着这些雅玩物件表面的形势布局(topographic configuration)和其表面鲜明的存在。这些规则是如何被运用于外销品生产中并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在此不作讨论。本书第三部分将展示,明清时期单一器物的装饰规则是与影响了器物表面组合的一整套室内装饰的不言自明的规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两种惯例或者规则来说,任何一方只有在参照另一方的情况下才能被全面地理解。奢华的装饰包括了种类繁多的工艺品和实践行为,但我的兴趣集中在17世纪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和鉴赏家李渔所谓的“玩好之物”上,这些玩好之物最初所存在的物理环境是社会精英的住宅内。李渔的“玩好之物”概念与现代西方观念下世俗装饰艺术的概念大致相符,包括了室内装饰的各个要素。因此,我们将主要讨论人的身体和建筑之间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之内装饰既不从属于人体,也不从属于建筑结构。相反,这些物件表面的装饰在物品的陈设和使用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稍纵即逝的环境。本书集中讨论这些问题,是为了在物品的表面之于装饰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作出连贯的探讨。为了实现这种连贯性,本书也令人遗憾地无法兼顾另外一些重要的话题。首先,“玩好之物”的观念排除了全部的宗教仪式性装饰,而后者需要一个视角更为广阔的、涉及更多概念性问题的探讨。佛教和道教的仪式是奢华的,这从道士、僧侣的长袍到装饰寺庙的各种幢幡及其他织物中可见。宫廷正殿的装饰同样是壮观的,它们同宗教装饰一样,由同一类负责室内装饰的工匠制作而成。2毫不意外的是,众多影响了表面的构成和其物质性的共同惯例在宗教和世俗的装饰中都发挥了作用。但宗教装饰与世俗装饰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某些具体的功能性的要求决定了特定器物的相应外观,如覆盖寺庙供桌的纺织品必然不同于居室厅堂中覆盖普通桌子的纺织品。其他的差异则贯穿于表面的设计之中。在宗教装饰中,纹样为了适应宗教仪式而倾向于带有象征意义。譬如,佛教的纺织品通常采用莲花的图像,这跟大乘佛教的重要法典《法华经》有关。另一方面,在世俗的装饰中,带有纹样的表面常常采用吉祥图像,让人联想起繁荣、快乐和富饶等概念。虽然我们充分意识到宗教性装饰在室内装饰这一范畴中的重要地位,但本书将不对之进行讨论。正如大量插图和绘画的记载所展示的,私人的住宅空间在节日、婚庆、葬礼和祭祖的场合中是作为宗教性场所被使用的。世俗性装饰的正常规则在这些场合中都被悬置,以便暂时营造出神圣的、寺庙般的空间。因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室内空间布置本身,这一仪礼原因所促成的的装饰的转换将留待另文讨论。此外,即使是在世俗性室内装饰这一狭窄的范围内,本书也只将覆盖其中的一部分。因本书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可移动的小件器物(portable objects),那些因佩戴在人身上而可以在室内移动的装饰以及隶属于建筑本身构件(尽管它们饶有意义)的装饰除了略有涉及之外,将不纳入详细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前者,我将跳过服饰和饰品(包括折扇、首饰、挂件和鼻烟壶)的讨论。对于后者,我对窗户、门、栏杆、柱子、天花板和地板的永久性装饰处理不作任何讨论,如有涉及,只是为了帮助说明那些可移动的器物。同样,出于对连贯性和重点的考虑,我还将忽略那些跟阅读和书写有关,但又不单独被用于展示的世俗性装饰——譬如插图书籍中的装饰成分,或者优雅通信中所使用的奢华信笺。这一讨论将集中于跟家居相关的非宗教性展示品。虽然显得广度不足,但代之以深度。我相信,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思路以及在后文中得到的针对中国装饰的众多结论只需要稍加修改,便可被推广运用于本书所未能集中讨论的中国装饰品的领域。在此,我还希望解释一下古董在本书中的地位。在明清住宅的室内布置中,当代的器物通常与古董组合起来陈设展示。一般的规则是,藏家越富有,把古董作为室内装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本书第三部分在不涉及古董的情况下难以重建决定室内整体景观的准则。尤其因为明清时期的作者通常选择通过讨论古董(它们在室内装饰 中占据特别显要的地位)来介绍装饰品展示的一般惯例。但考虑到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是早期现代的装饰实践,而不是收藏,并且本书的讨论的装饰品的时间上限始于早期现代,将不会过多地牵涉到对于古董的讨论。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古董的表面装饰不同于那些新近生产的器物,但当时的人往往是用同一眼光审视,用相同的术语讨论这两者的。并且,不要忘了从晚明开始许多被认为是古董的器物实际上是新近制作的仿品,它们的外形和表面装饰大部分符合当时的装饰规则。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古董对室内布置的表面构成有着特殊的贡献。岁月的痕迹——使用和磨损所带来的器物表面的视觉转变——为整个房间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时间感。天然的物体,如石头的表面所带有的岁月痕迹是受到高度赞赏的,而古董表面的岁月痕迹所展示的是文化的历史。不同年代出土的古董很早便受到历代收藏家的青睐。它们的表面既带有埋藏于地下时与泥土接触后所留下的痕迹,也带有前一任藏家上蜡和上漆处理所留下的痕迹。正如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古铜器收藏的评论所言:“他们希望它们有着某种程度的锈迹。”多种多样的效果使得鉴赏者只能依照当下的品位为古董的美观度和诱惑度排名。5至17世纪,古铜器的范围已经扩大,包括了从唐代以来生产的仿古铜器以及17世纪生产的宣德香炉,后者因为让人联想到15世纪宫廷作坊制作的宣德炉而有着特别的高贵地位。“岁月痕迹”这一参考标准也被扩展用于其他的古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那些用有机材料雕刻的物品。我们生活在一个设计已经取代了装饰艺术的时代。现代对于设计的概念是作为机械化的副产品出现的;机械化产生了设计者,设计者替代传统工匠(传统工匠的生存本身正被机器所替代)负责构思和执行。在我们今天对“设计”这个术语的使用中(如室内设计、产品设计),设计是设计师的工作。在器物被投入机器生产的状态下,现代设计有着特定的特征——执行是从属于构思的。当然,机械化在工业生产的历史上是非常晚近的发明,肇始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普及于19世纪。装饰品的工业化生产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机械化之前,这种生产是基于工匠的分工。虽然在工业的环境下,执行与构思是分开的,但二者都是出自工匠之手。从西汉的个手工业作坊直到17世纪,中国将近两千年都是如此。甚至当明代宫廷要求坐班匠为瓷器设计图样时,这些坐班匠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设计师,而是作为高水平的工匠被纳入整个生产过程的。然而,18世纪前半叶,一批优秀人才被任命负责清代宫廷装饰品的生产。尽管机械化并没有开始,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人对于工匠生产的熟练控制使他们的角色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设计师。他们所处的情境与现代设计师所处的情境的区别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经济效应,而是创造奢侈、新奇和精致之物,是为了具体呈现王朝的威权。总而言之,清代宫廷的装饰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设计,而且现代设计这一概念与1570年至1840年间生产的99%的奢侈装饰——无论是手工的单个生产还是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的关联更小。在所有这些手工艺品中,构思和执行都是密不可分的。出于这些原因,学者在描述明清的奢侈物品时,一般优先选择其他术语,而不是“设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装饰”(decoration)、“装饰艺术”(decorativearts)和“纹饰”(ornament)。这些词汇让人联想到机械化以前的世界,然而这些词汇被运用于现代生活的情境中时,常常带有某种负面的含义。艺术史家最初用它们来表示一个外在于现代世界的存在,在那里,传统而不是创新占据着统治地位。“装饰”在今天是一个贬义词:“纹饰”暗示着繁琐和“无用”,虽然现代设计的器物有时候也被包括在装饰艺术的范畴之内,这一分类只有在将之贬低到一种非美术的地位时才能被沿用下去。然而,对于前机械化的社会,如1840年之前的中国而言,这三个术语看起来都是恰当的。在那一历史情境下,装饰被阐释为将视觉愉悦引入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用来吹嘘所有者的地位和权力。装饰艺术借助于实用器物的审美化来实现装饰的功能,而纹饰被认为是实现审美化的方式。几代学者在这一参考框架中已经构建了关于明清奢侈物品的丰富而又详细的历史。同时,设计的概念并没有受到排斥,而只是使用了它的一个更为狭窄的意义。学者所讲的设计,指最终会被工匠转变成物质形态的图样形式,他们也将表面装饰的图样组成称为设计。更广泛而言,很常见的是将明清工艺品的设计视为指导了制作的构思。这些不同的用法承认了机械化之前装饰实践的某些方面,预示并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机械化和数字化世界里设计的重要角色。刚刚关于设计概念的简要叙述已为读者梳理了欧美近百年来关于中国文房雅玩研究的一系列专著的研究理念。它们的研究重点包括断代、鉴定、工艺技术、象征主义和品位这些问题。因为本书将利用这些成果,我希望冒昧地指出,这一伟大的学术努力因为将现代西方对于装饰的假设强加于中国装饰品之上,已经扭曲了明清奢侈物品的图景。这些专著非常显著地——但完全符合逻辑地——低估了(如果不是完全忽视的话)作为装饰的奢侈物品最为显著的、至关成败的特征,即魅感的表面(sensuous surface)的形势布局(topography)。我认为器物表面本身是现在关于明清(实际上所有非现代的)奢侈物品思考的关键盲点。大多数这方面的专著——当然也存在例外——偏离了对于装饰品的主观体验,而更倾向于将器物视为等待着秩序化和客观阐释的物品来讨论。6对我而言,我的前提是,装饰品的感官体验既然是它们的制作者关注的重心所在,那么也自然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用崭新的概念对器物的表面加以审视,或许可以进而重新认识和定位奢侈物品。而这正是这本书的意图所在。正因为如此,本书当然不否认过去一百年来所取得的众多研究成果,但它的确有志于重新整理和思考这些积累起来的信息。本书的基本论点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概括。奢侈物品魅感的表面同时带有隐喻的(metaphoric)和触动人的(affective)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借助于我们对器物的愉悦体验被实现。就这一点而言,器物可以说是具备了物质地思考(thinking materially)的能力,只要我们记住它们的思考方式与人类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物质地思考需要有人类观者的参与来促使它发生。奢侈物品物质地与我们同思,是为 了让观者产生愉悦感,完成它们作为装饰的最基本的功能。我认为这一功能从视觉上和物理上将我们与周边的世界联系起来,制造出一种有意义的秩序,摒除了随意性,并将我们编织入周围的环境中。固然,所有的视觉艺术之所以能打动人心,都是用我刚刚所描述的这种建立关联性的基本方式去调解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但装饰与其他的视觉艺术略有不同的一点是,它的全部调解功能就是营造这种感性的关联,而其他的艺术创作往往会在此之外同时追求营造一种距离感,去刺激人们冷静的思索。确实,装饰的众多社会功能的实现取决于器物能实现这一感性调解与关联的能力。在接下来的详细阐述中,本书有志于修正读者对装饰的感性体验的认识。因为意识反馈了感知的体验,如果读者观察得足够细致的话,我认为将会由此获得对装饰品的崭新的、感官性的体验。意识和体验的转换不是小事,它的重要性也不只局限于抽象的现象学意义。它意味着艺术的每一层面将被置于更为广大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态之中,因此装饰本身的涵义亦随着读者这一“新视觉”的引入而发生转变。由此,本书关注的是作为人类生活永恒存在的艺术形式之一的装饰的基本特征。对此,相对于涉及不同历史和文化情境的装饰的比较性讨论,个案的研究方法更为有效。前一种研究方法以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秩序感》(The Sense of Order,1979 年)和奥列格?格拉巴(Oleg Grabar)的《纹饰的调解》(The Mediation of Ornament,1992年)为代表,但因为他们在不考虑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来考察装饰的一般法则,导致其研究存在相应的弱点。虽然我很欣赏这些研究巨著,并且从中受到不少启发,但总觉得它们一方面过分宏观,一方面又不够有野心。因此,我选择集中讨论跨越了明清二朝、特别是1570年至1840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的奢侈装饰,这一时期在本书的英文原题中被称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出于行文的方便,我有时也用“明清”(本书此词指的是从晚明到清代中期)一词指代这一时期。虽然历史中的线性变化这一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不占主要位置,但我要强调的是,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描述为“早期现代”是想指出——因为需要指出——当代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有着一段前史,并且西方绝不是现代化的唯一起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1570年至1840年这一时段的中国仅仅呈现出早期现代的特征,同时“明清”这一术语也并不是完全中性的描述。这一时期是复杂的,也确实是断裂的,对它的全面理解不仅需要区分和并用现代和朝代两种时间框架,还需要了解前代文化较之于后来者的特殊权威性。部分,“玩好之物”,为本书设置了基本的讨论场景。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生产和消费奢侈物品的社会环境。然后更为详细地展开主题,即装饰品通过跟愉悦相关的魅感的表面所带来的隐喻和触动的可能性来与我们一同思考。第二部分,“表域资源”,考察了单个器物所利用的表面处理的主要形式资源,每一资源都有着各自隐喻和触动的可能性。第三部分,“从表域到物境”,描绘了单个器物的表面组合在一起所营造出的室内整体的物境。因为本书关注的时段跨越了将近三个世纪,我将主要侧重于重建装饰艺术变化的连续性背后的深层结构的、认知的框架,但不会忽略讨论时代之间的差异。阅读至第三部分的末尾,读者将会逐渐认识到,在那些非宗教性的奢侈装饰背后,其实存在着松散变化的、不成文的、但仍不失连贯的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汉人和满人的精英阶层而言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本)。本书最后一章将尝试回答贯穿了整本书的问题——当人们在装饰中获得愉悦时,到底与装饰发生了什么样的精神的和身体的互动。这一结尾完善了我强调应该用人的经验性体验去认识装饰这一理论观点。这本书有志于成为当代读者在体验明清的玩好之物时可借用参考的一个“系统”或者“工具箱”。考虑到这是一本小书,我不得不避免针对特定器物的过于冗长的解释。本书大约三分之一的插图是展示装饰品如何在明清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绘画或者木刻版画,同时也采用了不少表面描绘有装饰品的器物的图片。这些插图把单个工艺品还原到当时所处的种种环境之中,同时提示我们明清的观者是如何关注装饰的。这些图片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具体器物;“参见图片”则指出了相关的,位于文中其他地方的插图。当然,认真的读者可以自己在文字和图像之间建立起更进一步的联系。这些不同器物的图像也有助于抵消插图中景德镇瓷器占相对多数的问题。我在选择单个器物的插图时,故意集中在某种特别的器型上,而不是着意涉及所有该器物的形制,因为在一本讨论表面这一问题的书中,关注一种基本器物形制能承载的多样的表面处理是很有意义的。瓶、碗、杯、茶壶、酒壶、笔筒和香炉是最常见的形制。在决定讨论哪种材料类型时,我遵循了同一个原则,更多地关注黏土、硬木、竹子、漆器、丝绸、硬石(包括玉)和铜合金这些材料。人们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史家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我想我绝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被艺术所带来的众多愉悦感所吸引而进入这一领域的人。因此,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作为学科的艺术史并不鼓励针对愉悦感的讨论,这是一件多么使人震惊的事!30 年过去了,在学习执教辗转于几个国家之后,我发现这一切仍然鲜有变化。我终于逐渐明白,“愉悦感”在现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下是另一个研究的盲点。在现代的艺术史知识体系中,学者们只有悬置“愉悦感”才能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体系里(主体—客体、中央—边缘、真品—赝品等等)书写艺术史,而这种二元对立仍然在左右着现代艺术史这一学科。如果不能跳出这些二元对立,我们是无法考查愉悦感在艺术鉴赏中的重要性的。所以在艺术史这门学科的认识论终于得到彻底反思的今天,愉悦感应该自然地被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考虑到在艺术实践中装饰是产生愉悦感的最重要的手法,本书专注于讨论器物表面的装饰,望能对(作为现代重要人文学科之一的)艺术史的学科建设尽一分力。同时,就个人而言,这本书也是我把从每日流连在艺术品中所获得的愉悦感融入到历史书写中的一次迟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