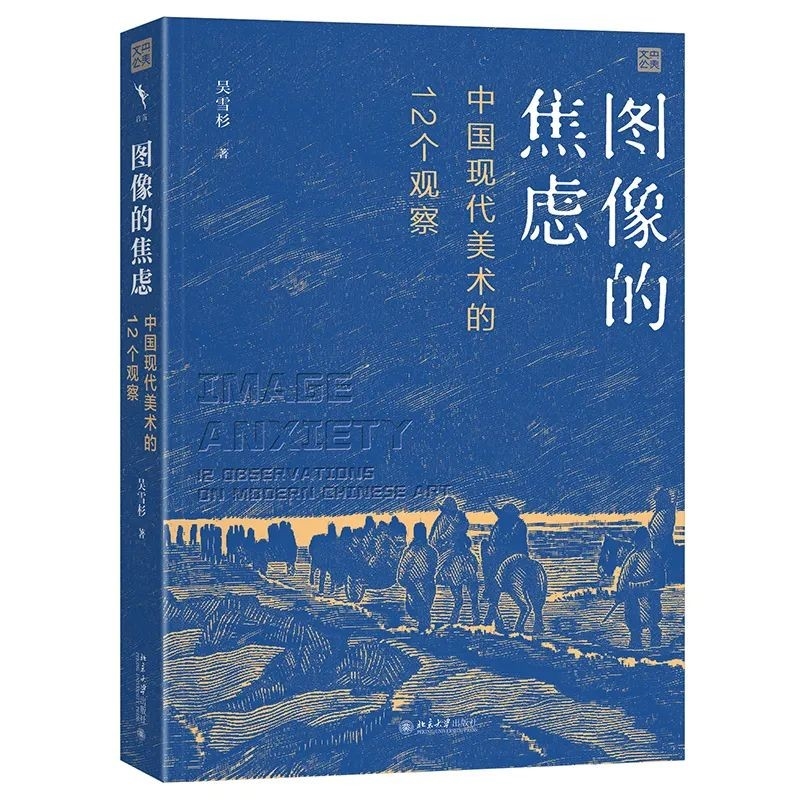【图书信息】
作者: 范景中(编)
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副标题: 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
出版年: 2003-03-01
页数: 1201
定价: 12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艺术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810830379
【内容简介】
《美术史的形状》是为那些对西方美术史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编纂的,是为那些想了解西方美术史的探索方法、一般理论和学术演变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也是一本关于美术史文献的书目,如果说美术史家都是旅行家这种说法言之不虚的话,那么,《美术史的形状》也是想给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旅行用图。
【作者简介】
范景中,男,1951年11月生于天津。197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年入浙江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理论。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译有:《法国象征主义画家摩罗》、《古希腊雕刻》、《图像与观念》、《艺术发展史》、《艺术与错觉》等。
【目录】
上册
序言
瓦萨里 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名人传
贝洛里 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
德皮勒 绘画的基本原理
温克尔曼 古代美术史
歌德 论德意志建筑
布克哈特 历史的沉思
莫雷利 意大利画家
沃尔夫林 意大利的古典凯旋门
维克霍夫 论艺术普遍进化的历史一致性
李格尔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普列汉诺夫 从社会学观点论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
旋洛塞尔 论美术史编纂史中的哥特式
瓦尔堡 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和国际星相学
德沃夏克 埃尔·格列柯和手法主义
弗莱 视觉与赋形
附录
戴恩斯 哥特式概念
贡布里希 阿比·瓦尔堡:他的目的和方法
注释
下册
序言
第一章 作品研究与查阅文献
第二章
1美术书目的历史
2 美术词典的历史
3 美术品目录的类型和简史
4 美术期刊
5 美术史丛书
第三章 图像志书籍的历史
第四章
1 美术史学史书目
2 文艺复兴美术研究书目
3 美术史家及其代表作书目
第五章 瓦尔堡图书馆:古典文化艺术的记忆者
附录 美术文献
瓦尔堡图书馆的历史
美术书籍的艰难诞生
【序言导读】
本书是为那些对西方美术史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编纂的,是为那些想了解西方美术史的探索方法、一般理论和学术演变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但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不是西方美术史的专家。我至多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喜爱西方的古典雕塑和大教堂杰作,喜爱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和手抄本及印刷本中的精美插图,喜爱伦勃朗,也喜爱凡高的艺术,喜爱它们就像喜爱西方的古典音乐一样。我常常为人类能创造出这样的非凡奇迹而感到震惊,因此我想把自己从艺术中得到的惊奇感和愉悦感传达出来,同时,作为一名教师,我也想把西方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和境界展示给年轻的一代。
当然,我也不否认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抱负,在我看来,一切美术史家都是旅行家,旅行使人胸襟开阔,识见广博,他不仅能在自己的熟悉领域,临视旧乡,指点江山,而且还可以进入邻界去吸收清寂的空气,凭高极目,获得喜悦。因此就像人类的旅行没有疆界一样,学术的整体性也不应被人为的界限隔断;就此而言,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的研究就会有所欠缺,同样,不了解西方美术史,中国美术史也很难进入美妙的境界。无论如何,不管是哪种美术史,它们都在历史中显示出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使我们获得了高度文化修养的那种古典文明的价值。因此眺望西方美术史,尽管是迢遥的远望,也无疑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美术史的范围内开拓出更广阔的领域,达到某种更精湛的程度。
这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的工作的主导思想,但实际做起来却很不理想。它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它所要求的基本学术条件,例如,对外语的精通,对文献的把握,对西方文明的理解,都是我不具备的,而且,这项工作几乎是筚路蓝缕,在我以前,除了滕固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翻译过一篇介绍德语国家美术史研究状况的短文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先例可循。因此,尽管我只是想遥看异国的景象,视线也是模糊的,它可能会落入冥渺的天际。幸好我有个信念,我觉得,对知识不是求全就是虚无的态度,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合乎情理;况且,也是更重要的,我还可以学习。也许,业余爱好者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对他的工作充满了乐趣。
但是,学习又谈何容易,当一个人处在孤往独行之中就尤其如此,有时候学习不过是排遣寂寞而已。然而,幸运的是,在几年后我却意外地获得了奇遇,结识了杨思梁和徐一维这两位不可多得的挚友。从此,我的工作面貌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他们都是杭州大学的英文教师,而且都具有语言的天赋。杨思梁不仅能说多种外语和方言,而且有过目成诵的本领。我翻译的波普尔悼词,就是他听贡布里希读了一遍便默记在心然后背下来写给我的。徐一维则多才多艺,似乎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都能化难为易,他不仅英语出众,而且还学习过意大利语和拉丁语。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很快就体现出了强烈的献身精神,不知疲倦的下苦功夫和惊人的通力合作的胸怀。尤其重要的,他们都体现了拉丁语所谓的Sola nobilitas virtus,他们的高贵的气质使我们排除了知识分子之间的最坏的毛病,即all the jealousies which spoil friendship那种恶习。康德曾经说过:‘通过艺术和科学,我们获得高度的文化素养,我们在种种方式的礼貌和体面方面已有高度文明。但从道德上衡量,我们仍有很多不足,因为道德观念属于教养范畴。’(《普通的历史观念》)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我总是想,我们不只是生活在物质世界,我们也生活在道德世界,尽管这一世界常常被势利世界、被阴暗世界所包围,然而能从这种道德世界一瞥慰人情怀的光辉,哪怕是小小的一束微光,我们也会感觉出人生的价值和美丽。而我们的合作,却使我同时享受了艺术和道德的双方惠赐,我不能不由衷地感恩。
说起感恩,我自然想起Grace,它既指上天赋予的恩惠,也指上天赋予的资质。我承认我比较相信天才,但我却愿意做一个半天才论半环境论者。我自己生性愚钝,那是无可奈何的。但平生的际遇也是命途多舛,抄家、流浪、充边的生活都经历过。我没有受过严格的正规教育,中学只读过两年,大学只读过一年,而且根本就没去上课,实际上就像我常说的,我是一个受教育残缺不全的人。有时我会感到,自己就像在寒夜中飘泊的一颗流星,无人导航,孤独偊行,也不知最终会陨落在何方。尤其遗憾的是,当我1990年终于获得了一个真正受教育的机会——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博士时,又发现了癌症。在我欣幸命运骤然转机的关头,却坠入了深渊。
当我在病床上,与另一个世界的威力进行较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曹楝亭的诗句‘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忧患成’所凝结的沉重感慨;感念逝去的年华,我愈加珍惜杨思梁和徐一维在介绍西方美术史学方面所付出的宝石般的时光。他们默默无闻地帮助我工作的景象,每每忆及,便情不能自已。他们不但经常不署名地翻译那些高深的论著,而且实际上还像秘书一样,为我书写了大量的英文信件。也许是天生对文体的敏感,由于我对英文缺乏训练、没有辨析文体的能力,所以从来不敢去用英文写作,我给贡布里希写的唯一一封正规的信,是请曹意强先生于1991年秋赴牛津读博士时转交的;那封信除了向贡布里希介绍曹意强之外,主要讨论的就是贡布里希的写作风格。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我从死亡线上向外苦苦挣扎时,杨思梁和徐一维对我的帮助,当时,杨思梁已赴美国,他自己也正处在困难之中,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帮助我获得一些收入。徐一维则经常在我们新分配的陋室中修修补补,为我们解决了大量琐碎而恼人的家务。我深知,他们牺牲了他们最重要的研究,凭他们的智慧和基础,他们都是才智超群的奇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美术史的形状》,它的雏形就是徐一维在赴美之前和我拟定的,他为此翻译、抄写了30万左右的文字。杨思梁在海外时常给我寄书,使我在蛰居养病的5年中还能与美术史保持著微弱的联系。10年之后,当我能够重拾旧业,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样一部书题献给他们二位。
现在,我已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原来的计划,想以十卷本的形式出版这部《美术史的形状》[The Shapes of Art History]。此书的英文题目意在暗示:我所谓的形状,是复数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形状;它表明,我不是一个一元论者;它也表明我没有陷入那种为美术史找出本质的泥潭,即我不会费神地去追问‘美术史是什么’之类的亚里士多德本质论式的问题。当我谈论形状时,我想到的不是研究学科,而是研究问题,只要你研究问题,它们随时都可能冲破任何题材或学科的界限。关于这一点,我应该感谢波普尔的哲学。
十卷本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卷,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美术史文选;第二卷,从20世纪30年代到当代美术史文选;第三卷,美术史书目文献;第四卷,美术史的基本术语和概念;第五卷,美术史中的图像学研究;第六卷,美术史中的风格理论;第七卷,美术史与观念史;第八卷,美术史与科学史;第九卷,美术史与修辞学;第十卷,美术史的历史。
这十卷本中没有给美术史中的鉴定学单列一书,无疑是一个遗憾,因为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可惜我手边的文献不足,多年来,我一直孤陋寡闻,几乎处在美术史的边缘。因此我希望这十卷中的莫雷利和奥夫纳的两篇文章以及‘鉴定学’的专论能弥补这一缺憾。我也希望有其他的人来补且罅漏,张皇幽眇,编出更翔实的卷帙。
不言而喻,这十卷本不足以代表西方美术史的整体面貌,它们只是我所窥见的一麟半爪而已。然而我力求它们能够反映出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毕竟这一学科为人文科学频频赢得了光荣,或者说它有个光荣的学术历史。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现代人文科学正在逐渐衰落,有时不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我不只越来越梦想著回到19世纪的库格勒[Franz Kugler] (1800-1858)以来的研究时代,甚至也经常在心中勾划出一幅董其昌、项元汴等人苕水书船、访古搜奇的图景。我想象,在那些时代,艺术的理解、鉴赏和研究还深深地植根于文明的整体之中,它们通过各种文脉吸收养料,决没有被狭隘的专业化所孤立、所隔绝。
因此,我理想中的美术史与越来越制度化、经济化和时尚化的学术工业式的美术史截然相反,我认为,它应是专业的学术[Wissenschaft]和普及的教化[Bildung]的结合,博物馆的活动和大学的教学的结合,鉴赏家[Kunstkenner]的实践和美术史家[Kunsthistoriker]的探索的结合;它不仅体现知识的整体性,而且也体现人性的整体性。这就是我所想象的美术史的形状,这也许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梦想。我想,伟大的潘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梦想的,否则他在他的名篇‘作为人文科学的美术史’中就不会以康德关于人性的感人肺腑的谈话开头。我深知,很多人不想把艺术视为天下公器,他们觉得那是懂艺术者的专有之物,他们抱著专家的优越态度,高视傲兀,目空一切,正如歌德所说,当他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便会表现出固执,而当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时,又会显得无知。因此,我从不想去参加那些关于美术史到底算不算人文科学的辩论。
我始终强调,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是一个愿意终身学习的人。就此而言,我心里想到的是17世纪的历史学家帕普布洛奇[Daniel Papebroche]。他是一位精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但他在不熟悉材料的情况下,却贸然在《古文书真伪辨异序》[Propylaeum Antiquarium circa veri ac falsi discrimen in vetustis membranis]中否定了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的圣德尼修道院[St. Denis]中那些极其重要的特许状的真实性。这激起了马比荣[Dom Jean Mabillon](1632-1707)的争辩。但后者不是感情用事,讥讽其文,把一些字眼使用过火,而是智慧地列出历史批评的一般原则,运用前者欠缺的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等辅助学科在纯学术的水平上进行讨论,并最终产生出创建了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的经典著作《古文书学六书》[De re diplomatica libri VI](1681)。
马比荣的书代表了把对学问的彻底忠诚和审慎的精确性与独立的历史批评精神和无比的熟练技巧结合起来的典范。帕普布洛奇读后致信马比荣说道:
我可以坦率地向你公开承认,我以这个题目写的那篇文章得到的安慰没有别的,只是为你那篇如此杰出的论文提供了撰写的机会。的确,在初读你这部书时,我看到自己被彻底驳倒,毫无答辩余地,也感到一些痛苦;但你这篇极其难得的文章的效用和妙美很快就征服了我的弱点。而且,在看到如此清晰地阐明的真理之后,我欣喜万分,于是就把我的同伴邀来共享我内心充满的欣慰。因此,一有机会,我便毫不犹豫地公开声明,我已完全放弃了我自己的主张,完全接受了你的思想了。我向你恳求友谊。我并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很想学习的人。
与那些自视甚高的专家不同,这是自尊和谦卑的流露,是一种简单事实的表述:承认自己所知甚少,而未知又何其之多。因此,他轻视那种在见解上以权威自居的自命不凡,而代之以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乐于倾听别人批评的态度,尽管承认错误往往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这种态度不仅帮助他增长知识,而且帮助他认识到他的精神正在成长,从而显示出道德和理智的责任感。这就是我向往的襟怀。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一篇关于骨法的文章中讨论过美术史的写作方式。多年来,我一直对于这个论题抱有极大的兴趣。记得莱辛[G. E. Lessing]曾经抱怨过:‘我们这些聪明的作家很少是学者,而我们这些学者也很少是聪明的作家,前一类人不愿意读书,不愿意追本溯源,不愿意收集资料,总之,不愿工作;而后一类人除了干这一类事之外,其他事情什么都不干。前一类人的作品中缺少素材,后一类则缺少把资料写成好文章的本领。’我认为这些话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现代的学术文章越来越缺乏光彩,越来越变成文件;不是时文,就是谀文;时而晦涩,时而干瘪;这就是一些学者怀旧的原因——他们怀念在二战之后日益断裂的19世纪以来的写作传统。
关于这一传统,我想到两位人物。第一位是法国的米舍莱[J. Michelet](1798-187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从小就像卢梭那样,把文学看作生活里的精美的奢侈品,是灵魂深处的花朵,因此他把文学的笔调融入历史。他像画家一样利用歌谣、古币、像章、图画、建筑和彩色玻璃进行写作,在他丰富的想象之中,那些遗物都能重现往昔,他甚至常常把自己当成笔下的那些主角,滔滔不绝地叙述,以致忘乎所以,正像汤普森[James Thompson]所描述的:
当他撰写恐怖统治时,由于紧张而病倒,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不但使过去复活,而且他自己也从中再经历一番。他说;‘基佐[F. Guizot]称历史为分析,蒂埃里[A. Thierry]称之为叙事;我管它叫复活。’有一次他曾说:‘别人更有学问,更明智;至于我,更多的是爱。’正是他的这种爱,对自己的论题的这种同情,使他赢得了巨大成功。不妨补充一句:他的不朽也是由此而来。
此处米舍莱所说的别人,就是我想到的第二位人物英国历史学家克赖顿[M. Creighton](1843-1901)。与米舍莱相反,他沉著而冷静地工作,在他的《教廷史》[History of the Papacy]中公开宣称他的目的是‘把资料收集起来,以便对16世纪欧洲出现的变化作出判断;而人们只是大而化之地把这个变化叫作宗教改革’。当人们批评他忽视了历史学家的责任时,他回答道:历史的真正价值和秘诀恰恰就是它的超然态度和纯洁的公正。另一位历史学家霍奇金[Thomas Hodgkin](1831-1913)曾经向他学习过,并这样记述他:
他提醒我注意各种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他教给我撰写历史应当遵循的方法,从而提高了我的水平。我觉得米舍莱曾使我有点眼花缭乱,因而认为主要之点是把历史写得像图画一般,必要时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想象。但克赖顿却对我说,‘我总是喜欢使我写的东西和资料扣得紧紧的’。从那以后,他这句话就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与米舍莱的‘热抽象’——借用抽象艺术的术语——不同,这些‘冷抽象’的写作方式同样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它们的魅力也许在于:叙事真挚、诚恳,笔力简洁、刚健;理性的力量有时胜过华词丽句,同样能打动人的心弦。
这是两种极端的写作方式,一种近乎古老的ekphrasis[艺格敷词],一种近乎现代的interpretation[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正如维吉尔在描绘爱情时声音甜蜜和谐、在叙述战争时诗句迅猛激越一样,手段是用来表现的,或表现感情或表现观念,但它又不是无所凭借,而是有赖于程式、有赖于文体。历史学家所选择的文体其实就是他们表现观念的框架,没有这种框架,他的观念就无所附丽。不过,我们也不难认识到,在所谓冷与热文体的两极,当中充满了游刃的空间,在这部选集中,我也力图给出各种程式的样板。但有一点应该提醒读者,若想体会作者的文体,必须去读原作。译文的作用,充其量不过如歌德所说:如果我们极口称赞一位半遮半掩的美人,赞赏她的姿色,那不过是想引起读者对原著的不可抑止的思慕而已。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傅新生和李本正先生翻译了正文,孙瑜、李宏、万木春、贾春仙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我则根据前人著作补写每篇前的评传,材料取自各书,连缀成文,述而不作;然而惨淡经营,差似有一得之见,或钩玄提要,偶有别裁新解之处,亦径直写入;限于篇幅,不作注释。
谨将几种重要参考书列举如下:W. Eugene Kleinbauer, Modern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Writings on the Visual Art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1; Michael Podro, 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2; Gert Schiff, German Essays on Art History,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88; Udo Kultermann, The History of Art History, Abaris Books, Inc., 1993; Eric Fernie, Art History and its Methods: A Critical Anthology, Phaidon Press, London, 1995; Jane Turner, The Dictionary of Art, Grove’s Dictionaries Inc., New York, 1996.
许江教授、尹定邦教授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长期的支持;曹意强教授、邵宏教授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他们也都将有美术史学史的专著问世,届时请参阅;黄专教授在病中仍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令我十分感动;Uta Lauer博士、王胜先生、梁颖先生、洪再新教授、严善醇教授、沉揆一教授、沉语冰教授在资料上时常予以惠赐;王霖先生则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许多精细的工作;凡此种种,难以缕述,友朋高谊,谨志篇末,并致谢意!
范景中
2002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