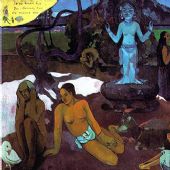凝视[gaze]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事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看”。它同时也是探查和控制。……当我们凝视某些东西时,我们的目的是控制它们。
——【英】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
视觉,被看作最高级的人类感官形式,它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排除了与身体相关的利害关系,而更多地与精神或灵魂相连。因此,“视觉”在道德谱系中占据着较高级的位置,视觉活动天然地包含了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意味,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个体或群体之存在的认知,是以视觉模式进行的,个体或群体的身份,由一系列“看上去相似”的符号或类比关系来判定,具有连贯性,可以被由表及里地认知。以这种方式认知出来的身份是高度统一的,可以被完整地掌握、被权力所浸透。在20世纪中叶以前,视觉化的身份图式主宰着西方文化,也支配着西方人对其它文化的认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看”的关系,一种凝视的关系。 西方主体在凝视中寻求一个统一的“东方”,以便彻底地加以认识和掌握。
视觉艺术,是人类视知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最高级活动方式,也是被凝视所浸透的最有代表性的活动。视觉艺术离不开“看”,因此总是伴随着不间断的价值和道德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整部西方美术史就是一部再现各种价值和道德取向的历史。
从18世纪开始,随着殖民活动的不断深入,“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艺术体裁流行开来。19世纪,对东方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波及面相当广泛,是一场由文学家、艺术家、摄影师、旅行家牵头的对“东方”的全民凝视活动。直到今天,这一活动仍未停歇,表现为西方艺术家对东方的各种再现,如绘画或雕塑、建筑或影像,最近一二十年间则更多地表现为策展活动。
萨义德(Edward Said)一再说:虽然西方对东方的再现经过了历时性变化,但其背后深藏着“永久性同时代感”,确保东方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被观看对象的稳定性,这是东方主义与殖民帝国得以建立、承继的基础。 但是,通过对19世纪西方美术史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经过了一系列变迁,其连续性不停地被各种本质性的断裂、转向所打断,其稳定性并不大于其变化,反而不断地揭示出内存于殖民体系的矛盾。这些矛盾在视觉艺术中直观地表现为“凝视”关系的调整。但有趣的是,这些矛盾、转变,并不与“东方”本身的变化相关,也并不与反殖民斗争的各阶段相对应,而更多地属于“西方”文化的自体运动,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力量关系变化所导致的。
1、凝视的绝对权力: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热罗姆
谈起视觉艺术中的东方主义,人们首先会想起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的东方后宫或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马战图景。在一些艺术史家眼里,安格尔的东方是色情的凝视,是帝国尊严在视觉领域内的延续;而德拉克洛瓦的画作则是一位感情充沛的艺术家投身于异国他乡的浓烈色彩时所发生的共鸣,体现出自由的精神。然而,当我们观察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的东方主义作品,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让我们从最熟悉的作品开始。
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1862)被精心设计成一幅圆形画,如同从窥孔里所看到的。宫女神情慵懒,肉体彼此叠加,充满了色情的魅力。很明显,“色情”所关乎的不仅是性,甚至主要不是关乎性的,而是一种剥削性的权力结构。 通过将一个人的身体处理成色情对象,剥夺其精神价值,消解其抵抗能力。因此,色情活动要通过凝视行为来完成,色情对象(宫女)是凝视的纯粹客体,被剥夺了主体资格,在权力关系中只能束手就擒。德拉克洛瓦的《萨丹纳帕那斯之死》(1827)对权力关系的表达是类同的。此画的有趣之处在于体现了一种双重凝视关系:萨丹纳帕那斯王凝视着被自己下令杀死的宫女、奴隶与马匹;观众则凝视着整出悲剧的发生。此画同样被精心安排了色情意味:宫女袒露肉体,她们被杀时绝望的状态充满了魅力,被从各个角度展现出来,王的毫不动情的凝视增加了场景的残酷性。由于残酷性是绝对权力的一种极端表达,它比肉体的展示更具有色情意味。而在观众的凝视中,王也沦为观看对象,王置身于金银珠宝、美女名马中间,暗示他也是景观而非主宰者。只有观众才能毫无悬念地看到悲剧上演,用凝视去征服王和他身边的一切。
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都强调了凝视的绝对权威性。画中人被固封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切举动都深陷于画作之中,对观众的凝视毫无意识、也无从抵抗。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一幅画,一个被凝视的客体,所有的阐释活动都由凝视者来进行。
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两位画家将这种结构普遍应用在不同的画作中。
安格尔的《瓦品松浴女》(1808)描绘了一个背对观众的裸女,对别人的窥视毫无察觉;《大宫女》(1814)和《泉》(1856)都面对观众,但《大宫女》的眼神迷离、充满诱惑,《泉》的眼神则极其无辜。这是两种理想色情对象的基本范型。人物面对观众,眼睛却未曾向外投向观众,而是向内投向自己,构成对自己身体的揭示,协助观众完成凝视行为。两个人物的形体都有着非自然之处:《大宫女》的脊柱被不合情理地拉长了,《泉》则不可思议地完美,她们的身体完全是为观众而设计的。德拉克洛瓦描绘的大都是强壮的男性,《吉奥与帕夏之战》(1835)和《猎狮》(1855)是其代表作。尽管前者表现了两个战士之间的争战,后者表现了猎手与猛兽的斗争,但在两幅画中,人和兽并没有区别,战士、马匹、猛兽,都处于极端激动的状态,身体彼此纠结,眼里闪耀着野蛮而残酷的光辉。在西方文化中,身体/灵魂这对范畴,是紧密地与自然/理性这对概念相匹配的,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为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区别。尽管德拉克洛瓦描绘的是男性,他们却从属于“身体-自然-女性”的范畴,和安格尔的宫女一样,也是凝视的纯粹对象。
在西方艺术史的这一时期,对绝对权力的诉求不仅存在于东方主义作品中,在处理性别关系时,类似的权力表达更明显。达维特(Jacques-Louis David)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的代表作《贺拉斯兄弟的宣誓》、《布鲁图斯》、《劫夺萨宾妇女》,对充满力量的男性和软弱无力的妇女的区分几乎是原型化的。 在权力的分配体系中,性别与种族,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相互平行,而且相互交错。 这一点在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那里得到了最极端的表达,他的《东方奴隶市场》,在表达男性的绝对权力方面堪称典范,同时又以揭露东方人的陋习为契机,暗示了西方世界的道德优越性。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的:黑人是性别化的,因为他们也是被剥夺的对象。
可见,东方主义的盛行不仅与殖民活动相关,而应该被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文化观念:身体和欲望是罪恶之源,必须受到监管。这一观念贯穿于教父言论、神学论著、信仰指南、宗教和世俗实践中。女性作为一个性别整体被看作人格化的身体和欲望,有色人种作为一个种族整体则是被性别化的。凝视的权力要穿透这些难以驾驭的不祥之物,恢复理性的完美控制,从而赋予秩序,消除恐惧。在文学和视觉艺术中有个意象——“黑色的女人”,她是欲望的化身,也是巫婆和魔鬼,她是恐惧、拒斥、欲求的对象, 或者说,正因其是欲求对象,才成为恐惧之源。她集中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对比——光明与黑暗、理性与欲望、高尚与堕落,人们试图通过不断地将她再现出来,而达到掌控她、战胜她的目的。但是正如法农(Franz Fanon)所言,黑人不过是“潜伏在一切白人心中的黑人”, 是西方人将内在于自身的消极价值投射出去时所找到的替罪羊。真正的恐惧之源不是异性或异族,而是人们内心隐秘、堕落的欲望。因此,凝视的权力并未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是半推半就、充满矛盾的。凝视的过程也是投射的过程:把那些内在的恐怖之物投射出去,从而摆脱它们。
处于重重矛盾中的凝视,是西绪福斯式的努力,总不可能到达终点。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指出,尽管达维特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分法使其被奉为英雄主义典范,其作品中却纠结着矛盾的情感:贺拉斯兄弟既是保卫罗马的英雄,也是杀死胞妹的凶手;布鲁图斯既捍卫了罗马的民主,又废除了父子天性。价值判断缺席了,“它展示了人性具有永久的不完整性从而反对自己”。 但这并不等于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在很多情况下,发挥影响的是表象而非实质。达维特的作品虽然充满矛盾,却在一两百年内鼓舞着英雄主义气概。而在一些历史时期,凝视的权力呈现出完整、统一的面貌,为父权和殖民体系提供合法性。矛盾被暂时隐去。事实上,矛盾正是通过隐藏/现身的游戏,推动着历史时期的一次次转型。在那些矛盾隐身的历史时刻,人们便拥有了(临时的)安全感。
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热罗姆及其观众正处在这类历史时刻。资本主义蓬勃兴起,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活力十足,占据了道德正确性的高地;殖民活动处于急遽扩张期,人们对“白人的使命”充满自信。当然,从一开始,矛盾就存在着。1819年,席里柯(Theodore Gericault)借《美杜莎之筏》对法国政府的殖民活动表示质疑;1875年,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也给英国政府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印度的不列颠政府,一个要让自由的人民来依赖的真正的专制政府。” 但这些质疑没有产生实质影响,乐观主义情绪依然处于上风。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性经验史》中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吊诡现象:一方面,在清教徒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对性的监控加强了,另一方面,性话语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爆炸,神奇的是,两者竟能长期共处,共同推动资本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实际上,这是一种借助于力量抗衡来运作的新型权力机制,它的形成有赖于各类矛盾。19世纪发明的性科学,正处于这些矛盾的交错点上。通过“产生出各种种类的性倒错”,性科学让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些性取向异常的患者,而通过患者的坦白和倾听者的分析、解读,这些倒错是可以被治愈的。“坦白”是一个重要仪式,坦白者所经历的是双重过程:承认自己的倒错行为或思想,使他显得异于常人,被关进疗养院或受到监管,但坦白又承诺了重返社会的途径。这个过程伴随着双重焦虑:坦白意味着被驱逐,不坦白则意味着被永远驱逐。无论如何,只有把他者(对社会来说是坦白者,对坦白者来说是其倒错行为或思想)赶走,自我才能重拾完整性。就这样,“坦白”实现了绝对的权力,负责分析和评判的倾听者是权力的代表,“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
当然,我们不应该被这种表面的二元性所迷惑,这个社会之所以不断地要求“倒错”进行坦白,是因为倒错内在于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倾听倒错,是为了逃离内在于自身的倒错,通过分析、评判来摆脱它,将它投射到别处去。显然,坦白者/倾听者这对范畴,和女性/男性、白种人/有色人种一样,都是自我/他者的变体。驱逐他者,如某种袪魔仪式,保障了个体和社会完整性,父权体系、殖民体系、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都非常需要它。凝视的过程就是驱逐他者的过程,因此凝视的权力也运作于坦白仪式中:坦白者和倾听者分别充当了凝视的客体和主体,通过毫不动情地“看”, 阴暗面被投射出去,人们重新站在了道德的坚实大地上。
在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热罗姆的东方主义画作前,人们获得了彻底的释放:既释放了欲望,又释放了道德。因为,既然欲望属于原始、堕落的东方世界,那么凝视它、评判它的西方人,就拥有了道德正确性。欲望图像的不断增长,同时满足了释放和监管欲望的需要,这是此类作品盛行于沙龙的原因。照相机,这种新型工具可看作该时期的凝视之眼的象征:1850年代也是摄影的东方主义时代,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进行了中东壮游,出版摄影集《埃及、努比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德拉克洛瓦在创作中大量地使用照片。由于照相机被看作客观地记录对象的工具,它那冰冷的机械眼就掩盖了背后那双眼睛的主观性,让被再现出来的、充满欲望的东方世界,显得更加可信。
2、矛盾现身:古斯塔夫•莫罗的“莎乐美”
但是,有赖于矛盾来运作的权力机制,天然地包含着消解自身的因素,“一桶弹药可能是无害的,也可能爆炸”。 人们怎么可能既要求矛盾存在,又不容许它时而浮现出来?怎么可能永远站在道德高地上享受欲望呢?正如福柯所言:“(抵抗)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 尽管“革命”的时刻并未立即到来,但那些回响于达维特作品左右的不和谐因素,还是日益突显出来,终于呈现出“真正进退两难的道德境界。”
活跃于19世纪晚期的莫罗(Gustave Moreau),正置身于这个进退两难的窘境。
1876年和1878年,他分别在巴黎的沙龙和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两幅油画《莎乐美》。 画的情调是东方主义的,但显然不属于安格尔的序列。1876年的《莎乐美》中,施洗者圣约翰的头正在显灵,但画面重心却向莎乐美倾斜,她邪恶但充满魅力,令这幅画的价值倾向显得十分可疑。1878年的《莎乐美》中,莎乐美被描绘成一位高贵的东方女神,希罗底更像一尊神像,背景中出现的斯芬克斯则暗示了她们是妖魔而非神祗。莫罗的作品呈现出精神分裂式的矛盾:从语义上来说,莎乐美和希罗底是遭到责罚的(圣约翰被斩首,却借助显灵折磨她们),但画面却屈服于她们的魅力,甚至不惜颠倒了达维特所竭力维护的男性力量/女性柔弱的图式。
莫罗的莎乐美,从属于19世纪末盛行于欧洲的“Femme Fatale(蛇蝎美人)”母题,它表述了对女性的复杂情感:向往与恐惧、赞美与指责。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卡门是最著名的形象,莎乐美的故事也十分流行。 莎乐美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西方文化史上两次重要的“斩首”之一,另一次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珀修斯斩美杜莎。两次斩首的施受关系相反(一次是女性斩男性,一次是男性斩女性),价值取向却类似(珀修斯突出了男性的身体力量,莎乐美突出了男性的道德力量)。19世纪的莎乐美并未颠覆这一价值取向:尽管王尔德(Oscar Wilde)等人倾慕莎乐美的魅力,却无法否认她的邪恶。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次“斩首”的兴趣的普遍性。
19世纪晚期在性别史上是个有趣的时间段。女权运动经过启蒙时期的发展,又得到工业化进程的推动,逐渐知识分子化,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于1848年在纽约州的色内加瀑布市召开了第一次女权大会。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使中产阶级男子能够独力支撑家庭经济,造成了女性回归家庭的要求。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进程其实是彼此关联的:赋闲在家并接受教育的状况,造成了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的兴起、推动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化,后者又进一步提出了女性受教育和参政的要求。但这一状况的影响力不宜被过分高估:该时期也是女性“歇斯底里化”的时期,患有莫名其妙的妇女病的游手好闲的女性形象,在生活与作品中随处可见,她们感情脆弱、神经质,随时随地会晕倒。现在看来,这类形象很不真实,但它产生于真实的社会需求,即“对她们的身体和性进行细致的诊断和治疗”,以便促使她“为自己孩子的健康负责、维持家庭制度和社会礼仪”。 该时期有种围绕着女性的普遍焦虑,在Femme Fatale身上充分展现出来,她们充满致命的魅力,时而激情四射,时而冷酷无情,像精灵一样难以把握,总是令男子遭受挫折,“斩首”象征了这种挫折感。通过一些文学文本,我们可以观察到该时期中产阶级男子的矛盾状况:他们总是处境尴尬,在道德上自相矛盾,总是教导情妇保持纯洁,并为她们的“失贞”哀叹不已,但他们的情妇本身就是妓女,而他们自己则不是已有家室、就是从未打算把情妇娶回家。并非偶然,这些男子的形象总是伴随在Femme Fatale左右。
这种矛盾状况来自一场认同危机。贵族阶层的逐渐边缘化,使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内在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人们试图通过投射来躲避自身的阴暗面,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正是欲望主体。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模糊了,击碎了身份之整体性的幻想。拉康(Jacques Lacan)的主体观可以说明产生认同危机的深层原因。拉康认为,幼儿在6-18个月时,要经历一个“镜像阶段”:通过观看镜中倒影,形成关于自我形象之完整性的认识。这一经历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一、由于幼儿只拥有支离破碎的身体感受,关于完整性的认识便成了永远无法达成的幻想,导致人类欲望的永远无法满足;二、自我是通过与镜像相关的想象而形成的,因此在自我内部天然地包含着他者,幼儿不但把镜像看做自己,还把与自己类似的其他幼儿、甚至身边的事物也看做自己,这就决定了人类是很难将自我和他者区分开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进一步提出:由于认同拿幻想当做理想,每一种认同都注定要失败。 飘忽不定的Femme Fatale和自相矛盾的中产阶级男子,象征地表达了这种认同失败。尽管Femme Fatale看上去特立独行,她们始终是被塑造的客体,她们的激情四射和冷酷无情,产生于、服务于男子的自相矛盾的罗曼蒂克想象,进一步说明了Femme Fatale乃是男性(自我)的认同危机、而非女性(他者)社会地位改变的产物。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等基础范畴是某种独特的权力形式产生的结果”,因此,莫罗的莎乐美不是一场革命,没有建立另一套价值体系,她只是表述了该时期的道德困境,那邪恶与魅力的致命矛盾,只是悬置了判断、带领人们来到某个缺乏清晰规范的中性地带。凝视无法把握她,但她也没有抵制凝视。毕竟,尽管莎乐美如此美丽,谁又能否认她是罪恶的化身?施洗者圣约翰虽然被斩首,他那忧郁的眼睛却依然凝视着。
3、与矛盾共存:马奈、高更
不过,莫罗式的悬置判断,并不是19世纪末表述矛盾的唯一方式,另外两种方式也同样典型:一种来自马奈(Édouard Manet),他(无意识地)逆转了凝视,构成了对社会规范的深刻干扰,因此一度被公众排斥,后来又被尊为现代艺术先驱;另一种来自高更(Paul Gauguin),他利用矛盾来获取成功,但矛盾也将他永远地放逐在欧洲之外。
马奈的《奥林匹亚》是艺术史上最有趣的作品之一。这幅画因惊世骇俗的人物形象而引起了评论界的哗然,因平面化的手法而引发了艺术界的地震,画中人大胆、坦然的目光,又成了女性主义谈论的焦点。
艺术史家们注意到,《奥林匹亚》是“有典可查”的:提香(Tiziano Vecellio)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1538)是其构图来源,马奈对奥林匹亚的描绘,多处暗示着其作为维纳斯的身份。 正是因为自信该画取材于传统题材,马奈才敢在1863年《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者沙龙遭到失败之后,还将该画送交沙龙展的(1865年)。但它依然引来了公众的唾骂,媒体指责它是“怪模怪样的母猩猩”、“下流之极”, 这一切皆导源于模特维多琳•默兰(Victorine Meurent)那大胆地直视公众的目光,巴黎人认为这目光属于一名恬不知耻的妓女。有趣的是,实际上,目光猥亵的恰恰是提香的维纳斯而不是马奈的奥林匹亚:维纳斯舒展四肢的方式、挑逗似地歪斜着的头部、秋波荡漾的眼神,暗示着情事;而奥林匹亚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画外,身体还略显僵硬。那么,是什么使该画遭到“可敬的巴黎人”集体封杀呢?
让我们检视一下此画的构成方式。作为一个故事,《奥林匹亚》有三名主人公:斜靠在床的奥林匹亚、手捧花束的黑女仆、来访的男子(画外)。故事缘起于男子来访,黑女仆手中的鲜花暗示了其存在。按照拉康的分析,性别是根据与阳具的关系(拥有/作为)来建构的,女性没有阳具,她通过“作为”阳具,肉身具化了男性的欲望,因此“女性”本质上是不在场、不存在、缺乏,作用是确认“拥有”阳具的男性主体位置。而在《奥林匹亚》中,关系发生了逆转。这故事起因于男子来访,但男子在画面上不可见,由一束鲜花替代或象征出来。“鲜花”是故事的欲望能指(阳具),一切关联都围绕着它而建构。鲜花并非具有能动性的人,不能执行肯定或否定的动作,因此必定是一件客体。男子“作为”鲜花,便放弃了能动性,与客体认同。拥有选择权的是奥林匹亚,她若有所思地望向画外的眼神,显示了她拥有这种权力。因此在这里,男子变成了“作为”,而奥林匹亚成了“拥有”,由于男子在画面中是不可见的,更加形象化地确认了其“不在场、不存在、缺乏”。性别关系被完全颠倒。这也就是眼神坦率的奥林匹亚在巴黎公众中间引起巨大愤怒的原因。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由鲜花所代表的男子的话语(意义)并非直接到达奥林匹亚,而是经由黑女仆这个中介来传递,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图示来表示该故事的意义传递结构:
实线表示意义传递通路,虚线表示假定的意义传递通路。假定应由男子传递给奥林匹亚的意义,实际上要经过女仆迂回进行。女仆并非透明的介质,因此以她为中介的意义传递是经过变形的。黑女仆捧着鲜花,表明在故事结构里,她与鲜花是一体的,同属能指,需要被传递的意义则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无法实现透明的联结,在女仆的活动过程中,意义不断地迁移和变形。正如拉康所言:“所指在能指下面不断滑移……” 能指不揭示所指,而是在运动中创造意旨,女仆不传递意义,而是创造意义,因此,她才是故事中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她手捧鲜花的动作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欲望能指的鲜花没有能动性,女仆在占有鲜花的霎那,将自身的能动性附着其上,使故事充满了变数。在这个19世纪的巴黎故事中,女仆传话的方式决定着男子能否被接受。
在东方主义画作中,黑女仆的形象很常见,无论在安格尔《土耳其浴室》这类杰作、德格朗尚(Louis-Emile Pinel de Grandchamp)的《东方记忆》这类“东方主义脚注”式的作品、或蓬桑(Edouard Debat-Ponsan)的《按摩》这类平庸之作中,都有黑女仆,她们是沉默而顺从的“他者”,作用是强化异国情调、标识等级制度。《奥林匹亚》显然不同于此。
不过,马奈并非有意颠覆种族关系,相反,他对种族关系的处理延续了欧洲文化的固有框架:右角的黑猫与黑女仆有同构关系,象征着诱惑、私通、女巫、黑夜等消极因素,马奈试图将这类消极因素投射在黑女仆这个种族他者身上,但他对画面的处理溢出了主观预设,导向了相反的结果。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维多琳•默兰,尽管她的面孔成就了马奈的传世成就,并且她本人也是艺术家,但马奈对她并不重视:在马奈遗留的文献中,仅有一处对默兰的记载:一份留在笔记本里的地址,而且把默兰的名字错误地拼成了“默朗(Meuran)”。作为艺术家和模特,她从未受到任何餐会邀请。 在《奥林匹亚》中,马奈是按照爱与美的女神这一传统形象塑造她的,这美好的肉体本想(像提香的维纳斯一样)交付观众细细品尝,这正是他在遭受了《草地上的午餐》的巨大失败之后,敢于将《奥林匹亚》送展的原因。但默兰的形象也溢出了主观预设,颠倒了性别关系,成了对公众的挑衅。
纠结于马奈画中的矛盾,却变成他处理这个时代的矛盾的方式。一生都在争取沙龙认可的马奈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模仿古代大师的画作,总是遭到无情的打击?为什么他不愿把自己看作印象派,却以印象派大师名留青史?“图像总是溢出作者的预设,作品一经诞生,便获取了生命,谋杀了作者。”或者说,“图像打开了一条缝隙,使意义自我生成、不断延异。”这些后结构主义观念,在马奈作品中找到了完美的诠释。
与莫罗不同,马奈面临的不是认同危机,而是紧随着霸权话语的尴尬状况:一种被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用“模拟(mimicry)”来概括的现象。巴巴发现,殖民文化的最大困惑之一是“模拟”,它有两个层面:一是指殖民地行政组织制度对宗主国的模拟;二是指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文化的模拟。模拟就是再现差异,因为:一、当宗主国文化被搬用到殖民地环境中时,其意义必然发生扭曲;二、殖民者一面用“自由、平等、进步、文明”等启蒙理想来证明殖民活动的合法性,用宗主国的语言、文化、价值体系来摧毁当地文化,一面却要求殖民地人民接受统治和奴役,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样制造出来的殖民地“新人”,必然是对殖民者的“模拟”,他说英语、穿西装,面孔却是有色的,扰乱了以语言和肤色为基准的种族秩序。模拟制造出一个“几乎同样但又不同样的差异主体”。 一种“部分在场”,模糊了宗主国的文化和价值,使他者和自我的位置不再确定,消解了一切恒定性,而恒定性正是殖民关系赖以生存的根基。
考察《奥林匹亚》的凝视路线,会发现它是以“模拟”为基础的:黑女仆凝视着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凝视着观众,本应凝视着奥林匹亚的男子,在画面上却缺席了。凝视关系被完全逆转,变成了他者对自我的凝视。当黑女仆开口为男子传话,她传递的话语是似是而非的,她的法语是黑人的法语,是一个种族他者对白人老爷的模拟,注定带有差异。而当巴黎浪子维多琳•默兰扮演维纳斯,她也注定是对“爱与美的女神”的模拟,她的气质、她的身份、她的目光,阻断了与维纳斯相关的色情想象,她在故事中的位置、她的凝视,僭越了男子和观众的位置,造成了深刻的困扰。因此,当《奥林匹亚》与巴黎公众见面,立即引起群情愤怒,而马奈却不明白,他明明模仿了提香的经典作品,为什么倒霉地受到谴责呢?当模仿变成“模拟”,确定性被消解,“差异”浮现出来。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言:当“他者”回敬了一记目光,麻烦便产生了。
如果说马奈无意识地逆转了凝视,给自己制造了麻烦,那么,高更则主动地置身于麻烦中心。
高更是艺术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本人就是矛盾和麻烦的化身。高更是因塔西提系列作品而闻名的,尽管他口口声声自称“野蛮人”,并在《诺阿诺阿》中大肆赞美塔西提的“天真无邪”,艺术史家们还是渐渐认识到:这是高更为了赢取在巴黎艺坛的地位而采取的宣传策略,他拥有狡猾的商人品质,人品也很成问题。真正值得探讨的是他采取这类策略的原因和方式。
高更出走塔西提是局势所迫,他和巴黎的艺术家、批评家搞不好关系,弄得穷困潦倒,总在给妻子的信中抱怨贫穷、劳累的生活,期待在塔西提打个翻身仗:“三年内我将会打赢这一仗,靠了它生活就有了保障。” 从塔西提回来后,他一边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成“野蛮人”,到处出风头,一边忙着写《诺阿诺阿》,用来推广作品。 高更并未立即获得商业成功,但的确引起了公众的兴趣。
塔西提作品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田园牧歌式的塔西提景观,其中又以秀色可餐的塔西提女性为主;二、“哲学作品”, 用图像阐释塔西提文化和宗教,其中杰作如《白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死者的幽灵在注视》。两类作品似乎是不可通约的:前者居高临下地凝视塔西提景观,后者则以求知与理解之心深入塔西提文化。同样的矛盾也存在于《诺阿诺阿》中:一面对塔西提居民的纯朴生活赞不绝口,一面毫不掩饰殖民者的优越感。
高更研究者很容易被这种矛盾性所迷惑,认为它出自矛盾的性格,这种性格差点要了高更的命(1897年底,他曾试图自杀)。但细读《诺阿诺阿》会发现,矛盾并非自发产生,而是苦心经营的成果。
《诺阿诺阿》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是高更的塔西提妻子蒂呼拉(Tehura),二是高更的邻居若特发(Totefa)。两人性别不同,却都是高更的色情对象。蒂呼拉的特点是完全顺服,甚至在被冤枉时也绝不反抗; 若特发则青春无邪,导致高更心里升起了“可怕的想法”。对若特发的描述,是整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高更指责了“将女人……变得不正常”的西方文明,又将无邪的塔西提居民类比禽兽;在赞美塔西提“差别不大……免除了那种危险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性幻想”的两性关系后,紧接着又来了一段狂乱的性幻想,主体是“上了年纪的文明人”,客体是塔西提男青年。 一系列编排得极其紧凑的强烈对比,使文本在挑逗/遮掩的游戏中俘获了读者。文本所使用的策略十分巧妙:对塔西提“天真”状态的赞扬,既维护了文明/野蛮的二元论,又调动了对“东方”的兴趣;以若特发为客体的性幻想,既强化了对“危险”的文明的谴责和对塔西提的赞美,又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最古怪的性幻想。
那么,高更为什么要刻意使用这类矛盾呢?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在高更这个作者身上,从传记学或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研究,便注定要走入歧途。由于高更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关注着作品的接受度,所以在这个案例中,对受众的分析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19世纪末是资产阶级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个体面临认同危机,殖民霸权经受着差异的考验。人们经常谈到这个时期普遍存在着“世纪末情结”,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危机感,甚至导致了一些敏感的诗人自杀。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里程碑式著作《西方的没落》象征性地说明了这种危机感,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因揭示了西方主体(个体、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矛盾,而跻身于该时期最伟大的小说。这一状况使人们认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已达临界点,必须向其他文化寻求新的生命力,而在文学艺术界吹起强烈的“东方风”似乎提供了佐证。
和前一阶段的东方主义相比,该时期的关注点已十分不同。从表象来看,是从关注景观转为关注文化,人们感兴趣的不再是光怪陆离的异国风情,而是独特的文化体系,在视觉艺术中,艺术家也从描绘东方美人转为学习东方艺术手法。 但是,转变尽管十分重要,却不具有根本性,实际上,该时期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并不是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而是一般性的自我反叛。按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观点,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西方文化的特征是反主流,文化精英有意识地挑衅中产阶级道德标准,以致在现代文化史上,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精英与中产阶级大众的对峙。 矛盾似乎不可调和,致使文化精英中间普遍存在着受难意识,神经质的凡•高、狡猾的高更、风度翩翩的塞尚,——不同性格的人,都自视为被社会迫害的天才;有趣的是,中产阶级虽常抱怨现代艺术挑衅了他们的道德和智力,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这些艺术的理解,并付出金钱和时间。
矛盾的张力之大,已至一触即发的险境,但它也是解决矛盾的特殊方式:将矛盾的两极投射给不同的人群,从而将内在于个体的、极端危险的矛盾转化为社会范围内的力量制衡。“借助凝视的力量,通过驱逐他者来保全自我”,这一次,矛盾重重的主流文化成了需要被驱逐的“他者”,但由于它是主流,又不得不同时是“自我”,濒临绝境的主体求助于矛盾,在主流之中扮演边缘,以求暂时从矛盾中脱身。自我和他者的位置不再清晰,不再有明确的价值归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在这个时刻,高更的自我放逐如同一纸檄文,向腐朽的主流文化宣战,因此他成了该时期的文化英雄。
该时期的每个文化精英身上都有个他者,因为该时期的每个读者和观众都在寻找一个他者,那些属于他者的文化,空前地流行开来。不过,寻找他者的最终目的是释放自我:他者毕竟是他者,必须服务于自我、为自我而存在。实际上,该时期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徘徊于赞美与鄙夷、挑逗与遮掩的游戏中。置身于塔西提的高更,有效地利用矛盾赢取了关注。在塔西提,他既完成了自我的去中心化、又完成了自我的中心化,——利用对边缘的强烈需求,闯入了主流的中心。
置身于麻烦的中心,为高更赢取了成功,但也将他抛入了永恒的放逐。因为不论人们怀着何种目的进入他者的语境,他们始终都是进入了,再也无法用大一统的语言来忽略文化差异。不知不觉中,塔西提那些温顺的眼睛,悄悄地带上了凝视的表情:一种来自被凝视者的、飘忽不定的凝视。在短暂地回归巴黎并享受了一段富有的生活之后,高更遭到了爪哇情妇安娜的劫掠,一贫如洗,终老于比塔西提更原始的马克萨斯,用戏剧性的一生,为19世纪末的矛盾及其解决之道做了最精彩的诠释。
结语
从安格尔到高更,西方的眼睛一直占据着凝视的位置,但凝视的眼神已悄然转变。从安格尔的自信,到莫罗的悬而未决,再到马奈的自相矛盾、高更的自我放逐,一个世纪的路程尚未走完,主体却在矛盾中四分五裂。矛盾,改变着西方文化、改变着西方主体、改变着自我/他者的关系。在下一个阶段,对“东方”的热情持续高涨,造就了马蒂斯、达利、毕加索,——整整一个时代的“古怪”天才。这种变化不是“东方”造成的,而产生于西方社会复杂的自体运动,这也就解释了:东方艺术尽管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却始终未能拥有话语权,直到今天,那些声名卓著、“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东方艺术家,还是要等待西方世界的认可。归根结底,对于东方艺术的关注程度,取决于西方文化的阶段性需要,而非东方艺术家的阶段性成就。
如果矛盾始终得不到恰当的解决,也许会让整个西方社会陷入精神崩溃。但是,商业的伟大时代及时到来,洪流般卷走了一切,沉重文化失去了它的沉重,尖锐的差异成了吸引眼球的景观。文化精英和中产阶级一面互相抱怨,一面欢欢喜喜地携手步入艺术市场。天才们的怪诞行径成了精彩的表演,走进屏幕、走上杂志封面、化身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最后落实为价签上的数字。画廊和拍卖行关注当季的成交额,远胜于关注艺术家的肤色和信仰。矛盾仍未解决,但它被忽略了。商业的节奏太快,不容许人们细细反省。后殖民理论家们把我们的时代称为杂交的、多元的、差异化的,但它归根结底是商业的,商业主导了一切,甚至把民族和国家都边缘化了。
这一季的狂欢能持续多久?不得而知。但是矛盾始终还在,人们还在为凝视的权力争吵不休。至于下一季会上演怎样的剧目,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丹尼•卡瓦拉罗,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米歇尔•福柯,佘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弗朗兹•法农,万冰译,《黑皮肤、白面具》,译林出版社2005年
4、朱迪斯•巴特勒,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5、尤尼斯•利普顿,陈品秀译,《化名奥林匹亚——一段女人寻找女人的旅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6、高更,韦白译,《野蛮之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7、詹明信,张旭东编,陈新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
8、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9、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 1994
翟晶(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美术与设计》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