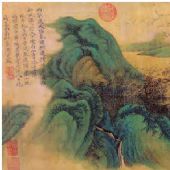序言
空间与缺席,这两个概念是我现在考虑比较多的问题,也是我对常规美术史的反思。常规美术史是关于“在场”的而不是关于“缺席”的。图像、绘画、建筑等都是很具体的,都是在场的。那么为什么要谈缺席呢?因为缺席不但广泛地存在于美术和建筑之中,而且往往决定作品的中心含义。我们需要看到它的逻辑——即创作者有意地把一些东西抽走以强化作品的信息。表现缺席的方式很多,而且在表现方法上自成脉络。因此我们需要挖掘出它们背后的成因以及隐含的思维方式或想象方式。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些例子,可能是绘画或者雕塑,由此提出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在别的比较大尺度的地方。
图1及图2两个作品表现的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西方美术题材——圣经第二十章中的耶稣复活。前一个作品是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著名画作《耶稣复活》,它以叙事的方式把故事表现得很清楚。另外一个作品表现的是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文本,但其中并没有耶稣,也没有基督复活的景象,显示的是耶稣墓葬空空的内部。我们看到墙上有一个方洞,一块石片正往下落。
方洞像是一个窗户,它所传达的信息是隐含的,表现的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即耶稣刚刚复活并已离去。这两个作品表现的是同一个主题,却是两种艺术体验。一个使用了“存在”的表现方法,另一个则是“缺席”的表现方法,但观者都必须事先知道耶稣复活的故事才能理解这些作品。
身体的缺席
另外一个例子是德克•赖纳茨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图3)。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做过很多研究,给集中营的遗址拍了很多照片。有一个摄影师学者曾提出疑问:在这张照片中为什么前面的沙地中不见任何东西生长?因为这个细节能够造成一种“刺痛”感。这张照片并没有直接表现集中营的废墟,但是通过空地——一个没有任何东西生长的死亡之地——可以把主题表现得更为深刻,更使人痛苦!是空地——空就是缺席——引出了更深刻的历史反思。我想大家可以渐渐地看到,当我们看到空或缺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艺术语言,比实在的表现更深刻、更让人反思、更让人想象。“空”不告诉你所表现的是什么,需要你自己去展开,自己去思考:空着的和缺席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作品表现的都是空,都和空间与缺席有关系。虽然每个作品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但其内涵和基本观念是一样的。空椅子是一种对“缺席”的经典表现,在各种艺术传统中均有出现。比如自佛教艺术在印度产生以来,绘画中一个常见的构图就是信徒对着空椅子祈祷(图4),佛陀是由他的“位置”表现的。哥伦比亚当代艺术家桃瑞丝•沙尔塞朵的装置作品总是包括一大堆空椅子(图5),每把椅子都代表一个生命。艺术家隋建国的现场行为艺术和装置作品《开发计划》的诞生背景是北京的城市变化(图6),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被要求拆迁,须在几个月内搬离。有一些同学和教师进行了抗议,用作品展示他们的看法。隋建国在原来上课教室的场地放了一排空椅子,此时的教室已经拆除。另一位艺术家尹秀珍也用空椅子做过装置。1888年,文森特•梵高画了两幅著名的空椅——他自己及他的挚友保罗•高更的椅子(图7)。他也写了这句话:“空椅——有许多空椅,将来还有更多的空椅,早晚除了空椅之外,什么也没有。”有一些空椅子反映死亡,或者很沉痛的东西。在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版画里表现了美国新新监狱里的空电椅(图8),它在1963年终于退役。在这之前,164人在这里渡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这些作品中的椅子实际上是表现“空”的一种语言。为什么古今中外的这些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空椅子的意象呢?原因很简单:椅子的本身已经在其空缺中隐含了主体和与主体的接触,隐含了人体的温度、对人的记忆,甚至是这个人的气息。空椅因此很容易变成一种对历史、对记忆、对灾难、对熟悉的人的记忆载体。除了这些因素是否还有别的?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一位老和尚曾经告诉一位科学家这样一句我很欣赏的话:空不是“空”,空是一种存在。非常对!对空椅子来说,空并不是空,而是一种存在。
作为空间的孔洞
我再举两组例子,说明“孔洞”如何创造新的空间。在中国古代的考古材料中或者美术材料里,实际上都存在很多“洞”。美术史学家一般不太谈这些洞,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是解释有形的图像,其关注的是可以解读的东西。但是“洞”告诉我们一种缺席,或一种空的空间。比如著名的曾侯乙墓有四个墓室,每个墓室的墙上都凿有长方形的洞,外棺上也有一个洞(图9),内棺上画着门窗。这些孔洞和门窗形成一个系统,很可能是为主体准备的。主体可以从这间屋子移动到那间屋子。主体是什么呢?可能是死者灵魂,中国古人是相信灵魂存在的。在这个例子里,洞成为一种艺术或者设计的方式。孔洞的叙事可以放到更大的范围,比如我们研究紫禁城和传统北京城,可以研究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打鼓打钟,如何掌握整个空间的流动。通过研究虚与实的互动,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叙事和理解。
无字碑
最后谈谈无字碑,这又是另一种“缺席”。无字碑是非常奇怪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文字的载体,但没有文字,引人猜测。比如武则天的无字碑,以及绘画中的很多无字碑。在李成和王晓的《读碑窠石图》里(图10),碑前边的行旅者戴笠骑驴,静默地注视着这荒野中的石碑,碑上空空如也。从他与碑的距离看,他不可能真的“读”碑上的文字。那么他在冥想什么?也许是“古今之感”,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相遇。仔细研究这个碑,它非常干净,丝毫没有残破,但每个观者第一眼都觉得它是个古碑。这也是一种感觉,不是绘画的直接表现“古”的感觉更是由周围的树造成的。这张画表现了两重的缺席,首先是字的缺席,然后是意义的缺席。我们找不到碑的确切意义。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吴历的手卷《云白山青图》(图11)。画卷的第一部分非常漂亮,开卷后的景象仿佛桃花源,有开花的树,还有山洞,诱使观者想象渔夫发现乌托邦世界的传说(图11-2)。接着打开画的第二部分,景象一下变得非常荒凉——寒林和昏鸦围绕着一方无字碑,这代表的是明朝遗民心目中的死亡(图11-1)。对于这个无字碑的形象,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来解读。
《礼记》中说后人在祭祀祖先时要“思其居处,思其笑语”,也就是说面对死去祖先的牌位时要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听见他们叹息的声音。牌位是个微型的无字碑,它的目的是通过肖像的缺席让人去构造出被怀念的主体,而不是表现主体的外在相貌。
总之,缺席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其思维方式对今天的景观及建筑设计亦有所启发。
观点与讨论
张旭东①:“空”不仅标记了空间的在场,也暗含一种时间的在场,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引出矛盾,带来故事。这种隐含的叙事性给“空”注入生和死,新与旧、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以及自我与他人间的张力。在表面的寂静和空无下,“空”总是同时间性构成一种具体的、意味深长的关系,换句话说,它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
“空”也不仅是一种抽象,作为一种再现或表现形式,它实际上预设甚至期待一种内容,由此带来了“形式与内容”的新型关系。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白话文和古文的优劣曾引起过很大的争论,一般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古文更高雅、更难;白话文更浅白、更容易。但周作人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古文是很容易学的,只要肯背,一百天内可以学会,因为它有自己的固定的体制,可以脱离实质而存在。白话文反倒很难,因为白话文的形式是空的、不定性的,要有扎实具体鲜活的思想、经验和内容才能填充和赋形。由此看来,“空”是一种有待被具体内容架构起来的形式,它的“没有”暗含着一个新的“有”,是为这个尚未出现的“有”清空的场地。这个“有与无”的关系和上面那个“新与旧”的关系正相对应。
丁宁②:巫教授的观点使我想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建筑的一种很有意思的理解:有一个人赤身裸体在房间中,友人来,问他为什么不穿衣服。他就回答说,房子就是我的裤子,你们干嘛到我的裤子里!可见,建筑的空间可以是一种特别个性化的体验场所。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在1889年,埃菲尔铁塔修建之前,当时反对的人特别多,其中就有莫泊桑。但是,建成以后,莫泊桑天天到铁塔上吃一顿午饭。大家很奇怪,为什么他之前如此反对,现在却天天光顾。他的解释是:你让我去哪里?在巴黎,唯一看不见铁塔的地方就是在这铁塔里。其实,有关空间的感受不仅仅与建筑有关。音乐何尝不是在一个限定的空之中振动、共鸣,才有其生命,即从虚空中产生有意义的音响,这是多么奇妙的现象。除了建筑、音乐,应该还有很多艺术的奥义与空有关。巫鸿教授提到了纪念碑,虽然没有展开论述,却不乏启发意义。林璎的越战纪念碑可谓奇崛,简约到了极点,其中的“空”,即没有任何可以落实的具象,只有抽象和文字,这其中是否也有中国哲学的影响?毕竟她是华裔,潜移默化中会不会有特别的领悟?这个话题如果深入探究下去,将会非常有意思。
王军③:我今天首先想到了老子的话:“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古人对空间的理解,有时候看起来很虚,其实很实,欲识其真义,就得通古人之心。比如,北京旧城的空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紫禁城居中,有人认为这严重阻碍了交通,是极大的缺点。可是,居中而治,其来有自。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什么是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提示的观测二十八宿绕北极的授时之法,又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提供此种服务的天子,是天的使者,必然与天帝对应,天帝居北辰,北辰居中,天子也要居中。在这样的空间里,你天天绕着紫禁城走,虽见不到天子,却无时不感觉到天子的存在,这个空间是很震撼的。只有置身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才能理解此种空间的意义。
李迪华④:顺着几位老师发言,我想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经历。一个是参观美国芝加哥的林肯公园中的睡莲池(图12),乍一看,我强烈感受到了和苏州园林一样的环境氛围。仔细观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低头查看设计细节,很快就能发现睡莲池的设计语言和苏州园林没有任何联系,它所有的单体构筑物都是方方正正的,使用的是现代主义建筑语言。阿尔弗雷德•卡德维尔正是通过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与植物的完美搭配,让像我这样熟悉中国传统园林的人产生了强烈共鸣。另一个是我和北欧设计师们交流的经历,他们都特别擅长利用光线营造建筑的空间感;我曾问他们在进行设计构思时是否想到过教堂体验对其的影响?设计师们都非常坦率地告诉我,没有这么想过,就是单纯在做设计。
所以,我想,今天中国的设计界是否走上了一条尽端路?我们一直强调要挖掘中国传统的设计文化,都在想方设法传承诸如汉唐文化、宋唐文化、明清文化、传统园林文化等,很多人把它们当作现成的设计理论和理念来应用在他们的设计中,太多的设计陈述可以找到这样的主张。中国在过去30多年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建设起来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然而,走进我们的建筑、城市,甚至是苏州这个保存了最传统的园林文化的城市,能够激发出人内心期待已久的传统文化共鸣的设计太稀有了。
巫鸿:我觉得有和无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关系,最美的地方是虚虚实实不断交换,可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是最诗意的。我刚才听了很多发言,每个都不一样,忽然觉得我们在做一个实验,空是一个悖论,已经空了,不需要了,可是我们现在要谈它。空有文字,文字往往是哲学、宗教、诗的载体,这些都不属于我们今天教育中普遍提倡的实证科学,实证科学需要证据、逻辑、推断。空是逃离这些,但是我们今天又要说它。各位都说了很重要的关于虚和实、空和有的理解,这对立的两面缺一不可,现在的学科里可能总是谈论实,但如何才能把虚与实都带到学术里?很难,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无语这种情况,只能用不同的方式一试。
提问:现在北京有四百多处古典园林,被破坏或即将消失的有二百多处,我想问一下“空”包括园林景观的消失吗?如果包括,这应该是一个悲剧。
巫鸿:有一种空是毁灭、毁坏的空,毁坏并不需要表现思想,比如山都没有了,或者雾霾等等。这些事没有声音、没有思想,非创造性的空。但艺术家有的时候可以进行转换,在废墟里做艺术品。
俞孔坚⑤:今天我和巫鸿教授路过圆明园,谈到了废墟,圆明园废墟背后的含义很深,有很多人提议再造,实际上这就失去了“空”间,失去了含义。留了废墟,就是留了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遐想,无限的含义。
提问:请问嘉宾,被破坏的废墟需要的就是维持空的现状?
俞孔坚:空的留存下来才有意义,记录的是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历史,如果加盖和建设,就不能引发遐想。存在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修缮。
巫鸿:一个学校的稻田是空的感觉,可以呼吸。我们的建筑往往都是纪念碑式的,需要观看,空不需要观看,营造的是一种平和。
提问:空可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带有能动性的占有?
巫鸿:我们不能马上锁定空的含义,空椅子是关于将要发生的事,虚位以待,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示已经发生,也可以表示未发生。空并不是给你一个确认的故事、固定的叙事,还有很多是靠谁来看,谁来想。空的意义,恰恰不能马上锁定,一但马上锁定,怎么能发现其他的东西呢?
俞孔坚:非常感谢巫鸿教授的演讲,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从景观专业角度说了很多东西。空和实,这是一个基本语言,景观基本是空间的概念,是具像的表达。巫鸿教授将非常抽象的语言落实到了形象的表达中。由此可以延伸很多,东西方处理空和实的不同方式就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如果比较故宫和凡尔赛两个皇宫,我们可以看到其处理虚和实的方法完全相反。最近国际讲景观都市主义,就是用“空”来定义城市。另外一点,缺席和失去是两个概念,缺席是我设计了一个空,失去是我丢掉了一个实。当年我听巫鸿教授讲桃花源,今天又有了新的体会。桃花源是一个空洞,这个洞仿佛若有若无,如果不去探索,不知道是什么天地。中国很多的传说都描写了葫芦洞,这种孔洞里表面是空,实则是实,包含阡陌纵横,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桃花源才有这么强的艺术感染力,从美术、文字和艺术上营造了空,里面装载了和谐的声音。今天的城市建设恰恰把空填上,丧失了风水。城市、建筑、空间的布局是用虚空间定义实空间,这次的演讲与讨论对我来说收获巨大。
①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研究系教授、中国中心负责人
②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③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历史的峡口》等
④ 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⑤ 俞孔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北京 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注:本文根据巫鸿教授2015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的讲座整理而成。
转载于《景观设计学LAF》2016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