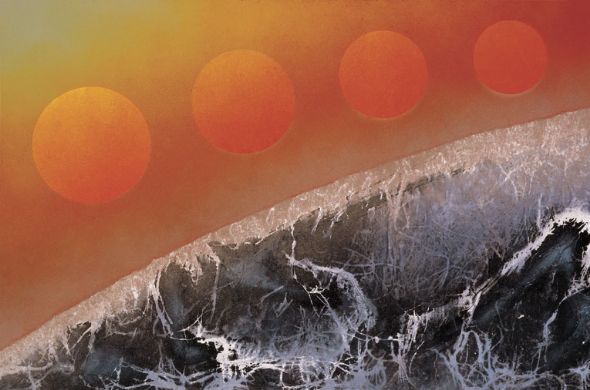
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绘画之发展向为艺术家、评论家、学者所深重关切之议题。[近年来对此类文评之收集整理,以显具成效。如《近代中国美术论集》(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及《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等。]提到现代化又必须正视此一观念之引进与兴盛乃随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而传播至中国,中国艺术现代化也正是因应此西方观念体现于艺术上之发展。虽然论述中不乏本位主义之见,然此亦文化融合再兴之契机。综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发展之大致趋势为强固「民族主义」、「主体性」与接受西方改造中国画两极间之角力与协调。本文以康有为(1858-1927)、黄宾虹(1865-1955)、刘国松(1932-)三位的论点来检视中国绘画现代化半世纪发展之路。这五十年的变化颇巨,随着时代之变迁、地域之不同、与西方各阶段之影响,论者举证逻辑与论述重点亦随之变迁,本文选样意在申论中国绘画二十世纪前期发展之梗慨。
中国绘画衰落论
衰落论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对中国绘画普遍之观点,[此一观点直至近年方为万青力先生质疑,请参万氏《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出版社,2005。]在受帝国主义压迫,深度检讨中国没落的大环境下,这种心态之产生自有其合理性;必须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方得对症下药。二十世纪初期所有的矛头皆指向清初四王以来之发展,间或往前推溯至唐、宋、元文人画之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康、黄与刘三人的见解自不例外。
康有为论曰:「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岂止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余遗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槽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214页。收录于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在康有为的史观中,中国画极盛于宋,衰落则源于唐而始于宋;[请参下文讨论。]而其罪魁祸首是倡导文人画的苏东坡,续之以元四家、文、董、再续之以四王及其余派:「中国自宋前,画皆象形,虽贵气韵生动,而未尝不极尚逼真。画院称界画,实为必然,无可议者,今欧人尤尚之。自东坡谬发高论,以禅品画,谓作画必须似,见与儿童邻,…于是元四家大痴、林云、叔明、仲圭出,以其高士逸笔大发写意之论,而攻院体,尤攻界画。…尽扫汉、晋、六朝、唐、宋之画,而以写胸中邱壑为尚,于是明、清从之。尔来论画之书,皆为写意之说,摈呵写形,界画斥为匠体。群盲同室,呶呶论日,后生摊书学画,皆为所蔽,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背绳墨,不则若犯大不韪,见屏识者。高天厚地,自作画囚,后生既不能人人为高士,岂能自出邱壑?只有涂墨妄偷古人粉本,谬写枯澹之山水及不类之人物、花、鸟而已,若欲令之图建章宫千门百户,或长扬羽猎之千乘万骑,或清明上河之水、陆、舟、车、风俗,则瞠乎阁笔,不知所措。试问近数百年画人名家能作此画不?以举中国画人数百年不能作此画,而惟模山范水,梅、兰、竹、菊,萧条之数笔,则大号曰名家。以此而与欧美人竞,不有如持抬鎗以与五十三生之大砲战乎?盖中国画学之衰,至今为极矣!则不能不追源作俑,以归罪于元四家也。夫元四家皆高士,其画超逸澹远,与禅之大鉴同。即欧人亦自有水粉画、墨画,亦以逸澹开宗,特不尊为正宗,则于画法无害。吾于四家未尝不好之,甚至但以为逸品,不夺唐宋之正法云尔。惟国人陷溺甚深,则不得不大呼以救正之。」[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202-203页。]可见康有为的衰落论乃筑基于脱离写实而趋向写意所造成。
黄宾虹则论曰:「今欧美学者颇知研究方法,以四王为甜俗。」[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19页。]「…近来我国画家虽多,而研究实理,远逊他邦,…茍守陈迹者,只知娄东王烟客、圆照、麓台,虞山石谷为正宗。又不明白其古来所传授之正法何在。无怪为人所轻视。」[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382-383页。]又言:「…今世民权,欲其发达,文艺言论自由,如朝臣院体可置不议,又不可不发扬民学。山林廊庙,皆指学人而言,非应制台阁体也。山林非江湖、市井,此等海外人已能明白。而中国画者沽沽于娄东、虞山、板桥、瘿瓢,陋矣!」[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27页。]于此、黄宾虹以院体(应制台阁体)及职业画家(江湖、市井)皆非中国画之正统之意明矣,而其所谓之〝学人〞之〝古来所传授之正法〞乃力倡〝书画同源〞之文人画,这才是黄宾虹心目中代表民权时代绘画之正宗。依黄宾虹的看法,国画之衰即在此正法之失传矣。
在衰落论上,刘国松与康有为表面上相似,但骨子里全然不同,康氏将衰落的源头指向唐王维、宋苏、黄、米等文人,然尤重元文人画(逸品)对后世之〝不良影响〞。刘国松亦将中国画之衰落追溯至元代的文人画,而衰落之症结在于元代以后文人画所能标榜的只是皴法组合成的绘画符码,此因袭之风为衰落之源:「元代以后就没有看到新的技法的发明,后人最崇拜的黄公望,也只是将前人所创造的披麻皴、矾头皴及米点皴组合得非常好而已。明、清两代的画人,更是推崇古人,模仿古人,根本不知道创作为何物了。一代模仿一代的结果,只注重形式技巧的承传,而失掉原创性的艺术本质,徒具古人躯壳,毫无时代精神。」[刘国松,〝谈水墨画的创作与教学〞,《美育月刊》76(1996/9),页25。]「纵使口叫〝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的石涛,也没有真正的想到丢下笔,而采用其他的方法作画。…六七百年的中国画家,都掉进了文人画的泥沼之中,舍本逐末,不能自拔,完全忘记或根本不知古代大师们创造〝皴法〞的本意。」[刘国松,〝当前中国画的观念问题〞《北京国际水墨画展论文汇编》,北京:中国画研究院,1988,页66。]
二十世纪初期的康、黄两人言论除共同体认中国画学已步入衰落阶段,同时又显露出「西方」在他们的思维运作方式与地位;康有为之思变是欲「与今欧美、日本竞胜,」以图强救国为鹄的;黄宾虹则以「远逊他邦」及「此等海外人已能明白」为警惕,欲驱使中国绘画朝特定之方向发展。这两种论点皆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陷入危机之状态下所产生的,反映出知识分子对图强之希冀与借助西方之观点以巩固自我立论之本意。
二十世纪中期,当刘国松提出他的看法时,台湾的国画界正因在日本殖民刚结束的环境下,特别强调传统国画之价值,藉以复兴中华文化。几所大学美术系都是以中(国画)与西(画)平行但各自发展为常态;而一般学习的态度,不是抄袭国画就是抄袭西画。于国画方面,特别强调师承,透过拟摹以达逼真师长之风格为最上乘;又特别强调〝书画同源〞的文人用笔价值观。而刘国松以此为中国画衰落之主因:「文人参与绘事之后,他们用写字的笔画起画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随后顺理成章的提出〝书画同源〞之说,…以写字的方法来画画,画也可以〝写〞出来。从此以后,文人画家再题款时就变成某某〝写〞了。由于写字又多讲究用中锋,于是到了走火入魔的文人手中,更提出〝不用中锋就写不出好画来!〞的论调。中国画就在文人的〝专政〞之下,一写就写了七八百年,把整个中国绘画的前途〝写〞进了一条死胡同之中,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刘国松,〝现代水墨画发展之我见─并微观当代香港与大陆的水墨画思想〞,《台湾现代美术十年(二)》台北:台北市美术馆,1993,页134。]
三位论者,康有为坚持写实路线、黄宾虹推扬师儒的文人画精神及写意画风、刘国松坚持革文人画的命,推倡抽象。他们各自理出中国绘画衰落之因,也在他们所建立衰落论基础上,康有为、黄宾虹、刘国松展开各自的中国画革新之路。
中国绘画现代化之路
一、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与写实绘画史观之形聚
康有为是书法家,但非画家;故而其画论与画史,不宜从一个「实践者」之角度评论。绘画之为艺于康有为的图强理念中,占有决定性的角色,亦决定了康有为的中国绘画史之性格。有些论者以康有为于一九一七年发表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为他的画论、画史建构之始。其实、康有为的绘画史观早此之前即已形成,这与他非常强烈的科学文化信仰有关,又与他承袭近代「西学中源」、「经世致用」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些原则扣合。总之、中国绘画史是他解决中国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八八二年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途经上海,已惊见「西人治术之有本」。[『康南海自编年谱』,收录于翦伯赞《戊戌变法」》(四),第114、116页。]因而感慨:「我聪明之士,则为诗文无用之学,以其愚下者之学」[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收录于姜义华、吾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37。此引文与下引文顺序颠倒,乃因此文论述之便。]而「泰西特以器艺震天下。」[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收录于姜义华、吾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37。]由此吾辈可以理解康有为提出「欧洲者今世号称文明发生之地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收录于徐高阮辑注『康有为的物质理财救国论』,台北:天下图书公司,1970,第15页。]的见解,是对西方物质科学成就之崇拜,相对反映出对传统文化之不满:「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7页。]
康有为于一九○五年发表《物质救国论》,洋洋洒洒、强调中国所需非革命,而是西方物质文明:「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乎足矣。」及「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于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20页。]而物质之兴,首以画学为重:「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国人视为无用。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以发明之。夫工商之品,实利之用资也;文明之具,虚声之所动也。若画不精,则工品拙劣,难于销流,而理财无从始也。文明之具,亦立国所同竞,而不可以质野立于新世互争之时者也。故画学不可不至精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86页。]在强调工商、工艺与画学之间关联的原则下,康有为开始建构他的中国绘画史,或中、西绘画比较史。
康有为在其《物质救国论》中就已提出后来发展的尊宋院体之雏形:「吾国宋、明制造之品及画院之法亦极精工,比诸万国,实为绝出。吾曾于十一国画院尽见万国之画矣。吾南宋画院之画美矣,惟自明之中叶文、董出,拨弃院画之法,诮为匠手,乃以清微淡远易之。而意大利乃有拉非尔(Raphael,RafaelloSanzio)出焉,创作油画,阴阳景色莫不迫真,于是全欧为之改变旧法而从之。故彼变而日上,我变而日下。今既欲竞争工艺物品,以为理财之本,更不能不师其画法。尤当遣派学生往罗马、佛罗链士画院学之,兼及石刻,师其画法,以更新全国,且令学校人人普习,然后制造工艺百物,乃可与欧美竞销流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86-87页。同时期发表的《意大利游记》(光绪三十一年初版、1905)亦言:“拉(非尔)生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年。基多利腻、拉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之画,有过之无不及也。…故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收录与锺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湖南:岳麓出版社,1985,第134页。)]
从拉非尔的油画康有为得到中国画变革的方向:「拉非尔所画…笔意逸妙,生动之外,更饶秀韵,诚神诣也,宜绝冠欧洲矣,为徘徊不能去。…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亦当派学生到意学之也。」[康有为,「意大利游记」,第132页。]此时期康有为认为油画乃西方之创见,而艺术之至极崇高境界为写形之美。他不但在写实与油画间画上了等号(阴阳景色莫不迫真),并指出中国之与写实背道而驰,实为画学衰败之病源。
准此,康有为在其《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延续并稍事修正十二年前之论述,以绘画尚写实、非逸品的信念,此在其所引证的诸多古例中极其明显;如引《尔雅》:「画,形也」;引《广雅》:「画、类也」即是。[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1页。]又引陆士衡:「存形莫善于画」;引张彦远:「若夫传神阿堵,形像之迫肖云尔,」又自言「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故言:「画以象形类物,界画、着色为主,无能少议之。」「今特矫正之,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主,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庶救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1页。]康有为扬颂界画、院体乃是因为「今之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此则鄙人(康有为)论画之意。以复古为更新,海内识者,当不河汉斯言耶!」[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2页。]这是在以「物质救国」为前提,所规划出的历史轨迹与文化召唤。
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康有为依「西学中源」理论,修正了早期拉非尔创油画之见解,认为油画创发于中国之宋代。这样,一方面更加巩固了他尊宋院体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虽效西法,不失本体;这是中国人不愿屈服于〝戎、狄〞的权宜之计与辩证法则。「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一转成「复古为更新」、「西学中源」。康有为论曰:「画至于五代,而新开精深华妙之体。至宋人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争奇竞新,甚且以之试士,此则将今欧美之重物质,尚未及之。吾遍游欧美各国,频观于其画院,考其十五纪前之画,无少变化…故论大地万国之画,当十五纪前无有我中国若。…鄙意以为中国之画,亦至宋而后变化至极,非六朝、唐所能及。…故敢谓宋人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之最,后有知者当能证之。吾之搜宋画为考其源流,以令吾国人士知所从事焉!」[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4-195页。]在其所藏宋院画中,康有为认定:「易元吉〈寒梅雀兔图〉立轴绢本,油画逼真,奕奕有神。」[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5页。]其他被康氏标定为油画者还有赵大年的〈雪犬〉册幅、龚吉〈兔〉册、陈公储〈画龙〉等。在列出这批「油画」后,康有为指出:「以上皆油画,国人所少见。…此关中外画学源流,宜久珍藏之。」因之论曰:「油画与欧画全同,乃知油画出自吾中国。吾意马可波罗得中国油画,传至欧洲,而后基多琏腻、拉飞尔乃发之。观欧人画院之画,十五纪前无油画可据。此吾创论,后人当可证明之。即欧人十四纪十三纪有油画,亦在马可波罗后耳。」[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6页。]
为了强化他的写实主义观,康有为在清画史中找到类似拉非尔,足启中兴画学重任之人,那就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在清廷活跃的传教士郎士宁(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郎士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士宁为太祖矣。若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214页。
]由此、康有为期盼中国画学回归到他认为光辉灿烂的宋代写实主义。
画学在康有为的改革理想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一个层次上看,画学是「物质救国」图强之最根本基础;但吾辈又不得不考虑「画学」与「君主立宪」体制间的关系。康有为提出「物质救国」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巩固「君主立宪」的思辩逻辑,以对抗「革命」思潮。他大声疾呼,强调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必须发展工商。虽然康有为并没有明确、并直接把他的画学思想与他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但他推崇宋院体,兼及明院画,又提出在清廷活跃之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画风足为复兴画学之基础;把中国绘画史上三个在院体绘画上很有成就的朝代整合为一而论之,与他巩固「君学」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故吾辈不得不注意到「君学」与「院体」之间接关系。简言之、透过画史之重建,康有为意图以绘画为工商之本,走向全面资本主义路线,从而巩固其「君主立宪」理想,以期中国免于革命之宿命。从康有为的倡立宪、崇院画、重物质、尚写实、西学中源等取向和黄宾虹的倡民学、崇文人画、重精神、尚写意、东学西渐的取向,可窥得二十世纪初中国绘画史建构的两个极端发展。
二、黄宾虹「民学合道」写意绘画观与文人画
黄宾虹的画论与画史从民主共和的角度发挥,充分显现了梁启超史界革命论的影响。黄宾虹发表过有关「民学」绘画观的论述诸多,时而以西方人研究取向作为论证的依据,时而引古文献论述。[黄宾虹曾转述过一个西方学者研究之重点:「这里我讲一讲某欧洲女士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画的故事,她研究中国画的理论,并有着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未到中国之前,曾经先到欧洲各国的博物馆,看遍了各国所存的中国画,然后到中国来,希望能看到更重要的东西。于是先到北京看古画,看过故宫画后,经人介绍,又看了北京画家的收藏,然后回到上海,又得机会看过一位闻人的收藏。结果,她表示并不满意,她还没有看到她想看的东西。原来她所要看的画,是要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画,是民学的;而她所见到的,则宫殿院体画居多,没有看到真正民间的画。这些画和她研究的中国画理论,不甚符合。所以,她不能表示满意。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欧美人努力的方向,而同时也正是我们自己应该特别致力的地方。」请参『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50页。]在这里吾辈可以清楚看出黄宾虹以「民学」反「君学」的辩证逻辑。
一九四八年演讲『国画之民学』时,以口语方式阐述〝民间画〞的历史背景:「我国号称中华民国,现又为民主时代,所以说〝民为邦本〞…所谓〝民学〞,乃是对〝君学〞以及〝宗教〞而言。在最早的时候,绘画以宗教画居多…再后,君学统治一切,绘画必须为宗庙、朝廷之服务,以为政治作宣扬,又有旗帜衣冠上的绘彩,后来的朝臣院体之类。君学自黄帝起,以至三代;民学则自东周孔子时代始。…诸子百家着书之说,竞相辩难,遂有了各人自己的学说,成为大观。」[『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48页。]「师儒们传道设教,人民乃有自由学习和自由发挥言论的机会权力。这种精神,便是〝民学〞的精神,其结果遂造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49页。]黄宾虹界定民学之画学的性格为师儒–即是士大夫阶级的画:「汉、唐、有宋之学,皆〝君学〞而已。画院待诏之臣,一代之间,恒千百计。含毫吮墨,匍伏而前,唯一人之爱憎是视,岂不可兴浩叹!…至李思训、王维,遂开南北两宗,而北宗独为院画所师法。宋宣和中,建五岳观,大集天下画史,如进士科,下题抡选,应诏者至数百人,多不称旨。夫以数百人之学诣,持衡于一人意旨之间,则幸进者必多阿谀取容,恬不为耻,不怪乎院画之不足为人珍重之也。」[『论中国艺术之将来』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8页。]黄宾虹的〝民学〞哲学观鄙视〝院体〞的艺术性,而辩院体为「唯一人之爱憎是视」而「幸进者必多阿谀取容,恬不为耻。」成为一种卑鄙人品之艺术,相形之下他高举文人画乃人品洁操之体现,二者之高下,乃天壤之别。
从〝民学〞到〝道〞,再到艺术接近自然与体现人品,黄宾虹提出他的师儒(文人)文化观:「故国家之盛衰,必视文化,文化之高尚,尤重作风。艺进于道,良有以也。稽之古先士夫,多文晓画。」[『精神重于物质说』,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15页。]由于〝艺〞成为一精神之象征、道之体现,故已非〝常形〞所能含容。由此,黄宾虹发展出〝民学之画学〞必为〝写意〞之定则,他说:「古先士夫…言论相同,皆无取于形象位置,彩色瑕疵,亦深戒夫多用己意,随手茍简,而唯赏其奥理冥照,以倡玄趣,极其自然之妙。其说可略举之。欧阳脩论鉴画曰:〝高下向背,远近重复,皆画工之艺。〞苏轼论画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至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黄庭坚曰:〝余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画知其巧拙。〞米友仁曰:〝言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每于静室僧跌,忌怪万虑,心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由此观之,一切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外露巧密者,世所为工,而深于画者,恒鄙夷之,而唯求影响;粗犷不雅者,尤宜摈斥;即束于绳矩,稍涉畦畛,亦步亦趋,自限凡庸,皆非至艺。」[『精神重于物质说』,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15,16页。]简言之,〝民学〞之画学着重内涵,黄宾虹以之区别〝君学〞之艺术:「君学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所以,君学的美术,祇讲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的意味。」[『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51页。]很明显地,能够代表中国绘画精华之写意画者,非文人画莫属,而其理由在于学识、人品与笔墨。黄宾虹在其『中国名画变迁说』中再度强调:「自唐至宋,其得名者,类非画家者流,而多出于搢绅士夫。赵子昂论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皆与物传神,各尽其妙。盖唯士夫之画,本源深厚,胸次清旷,能具笔墨之长,不斤斤于形似者为可贵。」[此篇未收录于《黄宾虹文集》;请参王秀中《黄宾虹年谱》,第299,300页。]
文人画的超越性从〝民学〞优于〝君学〞、从〝精神〞优于〝物质〞、从〝写意〞优于〝写实〞、从〝士夫〞优于〝画工〞的比较,都可显示黄宾虹的史观轨迹。他最终还要解决的是「民族性」与「合时性」的问题。就「民族性」而言,文人画已有千年之历史,其「合时性」必须经得起考验。在此、吾辈发现黄宾虹也采用了「西学中源」的逻辑,合理化了「民族性」的「现代」性格。这一思辩的基础,完全是由绘画形式比较达成。前此,美国的白鲁斯(EdwardBrightBruce)早于一九二五年已提出西方后期印象派即是受东方精神之刺激而成,开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重要之一章:「欧美经东方及己国之先哲之影响,盖已在美术及精神上得有觉悟矣。赛尚、凡高、高庚及现代之美术家方醉心于审美及思想,盖得自东方也。吾辈现方着手研究中国美术,欲采(探)求其思想之根源,方在萌芽。研究中国之美术,可以使吾辈得生命之新观察与理会,盖可断言。」[此文由王雪帆翻译,刊于1926年『艺观』杂志第一集。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173页。]白鲁斯在华期间曾求教于黄宾虹,或许也曾对黄表达过类似看法。一九三○年法人马古烈在中国亦提出:「中国画法向主写意,西洋画法前皆主写实,以像真为能。迨摄术发明后,始悟写实非美术之究竟,渐知写意之可贵。故欧洲今日之艺术渐趋中国化。」[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253页。]这契合了黄宾虹的见解:「迩年欧美重视东方文化,于图画犹加意,盖以欧画境界如我六朝唐人,神形俱肖,刻划极矣。今悟文人乐事,虚处求实,唯崇逸品。」[「与陈中凡书」,未收录于《黄宾虹文集》,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474页。在「与鲍君白书」中又言:「欧美近悟形似之非,趋向中国逸品。」(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364页。)]在一九三四年发表之『中国艺术之将来』中,黄宾虹更用笔墨比较中国文人画与西方现代画类同发展趋势:「自古南宗,祖述王维,画用水墨,一变丹青之旧,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六法之中,此为最上。…泰西绘画亦由印象而谈抽象,因积点而事线条。艺力即臻,渐与东方契合。」[『论中国艺术之将来』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10,11页。]对特别强调笔墨而排斥界画及设色的黄宾虹来说,比较东西方笔墨之相似性强化了他的画论之「合时性」,进而巩固文人画之「现代性」的辩证。虽然直接引用了如「印象」与「抽象」之类的西方现代艺术术语,黄宾虹还是认为中国画当属「写意」。
黄宾虹的友人及学生亦常作类似比较,藉以显现黄宾虹艺术的「现代性」。如傅雷就以后期印象派的画风与中国文人与黄宾虹的作品较之:「先生所述董、巨两家画笔,愚见大可借以说明吾公手法,且亦与前世纪末页(叶)西洋印象派面目类似,彼以分析日光变化色彩成份,而悟得明暗错杂之理,乃废弃呆板之光暗法(如吾国画家上白下黑之画石法一类),而致力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之表现。…近视几无物象可寻,唯远观始景物粲然。五光十色,蔚为奇观,变化浮动,达于极点。凡此种种,与董北苑一派及吾公旨趣所归,似有异途同归之妙。…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中画之说,以西洋之槽粕(西洋画家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无如真理澌灭,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也。」[「傅雷书」: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447页。]文中所指涉当是康有为及其所影响之一派如徐悲鸿的画风改革论。
二十世纪初期康有为与黄宾虹因为政治观念差异,所演绎出的绘画史也各执己见。康氏以绘画为工商发达之本,故以写实为基础,以院画为正宗;而工商之发达,不但可以与西方及日本竞争,又可保君主立宪之制。黄宾虹以〝民学〞为本,强调中国绘画之精神在于师儒所创立之文人写意画,以其为国粹派健将之身分,力主文人画优于院体及职业绘画之史观。
三、刘国松的「自由主义」抽象绘画观
康有为推崇院体〝写实〞,黄宾虹特重文人〝写意〞,各以之为中国画之精华与改革之方向,于二十世纪初期为中国绘画现代化提出发展之蓝本与传统之根源。刘国松则视〝写实〞与〝写意〞为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前面两个阶段,而坚信世界艺术史循着一个三部曲逻辑发展:「无论中国或西洋美术史的发展,都是走着同一条道路。那就是由工笔(写实)经过写意而走向抽象意境的自由表现。换句话说,整个的美术史,也就是艺术家为了争取表现自由的奋斗史。」[刘国松,〝由中西绘画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现代画家应走的方向〞,《新亚艺术》9/10(1972/7),页12。另外、他又强调「我现在不是站在一个美术史家的立场来看,而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一直认为,中国绘画在表现意识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工笔的写实时期,二是变形的写意时期,三是抽象观念的自由表现的时代。」(刘国松,〝回顾过去‧开创未来〞,《明报月刊》261(1985/9),页89。)]在五十年代台湾捍卫传统文化保守路线之当下,刘国松强调开放、追求与肯定自我之路线:「中国并非一个保守的国家,目前的现象仅是几位思想狭隘目光近视的〝权威〞所造成的,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在文化思想上,中国是一个兼容并包溶化力甚强的国家。」[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18。]刘国松体验现代艺术家必须循着自由主义超国界的跨文化领域发展:「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国与西洋两重传统之冲击下,〝我〞是中西文化的混合体,要寻找自我,必须以世界现代的眼睛剖析自己;要表现自我,必须藉东、西传统之精神力量支撑我们。想要创建新的艺术,不是时髦的西方画的追随,而必须先具有正确的认识与坚定的立场。」[刘国松,〝评介十届南美展〞,《联合报》:1962/7/16。]因为「一味跟随着西洋现代的风格形式,亦失去自己,我们既非古时之中国人,亦非现代的西方人。」[刘国松,〝中国现代画的路‧序〞,台北:文星,1965,页3-4。]
然就一个中国艺术家个人发展而言,刘国松还是认为必须体认兼顾传统与融合之必要:「一个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尽量吸收他民族文化,造成一个崭新的时代风格,如此生生不已。中国绘画的历史也是一样,最明显的是佛教输入后在绘画上所产生的变化。…这种实证,推论到现代西方文化的直接输入中国,而且在思想上已经激起了极大浪花的今日,中国绘画的环境已变迁的这个时代,眼看横在中西绘画之间的那条鸿沟,我们会发生怎样的感想呢?」[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18。]刘国松自言:「创作必须通过传统中才能领悟中国绘画不变的民族本质,并且要通过西洋传统才能悟解世界艺术中不变的人性,同时我们必须吸取世界各地的优点为自己的养分。」(neednote)从他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刘国松与康有为、黄宾虹相似之处在于藉西方艺术发展之现况,回溯中国绘画之源流,以建立艺术史之体系及个人创作之根源,只是他们所选择的根源不同。
对〝写实〞、〝写意〞、〝抽象〞三部曲的发展过程,刘国松从画史中耙梳出其源流,然他所认定的「写意画」与黄宾虹之定义大相迳庭,黄氏以「书画同源」的文人笔墨论为出发点,刘国松则认为狂草之类或侧锋的笔墨才合乎时代精神,[请参以下讨论。]且视在元代就被文人鄙弃的泼墨、减笔(后人所称禅画)为正宗:「写意画最早崛起于中国画坛是唐朝的事,根据史书的记载,首先舍弃写实而创见写意画风的是王洽的泼墨。后来继承王洽写意精神的是北宋的米芾…与南宋的梁楷。在理论上有苏东坡的〝绘画以形式,见与儿童邻〞;欧阳文忠的〝古画画意不画形,没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画家既尚真理,反对形似,遂各求自我之性灵心神,于是形象笔墨之外,忠实地以内心的感觉来表现对象的神趣。」[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20。]又说:「王维却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创造性画家,他反对传统的勾勒填色,并试验发明了一种以水破墨的技法,创造了〝水墨渲淡〞的画风,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次空前的革命。」[刘国松,〝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专题演讲专辑(二)》,台中:台湾省立美术馆,1995,页104。]无论是王维或王洽,无论是破墨或泼墨,刘国松将中国绘画第二阶段发展的时间锁定在唐代。与西方比较之下,刘国松认为「在欧洲义大利的文艺复兴尚未开始之前,中国的艺术思想的发展,已达到注重艺术家的个人心灵的表现了。…迈入了美术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在十三世纪初就画出了世界上级极少数几张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泼墨仙人》的梁楷。…他在宋朝时已将中国的绘画史推展到了第二阶段的末期。…在西方一直要到了二十世纪初,由法国在野兽派与德国的表现派的作品中才开始看到。但这两者之间却相差将近七世纪之久。」[刘国松,〝认清并把握住绘画发展的方向〞,《中华文化复兴月刊》4/5,页16。]刘认为西方:「绘画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印象派的画家们已经自觉画家不应完全受自然的支配,在创作时应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于是倡导绘画中要有〝个性〞,奠定了现代崇尚个性的绘画基础。二十世纪以降,无论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以及超现实派的画家,早已意识到自然〝形〞已无法表现今日的敏感的人心与日趋繁杂的社会,无不极力在摆脱以往一贯的具象形式,以求得画家本身在创作上与观者在欣赏上较大的自由。我们必须承认某种特殊的思想、意境、感觉或复杂的情绪,非具象绘画可以表达的。」[刘国松,〝现代绘画的本质问题─兼答方其先生〞,《笔汇》1/129(1960/4),页17。]
在刘国松的观念中,虽然中国绘画在世界绘画史上遥遥领先了七世纪,最终「西洋受了文化交流的恩惠,而吸取中国绘画的优点,放弃了以往那种客观的写实作风,变为写意的现代画,并进而发展至抽象世界的表现,使其本来落后的绘画一跃为遥遥领先,已远远地跑在我们前面去了。」[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19。]刘国松注意到西方受中国影响的辉煌成果,他并提出:「有一些抽象画家是由中国古代文字与草书中获得灵感与抽象形式及线条,并窃欲表现一种力量、一种感情冲动。在法国有哈同(HansHartung)、马松(AhdreMasson);在纽约有帕洛克(JacksonPollock)、克兰因(FranzKline)、杜库宁(WilliamdeKoonling)…形成一股很强的力量,世人称后者为纽约画派,他们自称为〝抽象表现派〞(AbstractExpressionism),此派不但在美国很有势力,就是在国际画坛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刘国松,〝近代绘画发展的趋势〞,《笔汇》1/12(1960/10),页10。]
照刘国松的逻辑推论,要赶上西方,中国画势必朝向第三阶段(即〝抽象〞)发展。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抽象艺术中出现了诸如「行动艺术」、「自动性技巧」、「即兴艺术」等名词,都在强调艺术的自动与偶发性,以艺术的纯粹性与抽象性强调与自然脱节形成独立自主的艺术形式,也是艺术家争脱被自然控制的自由表现。本其〝西学中源〞的信念,刘国松也从历史上找寻中国艺术类似发展之轨迹。他提出:「王维…试验发明了一种以水破墨的技法,创造了〝水墨渲淡〞的画风,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次空前的革命。随后更有张璪与王墨的继续发展,更发明了泼墨的方法,可谓是世界上行动绘画派和自动性技巧的开山始祖。」[刘国松,〝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专题演讲专辑(二)》,台中:台湾省立美术馆,1995,页104。]他又引清朝方薰《山静居画论》而言:「〝画有欲作墨本而竟至刷色,而至刷重色,盖其间势有所不得不然耳。沈灏尝语人曰:‵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正可为知者道也。′仆亦谓作画起首布局,却似博奕,随势生机,随机应变。〞由此可见,中国绘画的观念和理论,是最合乎现代精神。」[刘国松,〝绘画的峡谷─从十五届全省美展国画部说起〞,《文星》7/3(1961/1),页29。]刘国松认为根绝中国画因公式化而没落之途,就必须采用此种即兴法则:「中国画的没落是与走入公式化是分不开的,走入公式化与胸有成竹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针对这一现象,我提出〝画若布奕〞的理念以更新的创作思想。画画应该像下棋一样,走一步算一步,随机应变。不应该还没有画就已经知道结果了。那样的画一定板,不可能活,更谈不上生动了。」[刘国松,,〝谈水墨画的创作与教学〞,《美育月刊》76(1996/9),页25-26。]从这些〝即兴〞、〝偶发〞、〝自动〞的观念,刘国松对〝书画同源〞也有了新的体验与诠释:「在中国的画家中,宋朝的石恪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因为他画的罗汉,身上的衣纹全是用狂草的笔法画出来的。他这两张罗汉画给我很大的冲击。在以前大家说书法即画法,说以书法入画,但用在画上的书法都是行书、楷书乃至篆书的笔法,这种狂草很少用在画上。…玉涧的画,不算书法入画,应该是比较抽象的侧锋笔法…在北宋的石恪已将狂草的笔法用在画中,为甚幺我们不将这种传统发扬光大,并将它用在抽象画上呢?」[转述于叶维廉,〝与虚实推移,于素材布奕─刘国松的抽象水墨画〞,《艺术家》89(1982/10),页232。]刘国松很清楚地看出狂草与侧锋的抽象潜力,再配合〝行动〞、〝即兴〞、〝自动〞等原则,这是他认为世界绘画第三阶段之必然趋势,也是他的努力方向。
结论
总结康有为,黄宾虹,刘国松对中国绘画史的论述,可从以下几点检讨之:一、三家对中国画史诠释的同与别,二、文人画与禅画在中国历史上的势力消长,三、禅在西方之盛行与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艺术之影响,四、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与刘国松的理论中〝中体西用〞的逻辑,五、安亚兰教授的后传统主义(Post-traditionalism)思维。
三家共同认为中国绘画在二十世纪处于衰落阶段,这是时代的普遍现象。然三者在追溯衰落之源时,显露了他们的史观歧见。康有为因主〝君主立宪〞,又因他以绘画为发展工业之基础,故推崇写实,以宋院画为中国艺术完备之时。他把中国画衰落之罪归于文人画之鼻祖:「惟中国近世以禅入画,自王维作雪里芭蕉始,后人误尊之。苏、米拨弃形似,倡为士气,元明大攻界画为匠笔而摈斥之。…中国既摈画匠,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1页。]追求〝民权〞的黄宾虹以其〝国粹派〞的观点护卫〝文人画〞的传统,以康有为所标榜的院画为非〝民间画〞,而他的〝民间画〞也不接受所谓的〝市井、江湖〞之类的职业画家,只以〝师儒〞所坚持的〝书画同源〞为中国绘画之精华。刘国松与康有为同样反文人画,但康有为把禅与文人画之发展视为因果关系(王维之学雪中芭蕉到苏、米之非形似),而在刘国松的绘画体系中,〝禅画〞是最重要的,他从王维的〝破墨〞到王洽的〝泼墨〞一路向下追溯到石恪的《二祖调心图》、玉涧的侧锋山水画和梁楷的《泼墨仙人》,认定中国绘画至此已达第二阶段之末期,从此因为文人画之专制跋扈以致衰落之命运。
三家论述的症结所在为写实、写意、抽象之别。康有为因主写实,故将禅与文人画混为一谈,这并无可厚非,然其出发点在于批评非写实风格,故对画史上禅与文人间的关系不求甚解,甚而穿凿附会。黄宾虹之挺文人画虽兼引北宋及南宋文人对禅与艺间思想上的关系之论述,然其于艺术风格方面所追求者乃传统〝书画同源〞。元代夏文彦以降已将此类文人风格列居所谓禅画之上,而禅画被评为:〝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又评梁楷之画为〝皆草草、谓之减笔。〞[夏文彦,《图绘宝鉴》(收录于于安澜《画史丛书》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页99、104。)]自此禅画在中国处于劣势,反而在日本大兴其道。夏文彦发表他的谬论时,正是梁楷《泼墨仙人》出现后不久,[现在学界对这张画的意见尚属分歧,本文准于传统说法及刘国松对此画之定位。至于画之真伪与时代问题,与本文之论述无直接关系,在此不多加分析。]也就是刘国松认定文人画专制跋扈之始的时候。从刘国松力主发扬王维、王洽、张璪等一脉相传的破墨与泼墨传统来看,从他提出梁楷与石恪为范本的情形来看,刘国松认为复兴中国画的动力在于回归到中国画原来领先西方的原点,即其所谓第二阶段(写意)末期为出发点。在二十世纪初康有为视〝引禅入画〞为中国绘画衰落之始,黄宾虹援引黄庭坚与米友仁的禅画思想,然未多加发挥。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刘国松把过去被文人画强烈批评,甚至几被遗忘的〝禅画〞提出来作为中国画再生的蓝本。这在当时的台湾画坛,虽为创举,然刘国松之立足点实以国际现代主义为根基。
禅虽源于中国,南宋时期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佛教之一主流。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西方推扬〝禅〞,对西方造成深远影响,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走向东方之路铃木大拙功不可没。刘国松的史观应该是从这里出发,进而追本溯源,理出了中国绘画史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消长与复兴改革之蓝图。然于其史观之建立过程中,亦不乏〝西学中源〞的心态之作祟;其将世界绘画史分三阶段之发展为其一,其于画史中提出中国〝行动〞、〝自动〞、〝即兴〞艺术为其二。
铃木大拙对水墨画几点提示足兹看出他对现代艺术之影响,他反对忠实摹写自然,强调水墨画之重要,深信人类艺术有共通之审美基础:「实际上无论画家如何忠实地提示我们大自然中的物像,我们都无法公正地去评断它。水墨艺术家推论称:为什幺不完全放弃此一企图?还不如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想像力去创造活生生的物象。只要我们所有的人都依属于相同的宇宙,我们的创作就可能展现出某些与我们所称的自然物象一致的东西来。」[节录自曾长生与郭书瑄翻译《禅与现代美术》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
他又对现代艺术提出技法性之启示:「以尽可能的快速时间将灵感转移到纸上,在拖拉线条时要尽可能的迅速,线条越少越好,而在绝对必要时才将之展示出来,不容许深思熟虑,不能擦拭,不得重覆,不能修改,也不能改变形状。画师任由他的画笔在毫无自觉力的情形下移动,如果在毛笔与纸张间出现了任何逻辑与省思,将会使整个效果遭致破坏。…在水墨画中并不主张写实主义,…它所企图的是如何将事物的精神转化到纸上来。因此每一笔触都必须随着生命的脉搏跳动。笔触间要有生命呼吸振动的律动感,那必然是活生生的呈现。」[节录自曾长生与郭书瑄翻译《禅与现代美术》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这些观点不即是〝偶发〞、〝自动〞、〝即兴〞等现代艺术规律之先声吗?我们在刘国松的论述与技法上也看到受这些观点之启发。然而在处理这些技法的观念时,刘国松还是依〝西学中源〞之原则,先在中国画史中确立此些技法的历史渊源,找出其民族性根源,故而采用这些技法兼具维系传统与创新,又合于刘国松认为现代艺术走向第三阶段抽象发展的历史轨迹。
刘国松对理论与史论之着力可能是他那一辈艺术家中最深者,但就风格论,我们发现那一辈从事抽象艺术的画家有一通性,就是在抽象艺术的概念下寻求一种民族的风格,他们未必都接受过传统国画训练或着力于在纸上寻求笔墨意趣,然由他们对心象的诠释所〝塑造〞出的物象中,可以隐约地观察到「山水」之踪影。这些艺术家多属安雅兰教授归类为〝后传统(post-traditionalist)〞的艺术家,我想他们在技法上与在精神上都回归传统,但西方现代主义对他们艺术风格形成的刺激功不可没。以刘国松的作品与观念论,是衔接上梁楷的《泼墨仙人》与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将中国画推向他所谓的第三阶段之发展,鄙弃了康有为(写实)与黄宾虹(写意、文人)的论点。从二十世纪现代艺术史发展而言,刘国松与他同辈艺术家在全球化下一致性的艺术风潮与语汇中,确立了他们各别的风格与地位;然整体论之,他们实在世界画坛上建构了抽象艺术的中国风格。
1.近年来对此类文评之收集整理,以显具成效。如《近代中国美术论集》(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及《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等。
2.此一观点直至近年方为万青力先生质疑,请参万氏《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出版社,2005。
3.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214页。收录于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4.请参下文讨论。
5.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202-203页。
6.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19页。
7.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382-383页。
8.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27页。
9.刘国松,〝谈水墨画的创作与教学〞,《美育月刊》76(1996/9),页25。
10.刘国松,〝当前中国画的观念问题〞《北京国际水墨画展论文汇编》,北京:中国画研究院,1988,页66。
11.刘国松,〝现代水墨画发展之我见─并微观当代香港与大陆的水墨画思想〞,《台湾现代美术十年(二)》台北:台北市美术馆,1993,页134。
12.『康南海自编年谱』,收录于翦伯赞《戊戌变法」》(四),第114、116页。
13.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收录于姜义华、吾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37。此引文与下引文顺序颠倒,乃因此文论述之便。
14.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收录于姜义华、吾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37。
15.康有为『物质救国论』,收录于徐高阮辑注『康有为的物质理财救国论』,台北:天下图书公司,1970,第15页。
16.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7页。
17.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20页。
18.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86页。
19.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第86-87页。同时期发表的《意大利游记》(光绪三十一年初版、1905)亦言:“拉(非尔)生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年。基多利腻、拉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之画,有过之无不及也。…故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收录与锺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湖南:岳麓出版社,1985,第134页。)
20.康有为,「意大利游记」,第132页。
21.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1页。
22.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1页。
23.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2页。
24.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4-195页。
25.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5页。
26.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6页。
27.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214页。
28.黄宾虹曾转述过一个西方学者研究之重点:「这里我讲一讲某欧洲女士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画的故事,她研究中国画的理论,并有着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未到中国之前,曾经先到欧洲各国的博物馆,看遍了各国所存的中国画,然后到中国来,希望能看到更重要的东西。于是先到北京看古画,看过故宫画后,经人介绍,又看了北京画家的收藏,然后回到上海,又得机会看过一位闻人的收藏。结果,她表示并不满意,她还没有看到她想看的东西。原来她所要看的画,是要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画,是民学的;而她所见到的,则宫殿院体画居多,没有看到真正民间的画。这些画和她研究的中国画理论,不甚符合。所以,她不能表示满意。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欧美人努力的方向,而同时也正是我们自己应该特别致力的地方。」请参『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50页。
29.『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48页。
30.『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49页。
31.『论中国艺术之将来』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8页。
32.『精神重于物质说』,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15页。
33.『精神重于物质说』,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15,16页。
34.『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会讲词』,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451页。
35.此篇未收录于《黄宾虹文集》;请参王秀中《黄宾虹年谱》,第299,300页。
36.此文由王雪帆翻译,刊于1926年『艺观』杂志第一集。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173页。
37.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253页。
38.「与陈中凡书」,未收录于《黄宾虹文集》,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474页。在「与鲍君白书」中又言:「欧美近悟形似之非,趋向中国逸品。」(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海书画社,1999,第364页。)
39.『论中国艺术之将来』收录于上海书画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上海书画社,1999,第10,11页。
40.「傅雷书」:转载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第447页。
41.刘国松,〝由中西绘画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现代画家应走的方向〞,《新亚艺术》9/10(1972/7),页12。另外、他又强调「我现在不是站在一个美术史家的立场来看,而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一直认为,中国绘画在表现意识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工笔的写实时期,二是变形的写意时期,三是抽象观念的自由表现的时代。」(刘国松,〝回顾过去‧开创未来〞,《明报月刊》261(1985/9),页89。)
42.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18。
43.刘国松,〝评介十届南美展〞,《联合报》:1962/7/16。
44.刘国松,〝中国现代画的路‧序〞,台北:文星,1965,页3-4。
45.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18。
46.请参以下讨论。
47.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20。
48.刘国松,〝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专题演讲专辑(二)》,台中:台湾省立美术馆,1995,页104。
49.刘国松,〝认清并把握住绘画发展的方向〞,《中华文化复兴月刊》4/5,页16。
50.刘国松,〝现代绘画的本质问题─兼答方其先生〞,《笔汇》1/129(1960/4),页17。
51.刘国松,〝过去、现在、传统〞,《文星》10/5(1962/9),页19。
52.刘国松,〝近代绘画发展的趋势〞,《笔汇》1/12(1960/10),页10。
53.刘国松,〝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专题演讲专辑(二)》,台中:台湾省立美术馆,1995,页104。
54.刘国松,〝绘画的峡谷─从十五届全省美展国画部说起〞,《文星》7/3(1961/1),页29。
55.刘国松,,〝谈水墨画的创作与教学〞,《美育月刊》76(1996/9),页25-26。
56.转述于叶维廉,〝与虚实推移,于素材布奕─刘国松的抽象水墨画〞,《艺术家》89(1982/10),页232。
57.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第191页。
58.夏文彦,《图绘宝鉴》(收录于于安澜《画史丛书》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页99、104。)
59.现在学界对这张画的意见尚属分歧,本文准于传统说法及刘国松对此画之定位。至于画之真伪与时代问题,与本文之论述无直接关系,在此不多加分析。
60.节录自曾长生与郭书瑄翻译《禅与现代美术》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
61.节录自曾长生与郭书瑄翻译《禅与现代美术》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
康乃尔大学潘安仪 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