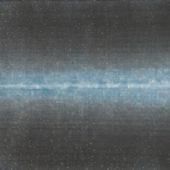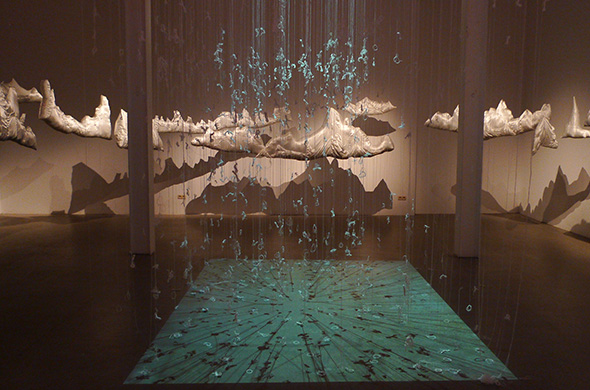
谢谢曹星原老师。这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题目,“论二十世纪文人画(水墨画)的命运”。在以往的艺术史中,20世纪文人画和水墨的论争已经很多了,这个论坛的不同之处是,连线起了21世纪艺术的最近进展,而从1980年代到今天很短的时间序列里,艺术的变化是超大容量的,这不是一个平庸的时代,因为很多问题的发生触及到了“范式”和“界面”的转换。在艺术不断展开其进程的时刻,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再回看一下“20世纪”的水墨历程,将关注的视角回到“命运”这个关键词上,或许会有很多与以往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立、冲突,我们一提不同很容易陷入这种简单化的状态,那也是一种不同,但我这里说提出的不同可能是在“艺术”的界面下,以新的学术的视角,在联系其20世纪和21世纪的“时间连续性”通道中去切入,因为有了“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对“之前”的意义和价值又会有新的认识,这是我所说的不同的前提,也就是“后来”让“之前”可以跳出“当时”而进入到更加连续性的序列当中,去获得我们今天的认识。那么也就出现了两种面对“20世纪”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一种就是在面对中国艺术这个不断发生的语境,从过去的艺术史延伸到今天的文化现场,在二十一世纪的状态下,去看二十世纪文人画或者水墨的命运;还有一种视角就是在我们比较传统学科上的“20世纪美术史研究”的知识的这样一个范畴上,在二十世纪文人画研究或水墨问题的这样一个课题上,去看二十世纪的本身的问题。我的发言是从我个人近来的学术实践,从对当前艺术进程的最新状况的研究,回过头去看“过去”对“今天”的作用,由此会出现对“过去某个事物命运”的与以往的观察视角不同的“命运”讨论。如同论坛设置引言最后提出的,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艺术的进程当中,再看二十世纪他的命运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与一般那些限制在“20世纪里”看问题的要求是不同的,因为回答这个议题就必须对今天的艺术有研究,又要对“20世纪本身”那些学院当中的“普及知识”有所了解,在“已知”的相对稳定部分或者说语境的基本框架后,再根据“后来”已经展开的艺术事实和文化逻辑,在“通”的联系中去看问题,当然会带来新的启发。这就涉及到水墨的命运和二十世纪美术的这样一种现当代转型当中的一种关系。文人画实际上是一个二十世纪以前时代的重要艺术现象,它贯穿了中国历史古典形态中的好几个重要朝代,或者说是在一个传统“社会机制”下“社会运行”环境的综合状态下的一种综合的艺术的现象,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后来又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艺术的“现代性”进程中,在外来文化“西学东渐”的“近现代”框架下在比照中被置入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也曾有不同身份者在特定时代有过很多激进的否定,也有作为“传承者”身份的从事者对其价值的捍卫,后来在逐渐的20世纪“视觉现代性”的进程中导出了一个“水墨”及其不断演化、变形和派生的问题。可能单独谈文人画不需要特别多的了解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放在“水墨”的关键词上,就不能回避21世纪你身边正在发生的艺术界面的转换。把这个讨论的对象了解了,讨论也就不会那么纠结了。如果文人画作为一个概念,与它相对应的有哪些时代当中哪些艺术家、地方画派、时代精神和我们学术上所谈的传统概念当中的一种学术的或者说是传统这样一种道统,比如说南北宗论,或者是哪个时代的文人画家他遥溯了谁谁谁,他从谁谁谁出发,经过了谁谁谁又自成一家,形成了一个上下文人画的传统。这构成了一个传统世界里的“道统”。这种道统,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美术史的研究对象的话,我们的美术史是否对他内在的脉络和他能够支撑起这个概念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家的关系、画派的脉络关系和理论的结点关系,包括作品系统、图像系统都做到位了?是否做了非常充足的学术的基础性研究。这对于我们谈文人画这个概念,基础性研究还任重道远,这可能给美术史学提出了很多机会和可能性。
从文人画这个概念来讲,看二十世纪,实际上二十世纪有文人画的这样一种现象。包括陈师曾先生的创作,包括他对文人画价值的专著,和他针对文人画在那个特定的风雨变革的时代所遭遇的,对其命运展开的种种论争,尤其康、陈等人站在社会革命和改良角度对以“四王”为代表的文人画内涵价值的批判。那么他做了文人画的价值捍卫。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的美术当做不断发展延伸进程中一个段落,再来看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可能二十世纪的美术不光是文人画的这样一个主体,二十世纪美术有他自身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美术从其传统形态到其“近现代”和“现当代”形态的转型。
我认为这里面可能大概分两种状态,一种就是中国的艺术,从它的古典形态到近代形态之后,向“近现代”形态的转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以“新潮美术运动”为代表的艺术界面的转型,实际上带来第二个议题就是在现代美术转型之后,从其现代的形态经过当时的批判精神、文化启蒙和前卫姿态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批评家身份的出现、策展人身份的出现,尤其是艺术形态在方法论和价值指向、文化功能上的“变化”,实际上带来的又是中国艺术从其“近现代形态”向“现当代形态”转型的一种当代转型的界面转换。把二十世纪这样一个美术的完整进程,从一个长线的历史或时间的序列来看,从艺术自身的界面转型、转换,回到“过程当中”,我想实际上谈文人画和水墨的问题,或者谈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这种艺术界面的转换,在社会的文化转型的宏观大背景下发生它的语义变化、功能变化、创作方法和视觉形态变化的一种作为事实的转型,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实曾经是被“学院知识生产”系统所回避的,但是这些年来逐渐开始“解冻”,学院机制的开放带来的也是学院派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开放,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也必然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我后面的讨论将在这个新语境下谈我的一个框架性的描述概念,也就是我近五六年时间投身于身边的当代艺术现场的策展和批评工作,在与艺术家们针对艺术新问题的创作中,和他们一起工作所形成的在“一线研究和策展”工作中所进行的理论表述,也就是我所提出的“水墨的延长线”和我所策划的相关展览,写作、出版等个人实践,然后再就我所看到的一些主流话语机制中的调整,就一些事实与学界分享。
我个人的实践“水墨的延长线”这个问题的抛出,基于的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关于水墨问题的最新进展,这个表述源自20世纪水墨问题的导出,但有新的发展从而超越了“纸本媒介”,客观讲这是“变化”但不是一种“现代主义叙事”意义上的进化论和“文化达尔文主义”的概念,而是一种基于艺术创作与艺术家的工作,在作品这种物质化的载体为见证,在作品的“物事实”基础上可以很清晰看到的一种水墨不断变化的艺术机制。2014年我在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的第三回推出了“来自水墨的新语境”中通过一些艺术家的创作勾勒出了这个关于水墨的新语境,在“实验室”的策展后,我的《实验报告》里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新一步的理论阐述,放在“文化体”在全球化时代的创生机制中,“文化体”和“文化质料”是我为了解释这条“水墨延长线”而采取的解释工具和分析模型,“文化体”是我受物理学经典力学经常采用的“受力分析”的模型分析法启发,“文化质料”是我受亚里士多德的事物生成“四因说”的“形式因”和“质料因”的分析模型启发,而在艺术生成和文化发生的领域采用了“文化体”和“文化质料因”相结合的理论方法,为了分析和叙述“水墨的延长线”的相关问题,那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我出版的《来自水墨的新语境》中有更为体系性的阐释,并且在其中收录的《艺树》杂志就“水墨的延长线”问题的采访中有很多形象式的展开。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就不做过多理论阐发了,大家有兴趣可以从我向论坛主办方提交的书里去查阅。
在艺术史进程当中再去看文人画、水墨画或者中国画、新国画、当代水墨、实验水墨、观念水墨包括我提出的“水墨的延长线”,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一个艺术发生的现场当中去做一个与今天紧密二十一世纪相关,与二十世纪相关,与古代相关的基本的状态,我想这是我的开场白。
在我给论坛提出的发言题目叫“‘水墨的延长线’与‘写意精神’的身份识别”,副标题叫“社会‘文化转型’与艺术‘界面转换’视角下的水墨状态”。可能我刚才的介绍,稍微对这个议题做了题解。去年策划的“来自水墨的新语境”和今年上半年刚新策划的“图像研究室:水墨进程中的一种‘显象逻辑’”,这两个展览合起来基本能够涵盖“水墨的延长线”的基本问题。这是我个人提供的学术视角,属于“延长线”部分。那么我对本次论坛“20世纪文人画(水墨)命运”的“命运问题”的论述除了我个人的学术工作之外,也将我看到的“主流话语”中的“写意精神”的身份识别,从“水墨延长线”和“写意精神”两个21世纪不同维度上的艺术事实来与大家一起讨论20世纪文人画和水墨的命运,因为谈命运除了“20世纪当时的命运”还要看到“20世纪之后”的“21世纪新情况”,“后来”发生的事实对“之前”发生的问题当然带有“命运式”的联系,要谈命运既要看到当时又要看到之后,两者联系起来,我认为才是对“命运”更加完整的讨论。
如果回到一个概括性的基本描述的时间序列,100多年来,在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进程中,“文人画”失去了其传统社会机制下作为画史画论的主导地位,从其命运的论争到其内在价值的争议,从“中国画”、“国画”、“新国画”概念的相继出现到“水墨”语词的广泛使用,社会转型中的民族、国家、媒介的认同机制也在不断促生其“艺术观念”的嬗变,无论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表现式水墨”、“新文人画”、“实验水墨”还是21世纪后出现的以“70后”水墨为代表的被冠之以“新水墨”、“新工笔”的“图像视觉”形态的艺术现象,抑或是“当代艺术”(暂且用这个概念)系统中对“水墨”的跨文化传导,作为一个学术整体变革可以看到如下景观:作为一种媒介,“写意”、“写实”、“形式”、“观念”等不同的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和动力机制在纸本媒介上实现了交互和扩展;作为一种“视觉资源”和“文化观念”,“水墨”作为“文化的质料”已通过当代艺术范式的使用实现了装置、新媒体、架上绘画、行为艺术的“跨媒介”传导和初步的精神辐射。在作品的“物事实”见证下显现的是艺术观念的变化:“水墨的延长线”即体现在创作的方法论和“跨媒介”现象中的“传导机制”,成为从艺术层面理解20世纪到21世纪水墨相关问题的观察视角,尤其在21世纪中国艺术的当代转型进程中发生了“界面转换”,这个界面的转换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与本土“关系方式”的新调整中,“水墨的延长线”作为一个文化逻辑和一种发生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体”在当代艺术界面下的“新常态”,也成为中国艺术全球参与进程中实现不同文明实现相互启迪的战略资源。而21世纪随着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在“艺术质料”储备和“价值对冲”需要下,当代艺术发展和国家文化战略的工作机制开始作用于“水墨”,从艺术现象看,在“水墨的延长线”之外,一种对“民族文化”和“主流价值”的当代体认的识别话语开始运作,从“概括要义”、“意象视觉”、“书写源头”等学理角度重新挖掘“写意”的可能空间,开启了对传统涵义的重新认知和对“中国写意”精神的提倡与纯化诉求。
我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发现近几年在主流话语的机制当中出现了“中国写意”,“写意”与“文人画”的命运是有内在关系的,那么最近这一到两年,主流话语出现了新的概念,叫做“中国写意”。这个概念实际上伴随着很多展览的发生,一方面是在中国本土,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欧洲为主的这样一个对外输出的一个机制。“写意”作为一种创作的观念在西方传播,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身份识别”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跨媒介的展览,有很多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就像这次论坛的引言所提到,包括像朱乃正先生的创作也涉及从油画到水墨的跨界,包括中央美院的老院长,徐悲鸿先生是水陆兼程的,吴作人也涉及水墨。在老一辈的老先生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跨界”。这些都反映了主流话语出现“中国写意”诉求之前艺术生态中的文化土壤。如果细作研究还会发现,很多老一辈艺术家都是跨界的,林风眠及其以后,他的弟子,吴冠中先生在1978年代后,他很多论题的引出,实际上对现代艺术的“形式主义”在水墨现代化当中的作用,在那个时期的创作局面宏实际上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当时非常有待爆破的僵化艺术的格局,林风眠与吴冠中都是跨界的,也就是艺术的创作不存在所谓画种的界限。这种跨界实际上是将“媒介”超越了既有的边界而带入了“艺术”的大视野下。就艺术本身来说“写意”再被提倡,在很多油画、甚至雕塑和纸本的这样一种水墨媒介当中形成了一个我们身边正在进行的对“写意”的综合提倡。那么这种现象对于“文人画”的命运又产生了什么作用,在艺术学、文化学与社会学之间,“写意”和“文人画”的艺术观念对于这个文化共同体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新的情况。
我们同样需要以学术的眼光去思考“写意”所带来艺术观念层面的问题。其实这在学术界特别是从学理上还是需要不断推敲的。从理论上来看,“写意精神”一方面是“写”字,这个“写”可能跟书写性有关,从它的书画同源的源头,“写”这个概念也在当代艺术批评当中被广泛使用,在一些油画的创作当中也经常提到“写”字,画面是“写”出来的。还有一个字叫“意”,这个“意”可能就是跟古典画论当中讲的“意在笔先”的意义相关,或者“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相关。“意”一方面联系到一种人和对象的主客观发生审美关系时候的“意味”,比如花鸟画中的“托物喻情”,山水画中的“造化”与“心源”的关系;“意”还表现为视觉形态的“意象”,与20世纪中国画中的“写实性的视觉”和21世纪70后水墨中的“图像性视觉”不同,是一种“意象”,它也有别于“抽象视觉”。当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出现了“写实的视觉”,我们说它改造了“写意”的视觉获得了一种“造型”的准确和再现的能力,“徐蒋画派”是一个代表,便于中国画进行“现实主义”和“历史性”叙事功能,21世纪又出现了以新水墨为主要说辞的70后这批艺术家,以“图像视觉”作为一种创作水墨的“显象逻辑”,让我们对这之前的一种现象,可以做一种相对的比较和界定,可能就是一种是写实性的中国画视觉,还有就是写意性的中国画“意象视觉”。“意”跟“写”结合,“写意”作为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艺术观念和方法。“写意”,它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高度理解和概括,也有一种“忽略意识”,“写意”在今天的语境中还有“大概”的意思,就是“大概”抓住一个对象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忽略掉那些“不重要的部分”,当然被忽略的重不重要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有一种“写意精神”,很“主要地”、很“流畅地”“写意”了一个对象,或者完成了一个动作,从这个层面上这是对“对象”的一种“流畅而概括”方法论,抓住要义而忽略次要,所一个是“概括要意”,同时还有流畅而精彩地“书写一般”解决问题,这是从方法论层面对“写意”的一种理解。刚才所说的“意象视觉”,是从视觉形态上;还有就是“书写的源头”,是从“写”的这样一个书画同源的上下文当中。
如果回到艺术家的创作那里,我们可以考察“写意精神”是不是也在“跨媒介”地介入到包括油画、版画和雕塑的创作当中,可能艺术家的作品还不是非常典型的或者说对“写意”的这种完善还没有形成一种非常深度的体现,但是在一种问题“度”的层面,可能不同程度在发生,比如朱乃正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件作品叫《青海长云》,我在2000年初的时候跟刘晓东有一次学术对话,从他的口述当中谈到的他的老师朱先生就是一个对传统画论进行深度研究,将传统写意的一些精髓代入到油画创作当中的一位艺术家。他把中国古代画论中微妙的东西“引”入了油画的创作。难道这里面没有写意因素吗?如果我们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可能写意或者文人画中的一些东西正在很多艺术家身上显现跨媒介的转换,比如洪凌、张冬峰、李江峰、许江,……有很多让“写意”沁入“表现”的油画家。当然这里面“写意自觉”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但是艺术家初步具备了一种可以称得上是“写意自觉”的这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绘画机制进入到了新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流话语对“写意”提倡的时候,确实有一批艺术家在追求“写意”的当代表达,这种现象还是值得关注的。对20世纪文人画或者水墨讨论一种命运,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今天是尝试把“水墨问题”和“文人画”分开考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当代艺术中的“水墨的延长线”,这是我个人的学术成果;另一个是主流话语中“写意精神”的提倡及其所带来的在学理上对“写意”的美学和艺术理论问题进行纯化清理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个人的学术工作,我在这个主流现象出现的同时也尝试对“写意”从几个层面提出了我的个人理解,可以说就这个问题是“写意”在主流话语中的再次出现,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引起了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算是一种理论爱好吧。
我个人重点的工作还是在“水墨的延长线”上面,曾经我和北京的一家民营美术馆想联合一些机构在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美术馆合作这么一个全球巡展,当时我做了一个几十位不同艺术家的策展方案,里面有徐冰的装置《背后的故事》和新英文书法,有尚扬的《董其昌计划》、有张方白的综合媒介绘画《鹰》系列,还有刘俐蕴的装置、潘公凯的新媒体《雪夜残荷》,也有张羽的指印水墨,刘庆和、徐累、王彦萍等的当代水墨,还有很多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的大量作品,比如70后图像性视觉机制下的张见、秦艾、徐华翎等。我们把这个方案给了中央美院一位教授去联系北美一家著名美术馆合作(他曾经在那家美术馆工作过),对方看到了我优盘里的策展方案,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合作成功。再后来大家也看到西方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展览,但效果不是特别好。我是2014年在“水墨的延长线”(应该是2011年前后我策划“中国意志”这个油画展之前就有了)这个思路下策划了一个以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为主的中型群展,描述出了这条“延长线”,对“延长的精神”进行了学术提倡,并出了本书进行了些理论出版。这个方向今后我还会再做下去,那么这一个议题的理论方面我就不展开了,因为我想25分钟的时间可能不能做太多的阐述。如果大家对“水墨的延长线”问题感兴趣,无论是纸本层面的方法论的交互扩展,还是跨媒介传导中的“水墨质料”,水墨在这里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文化资源。总结起来“水墨的延长线”所指涉的是一个艺术的新语境,它更多面向的是21世纪以来的艺术问题,其中一个维度是纸本水墨的方法论延长,另一维度是水墨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架上绘画、装置和新媒体艺术中的“跨媒介”传导。“水墨的延长线”是对这条不断延长的学术事实所做的形象化宏观论述。它与20世纪的水墨现场相联,20世纪的“水墨变化机制”(“变化”不同于“进化”)为此起到了“过程”的支撑作用。从这视角出发,如果回到我们的论坛议题要求,在21世纪看20世纪水墨的命运,“水墨的延长线”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20世纪的水墨绝非“穷途末路”,而是成为了一个“变化过程”支撑起了21世纪“水墨的延长线”,这里是“艺术界面”发生了转换,从而获得了充满可能的新的创造场域。
综上所述,回到议题“论20世纪文人画(水墨)的命运”,它的命运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20世纪视角”看20世纪,可能只能给出一些“普及性知识”层面的纠缠,而为什么不在“艺术”的前提下给“水墨”松松绑,如果连线起当代的新场域,一条“水墨发延长线”就在你面前,充满了可能性。二十世纪水墨的命运,不是穷途末路,而恰恰处在一个新的“文化发生”的态势里,处于一种我所讲的“发生性的文化态势”下。如果没有二十世纪水墨现场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没有今天二十一世纪艺术的状态。所以我们对20世纪水墨命运的研究,除了对当时二十世纪特定语境下的艺术历史继续那些重要课题的研究,也需要从一个连通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连续的视角下去回归到“艺术”界面当中,去看它的一个上下文的支撑作用。这是我对“论二十世纪文人画(水墨)命运”论坛参与的一个个人视角,我把这个论坛的议题分开为括号外的“文人画命运”联系到今天主流话语机制中对“写意精神”的提倡,并对括号内的“水墨”带入到“水墨的延长线”的艺术新界面中,一个是我自己参与的当代艺术进程,一个是我看到的现象。社会的“文化转型”与艺术的“界面转换”都摆在那里,当然这是我按照论坛引言要求在21世纪结合我的艺术史研究和当代策展批评实践所立的“一家之言”,有些地方有启迪性,有些可能还不成熟。希望借本次论坛与大家分享我的思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