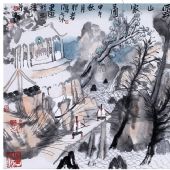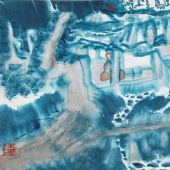笔墨常常会因为自身的执著和气象,往往把生命的笔墨遗失在人生长河大山中的某个角落,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当人翻开自己的口袋,竟发现其中的人性已所剩无几。文化和传承留遗给我们和赋予我们的真实意义,有谁明明白白地使自身的笔墨超越出人自己,象石涛老人说的那样“自脱胎于天地牢笼之手”呢?
有一种境地常常会提醒我们这些藉笔墨为终身职业谋生的教书匠,在白纸上随意地乱涂胡抹,往往比起要参加某类大展前,苦苦地经营那些动静无常的笔墨时,感觉要来的更富于灵性和更具真挚。我们会发现许多地道的让人割舍不去的味道沉浸其中。也许很多人漠视或者忽略这一切现象对创造意识的提示。笔墨所要表达真我的那个境界到底根源于灵性或者还是纯粹的功夫。也有可能有人更赞成两者的交互推演中,某一断面上的某个偶然缺口,正好是其校对目标的最佳抉择。
研究笔墨的,没有不知道黄宾虹老人的。他的艺术,他对传统的造诣,他灵性的光辉,无数的人用无数的语言,无数的文字来无数次地赞叹他。但是他的画,他的笔墨,一言不发,面对着的却是我们每一个搞中国水墨艺术人的心,究竟黄宾虹是靠的什么修炼使这样的一些看似胡乱勾抹的笔墨却能反射人的灵魂,人的内在情思?其中传达给我们的境界,我们说:语言无法形容,文字难以表达。这些笔墨深具内力,使人的灵性与万物与自然的灵性同为一体,很难分开它们单一理论,这些笔墨的奥妙与自然的奥妙一样,无所不在、无奇不有、精深博远、浑厚华滋,这样的大师不简单作画,不是他画到多黑才找到了真我的境界,黑与繁不过是画家的风范与性格崇尚的追求。而把握这些与自然与万物同一体的笔墨,才是洞悉真我的网络和渠道,才是通达解脱的自由大道。
这就像是听一位画家神侃或者拜读他呕心沥血的巨制文集,还不如看他随手的几笔点画、几缕勾皴、几下乘兴未完的小品那样能使我们更充实、更有感觉、更能了解他内在的品质和了解他对自然与自我的整合。
文字的规范和尺度限定了文字本身的有限。笔墨的表达却要比文字复杂和内在得多,肯定一点说,笔墨比文字更接近心灵的真实。领略它的魅力,品味它的韵节,却需要比在文字上浸磨更漫长和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和人生历程。
尝试画一万张笔墨或者画一张地球那么大的笔墨巨作,我们说并不难,只要你能活着不死,就能办到。但笔墨最最困难的恰恰是使我们洒脱出来的笔墨的背后是否真正的具有一片广阔而高远的空间,能使进入的人像你自己追求的那般自由、明澈、返朴归真。
笔墨不应简单地成为描绘我们日常生活万象、万物、自然的外在质地与形象的自然属性。笔墨追索的应该是“那个不可视的世界”。是灵性的雷达,始终捕捉的是心灵的内在的“以心造象”、“以形写神”。
笔墨不应仅仅是形式的外壳,其内边的容量,应为在笔墨的背后留遗出空寂的广漠的余地,予人思情发绪地散步在笔墨的丘壑;才可使造化生于其中,意味方有自出,造诣才可自成。画不在练就多大的能力写出它来,而能用无意的留心使造化在笔墨融合于纸的上面生发出人格与情感的光亮。并使这光亮,亮出人人共有的灵性知觉和觉悟后的智慧。此时的笔墨不应再刻意或者强调,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x像清风,似流水,悠然地从山间走过。坦荡地从看于山巅。如是真正的生命和自在将会使人的视觉摄放造化天地的感悟出,人之初原本具足的宽厚与仁爱,使心灵的内边鸣响出超然于尘世的善良和真挚。纯朴、清净的空间会引领着觉悟了的心一瞬间就扩展出致远的苍茫。只有笔墨超越了笔墨自身,境界才有可能成为我们日常中的平常心。
笔墨的种子一经种下,最佳的期待,就是使每天的浇水、施肥、日照、锄草、松土,都能坦坦地平常心,淡淡地平平然,任天地日月的精华灵气自然而然地造就、呵护、静修、滋养,多残酷、多险恶的风暴寒潮都应顺乎无行有常的四季变迁。多明媚、多灿烂的春光秋阳都应感恩上苍无私的爱予和赐福。
也有的笔墨产地相当的好,品种也不错,风水更是宝地中的宝地,就有一点千万别施用带催效、带激素的化肥,长出来的笔墨果实水分 太大,哪里经得住数万名笔墨专家的真牙利齿地啮嚼。便是果中之王榴莲能臭你个终身不忘,但都不能像石涛老人要求的那样,“于笔墨的混沌中放出光明”。最不幸的就是种下贪心的种子,施的爱和情越多,贪心也越大,执着愈强,贪欲更强。笔墨的萌芽一旦出土,每日必浇的应当是清净之水,施下土的也应该是无为的养料。如果每天只想着如何广告种子的伟大,如何操作策划尚未结果的秧苗,到了秋收,受到伤损的当然是心灵中的那颗艺术的纯净种子,一如善良清净有失,如何于残局中收拾出自己的人性与人格。天真和纯朴也就不再光顾灵性和精神境界的左右。而成为心中幻象的妄求,没有纯净无邪,笔墨的硕果不会生就真纯的品味。
笔墨山水免不了总是要到深山里走一走,看一看。卧游也好,行游也罢,山道蜿蜒间,清潺绕林,烟霞映带携山岚轻轻遥落,秋林涛涌垂暮鼓邈邈幽鸣,兴游不时于忘情处坐下,铺开宣册,划拉一棵歪脖老树,皴半崖系泉危石,走马观花,目识心记,画多了,画累了,走烦了,古大而危挺的老树旁,一经坐下,清凉四面,蝉吟鸟鸣于幽然后闻风声、草声、云声、水声,及至辰时一续,意也连石头,山道远岫层林,千山万壑,天籁地缘莫不音声徐徐,万物灵动之间,心空而神旷,万寂澄然,“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寓于海”。何以人之这般生灵之物竟至在无息无言地万物前顿失了自己。这万物的宇宙 主宰是人还是物质?是物质何以“千山鸟飞绝”处缀“孤翁”一人怡然“独钓”“寒江雪”。是人又如何“孤舟屡失道”却泊“满船空载”后一得“月明归”。孰有、孰无、孰空、孰妙;石涛拓“襟合气度”,张璪观“中得心源”,巨然明“清淡雅逸”,关仝幽“霸桥风雪”,董源赴“平淡天真”,谢赫开“气韵”,虎头妙“传神”,玄宰寂明月四逸“惨淡”,宾虹老人洒墨浓淡老逞太虚境中阴入阳出。这一切之一切,于今见之山水,何同何异,于今画之笔墨何异何同。
写生笔墨,许多人为一个写字奔忙而用心执着,后一个生字,其内在,其分量更较写字高深而无量,生不是简单生活的生,而更应当视为生命的生,万物之生灵之生性之生,大自然创始开天之“太朴”、“心源”之生。得自然一道、得自然大道、得万物一体,就在于对此这一生字的体验和参悟。笔墨的灵性,生命时常在大山的四方漫无企求地漂移,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的太少,钟情之后灵犀耀闪出生命永恒火花的更少。写生笔墨的甘苦也许就是要于偶然的偶然,使笔墨的感觉和灵性与生命自然的灵光一遇这难遇知音的当下,收取笔墨混沌中立现光明的释然。
自然的灵性常驻于山中,万亿千万年了,无声无息,自然的生命却百千万变化,生生不息,任你是人,任你是风晴雨雪、日月天地、任你是四时莫测、地动山摇,每每当人走近它的面前,每每当人投入它的怀抱,人人脉动而紧裹着的心灵,都会立现花的容颜,水的清纯,月的沉静,山的威严。扪心自问,这气象中的气象,出于心、出于手、出于地、出于生命,还是出于自然。
人的灵觉感应就静静地平伏在生命自然的灵界路口,期待着,寂静无声地期待着灵性造化的降临。人手中的毛笔会遭遇许许多多的“山神”“灵仙”,鬼使一般地去企图“神会”,去降伏“会心”,哪个是千古不变之心,哪个又是“造化万物之心”。是自然赋予了灵性,还是灵性赋予了自然。是自然生命期待着心的自然清净,还是自然之心平静了生命自然而然地来临。
不住名相,不生妄心,六根顿失,六觉亡消,不见本心,不知生死,不见无我,大地平沉,十方阔然,朗朗宇宙浩瀚上下无测远近,时空顿逝。人天两忘,空然无一物可视,众妙无一物可得。古人一向把禅和笔墨放在一个平台上谈艺术。这也是画家们的口中从来就不会忘掉这个“禅”字的缘由之一。
禅不可解,禅不可说,禅无形相可揣摩,禅无文字可诠释,她鲜活,她灵动,她无所不在,她超越生与死,她可接引任何一人走上“彼岸”,她可让画家超凡入圣,她也可让画家脱圣入凡。她因人而异,因时空,因地域,因五行阴阳而显现不同的法相和机缘。佛经上讲:“无我相,无众生相,无老者相,无寿者相,故以人相,以众生相,以老者相,以寿者相,以我释迦牟尼相,不能见如来。”
笔墨呢?传承呢?有相吗?有哇。求来的是名相,学来的是画法。传下去的是什么相?是心上之相,还是相外之相?这一瞬间使我想到了齐白石先生的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我齐白石画法和我画的画相似的——死。学我的艺术之道、笔墨之道——生。另有一位齐白石大师的高徒——李可染大师,他是齐派中国画大写意真正具有承传“心印”和“心源”的持有者与继承者,他说:“我不是个天才,我也不是生而知之。我不过是于偶然的条件下,窥到了中国画的堂奥。”
大师从来不把“禅”挂在嘴上,一个“窥”字,使人洞明了“心源”智慧。使悟性必须要在禅上下一番苦功夫之后才能得“窥”中国画的堂奥和“心源”智慧。“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冲出来。”这里的功力应包含至少两大方面,第一,中国画传统,第二,西方艺术。如果只在中国画传统上打下了功夫,那是出不来李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的。这个功夫不是只学自己老师的画法和用笔用墨,而是看清、看明,并“悟道”悟出艺术之众妙之明,见了明,才能看清道,看清笔墨,不是执著于笔墨之外相、画法之外形,用笔用墨的相近古人,而是拆散前人之法、之墨、之用笔,用自己的慧眼、明心智性来把握和洞彻笔墨的相生相克、相克相生,正如古人讲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源是佛家用语,译为智慧,大智、大慧。所谓功夫,只有通达并且融汇了东西方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态和艺术途径,一番博采众长,几十年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上有没有冲出来的勇气。只通达了中国画的传统,这样的画家还有必要冲出来吗?
孤守形图枯笔三十年有余,属于在“傻到家”的梦里被无形无相、似有非无的傻子狠命地“追杀”到当下。想想,原来是傻,现在还在傻中。既然都是千傻,何不同尘和光,痴梦共枕。万一有一日猛醒过来,肯定是畅畅快快地大笑。于是本人正走在山水之梦的山水之间。假的梦里,我不在其中沉醉,真的梦境不在梦中拒绝来回,笔墨的小船沉于梦的流河,梦的流河自由地流出笔墨江海的无形,美得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没事就到老师卢沉先生的家里听他讲中国的笔墨,地道宽广莫测的艺术天堂。我深知只有在此时,我才于梦中醒来,因为我已听到耳畔轰雷般的“狮吼声”就会打开这“梦境”的“天窗”。因为我已经看到醒过来的明白人就站在我的面前。笔墨当随时代不是只随画家生存的那个时代,一个“当”字,是能随所有的时代。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吴昌硕等诸大师们莫不是如此。在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一个时代,拿出来看都能“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