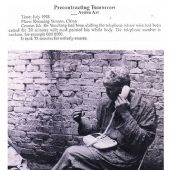如果将行为看作“状态的维持”,它便具有现在进行时的时态特征,是一种进行时态的“存在”。这种“的持续”并不等于状态的不变,周围环境中的种种因素都可以导致状态的改变,但边不变都只是“存在”的表征而已。生命不息,“存在”不止,不同行为体现出不同的“存在”方式。“意义”是一种行为的目的,一种期待中的结果。放弃“意义”即放弃了对目的.结果的追求,也就是放弃了对行为的终极要求,从而使行为在某种程度变得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意义”的自游行为便导致了生命“存在”方式的自由。如果是实施现场行为艺术作品和观者之间的交流是无中介的,那么何云昌以“无意义”的方式提示着生命“存在”方式的自由,同时却在现场直接为观着的“看”和他自己的“体验”之间制造着不同,并继续加剧着这种不同。从这一特点上我推崇何云昌的作品。
何云昌作品中总有一个矛盾如提水-摔跤-对饮,利用这个矛盾他与观者和自己设下不同的圈套。对于观者,开始时他煞有介绍事的准备和架势,为观众制造了期待。随后简单矛盾在被简单重复或延续的过程中变得很无聊,何云昌不注重行为过程中的细节表现,因此观众无法依靠细节获得信息,这使得无聊更无法忍受,在枯燥的无休止地重复或延续中观者的期待被逐渐消解。当行为被终止,其不了了之的无结果使观众彻底失望,至此何云昌将“无意义”象球一样抛给了观者。观众看到不知所以的举动,感到困惑。对于何云昌自己,因为追求行为的无意义而放弃行为结果,过程便成为他对生命“存在”不同状态的体验,也是对“存在”状态的进行时态的阐述。这些特点几乎贯穿在何云昌的全部作品。余观者,看到的是何云昌作品荒唐的英雄主义色彩。早期作品中充满了一个顽童对英雄主义的幻想-参拜和称赞,如《预约明天》《金色阳光》,其中镜子和电话的使用为作品添加了某种象征意味。对环境-色彩及表演状态的控制使作品充满浪漫的主义诗义,单纯而富于幻想。之后《移山》《上海水记》看似愚蠢和荒诞的努力行劲确实让我们想到预言《愚公移山》中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感受到挑战天工的气概。但如他所说,山水依旧。他以严谨必胜的态度-坚韧的完成着毫无意义的行为,透露出堂吉柯得式的荒唐幽默情绪。他心无认的专注及周围无人的自然单纯的环境,使这些作品带有某种超然反世的童话效果。《摔跤1和100》《枪手》《天山外》得作品,在与人与天与地的嬉戏中,除了依然不变的英雄主义色彩外,行为中又添加了游戏成份,对抗性被加重。在其中作品中所有的英雄主义都因行为的“无意义”而变得更荒唐。于何云昌,按自己的方式选择不同的“存在”状态,通过“无意义”的行为突破出生命和意志的存在,在强弱的对峙中增加着恐惧-伤害和孤独的体验和理解。在枯燥-无聊动作的简单重复或眼下的过程中,对体内的挑战随着强度设定的不断增强而被加强,作品的表演成分因此得到有效的压抑。随着强度的增强,自我和身体逐渐分离,身体活动的空间转化为心理乃至精神的生产空间。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在此成为这种转化-市场过程的媒材。如他所说,“随着作品进行,越到后面越残酷,所有的游戏最终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在看似英雄主义般的荒诞和看似游戏般轻松背后,需要顽强的意志抗拒恐惧,建立自信,在生命的消耗过程中体验生命的存在。
何云昌不强调作品的视觉描述,不强调作品的表演性,其作品是简单抽象的。行为作品不可或缺的材料—身体在他的作品中并非再现自我,而被他者化为生命的象征,并从日常生活-社会现实-政治以及经济模式中抽离出来,以同样从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抽象出来的简单矛盾相对抗。在功利时代,人们对行为寄予过多的期待,无意义的行为被视为无效-愚蠢的行动。而期待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远离“存在”方式的自由忘却了自由是生命的一种属性。何云昌作品里的行为因“无意义”被视为无效,由于其方式极近日常,被观者“看”到非常生活化的“无效”,其隐喻性让观众更难以接受。
何云昌以朴素的行为方式为观者着接受的困难,同时以日长化的方式体验着“存在”方式的不同。水泥,是种常见的被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工程中的普通材料,虽质素却拥有截然不同的性能和形态。粉末状松散无形有如灰尘一般被微风吹得无影无踪;和水摻拌后可被浇筑成各种形状,结合其他材料便可构成庞大的建筑,沉重-坚毅又冷酷。迥异的性格和迥异的杂存在方式也许是何云昌偏好水泥并以它为材料的原因吧。《铸》是一件1.4米x1.8米-高3米的水泥体,其留有0.8米x1.2米x2.5米高的空间,何云昌即被浇筑在这水泥钢板形成的狭小空间中,身体被隐却,作品的表演性因此被降低为零。整个作品犹如不透明的琥珀,精工完成,朴素-简单而沉闷-泄重。何云昌将观者“看”的程度降至极限,观者只能看见一个巨大的水泥体,却看不见何云昌本人,无中介的交流也只能通过气息在心理上进行。与此同时,何云昌将自己的“体验”极端化,面对无法以身体抵抗的黑暗-狭小-冰冷-恐惧-无助和孤独,意志成为支持生命存在的唯一力量。在水泥体内生命存在的外部世界的抽象体现以不可见的身体构成矛盾冲突中,身体的对抗小贝极端化,“体验”从身体层面转化为精神的层面。“行为”被彻底“无意义”地置于极端化的狭小空间,是对“存在”方式的又一种自由体验。“存在”超越了任何可视的,物质的矛盾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至此何云昌将其行为作品极少化为无视觉性,无表演性,非物质化,无身体的对抗性,这是艺术家将人生的经验,生存感受转换的结果。如果说艺术家的“体验”是现场观者不能同时感受到的,观者的“看”和艺术家的“体验”之间的不同是必然的,那么通过《铸》何云昌将这种差异进行了极端的处理。我所强调的何云昌作品之特点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也是为《铸》作展览的原因之一。
另外,作为行为作品的图像记录和传播手段的照片或录像,当现场结束之后,便中介于观者和作品之间。这“中介”并非作品本身,它将现场的“看”和现场之后的“读”在视觉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为我们研究“看”和“读”的区别提供了一个相对纯粹的条件。这是我做本次展览的第二个原因。在展览的设计上,我将之分为两个现场棗行为实施现场,观者直接面对正在进行的《铸》:图像展示现场,观者面对中介,即以固定角度的录像现场实施状况转播《铸》,以及何云昌以往作品的图像记录。将现场如此割分以强调两个现场的不同功效,并近一步探究不同现场中观者的“看”和“读”的区别。
唐盺
二零零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