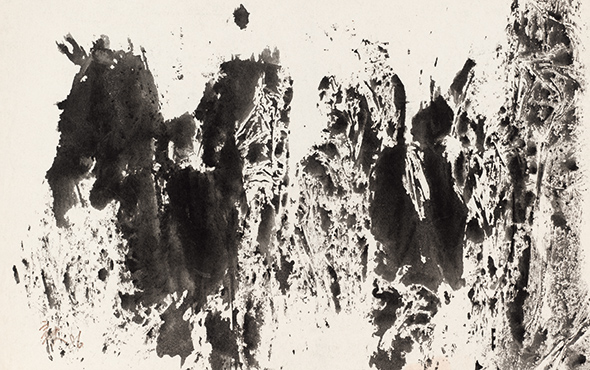
凌叔华女士论《我们怎样看中国画》一文,看完以后觉得极有见地,不过好些地方,我还不能完全同意,索性写在下面,希望凌女士和读者,加以相当的指正。现在分条来讨论:
一、似神气韵
凌女士说:中国画最高的目标是不求形似,是要“画尽意在”,并且引证苏东坡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凌士女的结论是:“形存神亡既不成诗,绘画亦不外乎此理。”
我们以为绘画既是一种模仿艺术或形象艺术,她第一个问题,就是“形的问题”。不过“形的问题”并不简单。“形似”一画一人像人,画狗像狗,画马不要画成驴是绘画里边最初一个阶级。原人、小孩、初学画的人都是在力求形似而不可得的圈子里碰来碰去。到了技巧纯熟的时候 ,假若他一一画家一一想制作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他对于“形”就要另下一番苦功,方能达到造型艺术最高的境界:“之形伟大Grandeur de la formeo 同时有一般人只晓得用纯熟的技巧来死抄自然,结果坏则作出像动物学的插图一类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画些学院派,Academy le, pompier,技巧繁重,趣味索然的画。
“形之伟大”非用眼睛来观察比较具体的例子不能领略,勉强用文字来解释,总嫌隔膜, 姑且分三点来说:
(一)比例
顾恺之《女史箴图》里面的人物,希腊人Eumor fopoulos 藏唐人壁画(现陈列大英博物院),比国人Stoelet 藏唐人《醉道图》(见《文杂学志》第一卷第五期插图)里边人物部分 的比例都十分考究,李龙眠《的林中仙人》(见《文杂学志》同号),至甚于梁楷的 写意人物(见日本审美书院出版《东洋美术大观》),于对人体部分的比例都很留心。他们用锐利的眼光来观察自然,同时脑子里有一种理想的“比例”,觉得有具某种“比例”的人物,才高贵,尊严;他们不夸张人物的形状去求某一种特殊效果,如金冬心、陈老莲这些人1。他们“理想化”人生,同 时接近人生,所以他们的作品格调特高。
(二) 直线曲线得其均衡
中国艺术线条应用的特点,是曲线重于直线,无论雕刻,绘画或装饰艺术2都可以见出中国人富于应用的天才,尤其是用线条组成花纹、图案的天才。中国铜器上的图案最容易看出来。但是中国艺术并不是和回教艺术 Art Musulman一样的纯粹抽象艺术。3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形形色色,不但爱好,甚至于对它们有热情,肯花许多时间去观察、分析,在艺术上想方设法要抓着它们的身体与灵魂,汉唐宋艺术尤其显著。两个相反的成分:“抽象的花纹图案”和“现实主义”Realisme打成一片,产生了不少特殊的珍品来。例如四川渠县汉代沈家碑上的“朱雀”浮雕,全幅极富图案趣味,几条极美的曲线,穿插交错,重复,组织成一个生气泼泼的朱雀。你看他昂首振翼,挺胸前进,多高贵!多尊严!我们仔细看来,觉得全幅最主要的关键在朱雀的右足:因为右足高举前伸,显得一身的力量都放在上边;一幅几乎纯粹图案的作品,幸而右足雕得真切入微,增加不少的生气。全幅都是用曲线组织,唯有右足曲中带直,对照得格外生色。
再如希腊人Eumor fo poulos藏宋人花鸟(在伦敦),十高寸宽八寸 ,比沈家碑的朱雀浮雕硬得多:前者还有古拙Archaicuc风味,这一幅确是艺术发达完成时期的作品。惊人的现实主义!鸟、枝、叶,无一物不是对自然逼得紧紧的。最巧的是,无论各部表现得多么精致,但挂有一点琐碎轻浮的毛病。处处表现出力量来,没有一笔是软的。这是因为不知名的艺术家制图造型的时间,心目中不离开自然;画轮廓时候手下总不离开“形”,除了鸟背用一条极美的曲线外,其他的曲线(例如右边一片反叶和树枝成一弧形)决不用一条无意味的线滑过来,确是时时想到叶子的阴阳向背和直线表示出来。画面没有一条逼直的直线,也没有一条菠圆的曲线,换句话说,没有一条线是抽象的,是离开“形”的。曲直方圆恰到好处,虽然我们觉得它处处有力,但缺乏夸张,做作卖弄的毛病。至于说到小鸟的生气泼泼,树枝树叶的排列交错、变化,更是无懈可击。用伟大的形把自然界的“神秘”“灵魂”活跃跃摄在一幅八寸阔十寸长的小绢上,诚令我们敬服!
再看一幅比国人Stoclet收藏,各国学者公认为赵子昂画的双马(现在北京),我们可以得到同等的满足,不过比起上一幅来,力量已经差一点,虽然还是张难能可贵的东西。
最后看一幅明朝人的东西:就是法国人桂乐莱Culty收藏四十年前他在太原买到的一蝠吕纪画的白鹅(现在巴黎)。这幅画的尺寸比前 两幅大得多:一双白鹅与真物一般大,绢本着色,用粉用得最好,构图造型的谨严不亚于“宋人花鸟”,曲线直线的运用也能得其均衡。假若我们拿一幅边寿民的芦雁来比一比,立刻可以了解什么是“形的伟大”。边氏用没骨画去,水宽宽的,很“吃昧”地快快扫几笔,猛一看来,觉得很“痛快”,但是仔细比较比较,觉得边寺民给我们的只是一点墨色,除此而外,都是“吃昧”,“巧技的卖弄”virtuosite。我们不能因奇爱那一点墨色,那一点“痛快”,把别的更可贵的东西一一形之伟大、构图的紧严、着色等霉一一忽略不理。
(三)形的单纯
“形的单纯”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照真东西的“形”毫无选择死抄下来,也就是不要用无意义的线,无意义的笔墨堆在画面上,造型的时候要抓着真东西的“形”的主要部分,加以洗练,到必要时不妨改变自然形体defor mer以达到某种效果。不过脑子里,或眼睛里要有一个几何形体的观念,要能欣赏单纯的几何形体,要知道自然界最美的人物都无形中为几何形体所支配,否则一昧的“洗练”,或“变形”,极走容入易夸张的魔道里,在造型艺 术里,“形的单纯”是许多大艺术家费尽穷心才作得到的,例如汉人的朱雀的浮雕,云冈石窟最好的佛像,赵子昂的双马,宋人崔白的芦雁都是极好的例子。宋瓷的纯洁高贵,大部分是因为具有这个条件的缘故。
总之,“形”的题问并不简单。从“形似”到“形的伟大”,中间知不道隔了多少阶级。由动物学插图到宋人花鸟的距离,和从茅庐到天坛一样远。中国艺术对于“形”的研究虽不及欧洲|艺术之有系统,中国人对于人体美因为种种的关系不幸而忽略过去,但是我们观察古人的 遗作对于形似不是不讲究,唐人张彦远说“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说得很清楚。“全其骨气”,就是说不仅能画一近似真物的轮廓,还要注意它的骨髓构造;它的生气精神,“立意”,就是在未动笔之先,对于对象的姿态位置一一构图要有一个具体的了解。这些条件都备了,假若动笔的时候对于描法不考究或无研究时,还是画不出好东西来。凌女士所解释张氏的话:“这也就是说虽有物意,用笔若差,也不成画。”拿“物意”(我不懂)来解释“立意”是不确当的。
中国画家在暗中摸索里居然也能作出宋人花鸟白鹅一类的东西来,是多么值得庆幸,值得大书而特书! 凌女士说:“中画国最高的目标,便是要画尽意在。”我们现在要说:“中国画里许多杰作都能得到伟大的形,同时能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灵魂。”、“南齐谢赫的六法是他批评画的标准。“气韵生动”一语几千年来不知道多少人解释、附会,始终没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说。其实谢赫认为六法皆备的名作都没有传下来(顾恺之还列在第二流,《女史箴图》究竟是不是他的真笔,到如今还没有定说)。我们不能看见谢赫批评的对象,想在四个字里附会,解释很难有什么收获。凌女士说:“气韵”就是“神可”以,说也是一种最聪明的注脚。“神”是什么意思?是“神来”之“神”?假若以“神”来代表“精神”,那么我们 可以说:“神”是离开不“形”而存在的,“形”到好了处,“神”随也着来了。宋人花鸟是极好的例。若是只有一个不完整的“形”,它能传的“神”恐怕也有限。
二、用色
凌女士对于用墨用笔说了不少的话,可是对于用色几乎一字不提,这确令人可惊异!凌女士难道以 为中国画里的用色不值得我们研究、欣赏吗? 或者因为凌女士自己太喜欢水墨画而忘记了许多令人爱不释手的着色画?
中国画着色独到之处,在他的装饰趣味和色调的关系le Rapport de ton,因为除了壁画外,用的材料都是比较细软单薄的绢和纸,所以颜色的数目,用色的方法比油画都简单,始终保持装饰趣味,对于选择颜料特别讲究,颜料里加宝石粉就是一例。在色调的关联,更加小心谨慎,极求画面上得到精致、高雅的调合。大英博物院陈列的唐人壁画,用粉绿为主调,配以其他美丽的暖灰色同少许鲜丽的色调,得到圆满的效果。不能到伦敦去看原作的读者,不妨看Lourence Binyon写的关于这些壁画的专书,里边有精美的插图,可以得其大概。比京Stoelet 君收藏唐人《醉道图》全幅处处着色,精致名贵,最令我们钦佩的是画面的白色,细细观察都是有颜色的,或作淡紫,或作淡绿,白色旁边初以石绿、老红及其他暖灰色,调合对照,无美不备,可惜这件东西不容易看到。拿文字来描写颜色是最可笑的,只得对读者抱歉。
中国人对于着色向来是考究的,无论在铜器上,资器上,绘画上,都可看出前人对于色彩 极为敏锐。资器上色彩的千变万化,色调的高雅纯洁,非任何民族所能比拟。为什么现在的人只晓得用粗重,强烈的对照,墨白对衬,甚至于白墙涂上一尺宽的墨边或完全刷黑!建筑上的大红大绿,配以毫无个性、恶劣的灰色。室内装饰,衣物等等的配色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画画的人多半在白纸上大笔枯墨随便刷刷了事,画画变成了一种应酬工具,或者像英国小姐画水彩画的那种态度,同时颜料、纸、绢的制造一天比一天坏,再不回头,真是不可救药!
三、画与诗
唐人山水画传到现在的,我知道日本藏有三幅,曾在东洋美术大观发表,据说两幅是吴 道子画的,不过现在已证明不可靠。还有一幅《飞瀑》,据说是王维画的。日本出版世界美术集第九集 ,印有罗振玉藏前清内府物王维的《雪摸图》,宋徽宗题签,曾见《宣和画谱儿 此画全幅不露空白,雪用粉画成,气味纯厚,能将雪后的寂静充分表现。最奇怪的是这四幅画都没有题诗。王维是位大诗人,并不在他的画上题诗,但是我们看他的画并没有觉得是“憾事”。凌女士也引《芥子园画传》里面的话,说“元人以前多不题诗,写年月名字,都在石隙或 画角不明显的地方”,后来这些自命师承王维的文人画家,为什么不从画面上求充实,为什么”画成之后,兴有未尽,意或未达,题上点东西方才放笔”?一定要人念他们的诗才明白他们的画,这些不在面上用功,不拿画来充分表现他们的“兴”,他们的“意”,把硬画降作文学的姆妾,同时他们又不专从诗上发挥,硬要拿诗来作画的注脚,这种人值得我们佩服,歌颂吗?
想在画中求诗,只可以在画的“形”上求,线条上求,颜色上求,画面整个的生命上求。换句话说,无论用色、用墨、描线,假若能用最经济的手腕,得到最高妙的效果,就可以说它有“诗”的好处,取其广义,例如我们可说:李龙眠是一位“线条诗人”,《画醉道图》那位不知名的曹朝人,是位“颜色诗人”。假若一定要题诗在画上,或将画当作诗的插图才算是“画中有诗”,那么王维的画里面,难道没有诗?徐青藤送人婚礼的画,一罐酒,一枝红梅,上题“佳人才子信有之”,又有什么诗?
我们以为中国山水画到了元末,路已经走完了,后来在技巧上、意境上(除二三人外),已经没有发明新路的可能,只好墨守成法,作剪裁拼凑的生活,后来愈变愈糟,装饰艺术上处处霉画些琐琐碎碎的山水,我国人特长的花纹图案反倒衰微下去,实在是一件大不幸事!
四、工与意
“写意”、“墨戏”、“笔戏”都是工作之暇拿来消遣的。吕纪可以画出大幅《白鹅》,同时他 也能鼓起笔来,随随便便画一只飞鹰(存故宫博物院),但我们批评他的 作品全部时,应该注意他的《白鹅》,因为他在前一张画里把他的学问、技巧、经验都放在里边,后一张不过是一时高兴,笔管儿放放野马而已。梁楷的李太白像固然不坏,但是元人的僧人像更是一张完整、极富个性的“像”。欧洲名画家也有作“写意”一类的东西:Rembradct , Goya, Claude Loira in,诸家的水彩画多令人爱不释手,不过这些人除了水彩画外还留下许多更了不得的油画,他们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后者里边。反之,在我国有毕生专画写意的画家,可怜的是几 十年光阴过去了,没有几件完整的东西留下,可以代表他们的。难道中国画家就没有更大的野心吗?现在画家多半是专工写意的,讲究几十分钟画一张中堂,技巧的卖弄到了这步田地,无怪中国画衰颓下来!
五、余论
在中国文化重新估价的时期,我以为最要紧在勇于认识,放大眼光,客观地研究中国画有的成绩,不要为因袭的成见或学说所蒙蔽,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概念 。至于其他问题,例如对于中国画整个的看法,中国画的出路等等,因为篇幅限制的关系,请读者参阅去年冬天《文学》杂志一卷五期,李健吾先生和我共同写成的一篇关于中国画的文字4,此地也就不便多加重复了。
1.金冬心、陈老莲追求古拙,从 Grotesque 方面得到的特殊的效果,当然不能抹杀。我们觉得陈老莲的好处在他的线条。爱他们的人可以把他们捧上天上,但假如把他们的作品摆在唐宋人的精品旁边,他们是站不住的。
2.装饰艺术 Les art s decorat if s 包括房屋里一切可移动的应用器物,和装饰器物(绘画雕刻除外 )例雹瓷器、铜器、漆器、织品、绣、饰品壁花纸等等,也有人用“工艺美术”一词。
3.回教不许财富拜偶像,所以不用人物或动植物来装饰回教堂和居。室他们用文字、几何形体、抽象蓬绽Arabespue和颜色来替代。
4. 指 1933 年上海《文学》杂志刊登的《巴黎中国绘画展览》一文。
本文原载 1934 年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后入选1947 年《中国美术年鉴》,以《及二十世纪中 国美术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