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导演曾说:
“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写小说、拍电影”
“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这期节目的主题正是“故事”
“每个人都喜欢故事,所以我就来讲几个故事”
万玛才旦导演的讲述从这句话开始
在艺讯网与导演合作的这期“洞见”节目中
他对故事的爱
以他特有的朴素语言
通过持续一整天的讲述展现了出来

这些故事
出自他的第一本译著《西藏:说不完的故事》
他翻译的这24个民间故事
不仅在藏地影响深远
也深刻影响了万玛才旦的创作与人生观
这些故事里的寓意
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既是故事的开始
也是导演用他的文学与电影创作
链接藏地与世界的开端


然而在这期节目的剪辑尚未结束时
却接到万玛才旦导演猝然离世的消息
回看大师那一天的讲述
重新感受他故事里传递出的
故乡、信仰、身份、寻找、觉醒与无常......
就像他短篇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名字
讲述从“说不完的故事”开始
却在一半戛然终止
感谢讲故事的人万玛才旦

讲故事,对万玛才旦来说是本能的冲动。为了解释这种本能,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书里讲,如果路途遥远,要么要有一匹骏马,或者自行车、摩托车、火车、飞机,要么就需要讲故事”,这也是藏地流传的一句谚语。
在过去的采访里,他也曾提起为了拍摄《撞死了一只羊》,他努力寻找到的另一句藏族谚语,——“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你也许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文字对导演来说重要非常,在拍电影之前,他本来拥有的是一个文学梦,文字是万玛才旦最初留下故事的工具。


1991年,万玛才旦来到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言文学班读书。大学同学回忆他大学时的样子,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边装满了书。
他喜爱的作家名单跨越东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包括托尔斯泰、郁达夫、马尔克斯,也包括余华、阎连科、格非、苏童、残雪等等先锋作家。他与电影的缘分,仍停留在儿时,热爱跑去看家附近水电站职工礼堂电影院里,两毛钱一场的黑白电影。
魔幻与神秘主义是藏文化中自生的部分,而荒诞则是他不断在藏地城市化进程中观察到的,传统与现代化激撞出的特殊气质,以及来自文学中狂野想象的滋养,他更早接触并持续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创作,让他遇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荒诞性,奠定了万玛才旦日后的文学与电影创作倾向。

自称“不安分”的万玛才旦,因为文学梦,放弃了干了4年的小学老师职位去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藏汉互译翻译专业硕士毕业后,借着申请学生资助的机会,他想试一试对藏民来说“比较新的专业”,他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开始了电影路。
作为著名的作者型导演,他的创作过程几乎总是文学先行,《塔洛》《撞死一只羊》等等很多电影作品都来自他的小说,2002年他真正开始拍电影时,他已经出版了多部小说,作者的身份让他对故事更加敏感。


拍“出道”作品是为了交北影学生作业,万玛才旦记得,他花了几千块钱,带着一台DV和4位大学同学,找到一间自己熟悉的寺院为场景,拍摄了短片《静静的嘛呢石》,拍摄前后用了6天时间,这部短片让他收获了作为导演的最初关注。
2004年,在老师杜庆春的建议下,他将《静静的嘛呢石》拓展为长片,之后又凭借2009年的《寻找智美更登》与2011年的《老狗》,完成被电影评论界称作“藏地三部曲”的创作。


随后的《塔洛》,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撞死一只羊》获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勤奋的创作,促成了后来鼓励了大批藏地青年创作者的大师,万玛才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藏地新浪潮”开创者与旗手。
01.故事与故乡
在接下来万玛才旦亲口讲述的故事,选自他的第一部译作《西藏:说不完的故事》,这本书中精粹的24个故事,大多来自口头流传。就像万玛才旦童年时听的《格萨尔王传》,它们都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
万玛才旦讲述的《西藏:说不完的故事》的故事视角来自主人公德觉桑布。听者将从他的视角,聆听和跟随叙事,一如《一千零一夜》里采用的嵌套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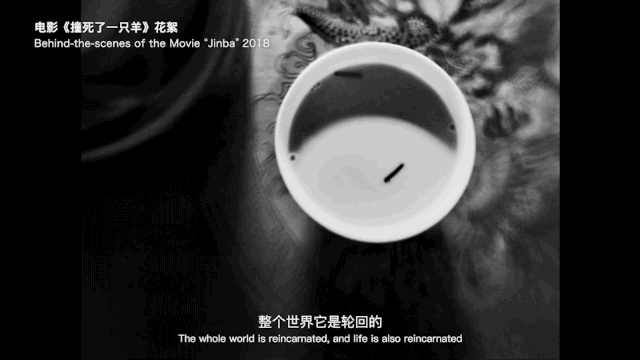
龙树大师指点想要学习法术的德觉桑布,前往寒林坟地,寻找如意宝尸。传说中,如意宝尸浑身是宝。其降世能消除世间的贫穷与罪孽。消除贫富,让所有人得到快乐。但想要取得它,背尸者必须全程缄口不语。
“既然你不开口,就让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为从背尸者顿珠背上逃脱,如意宝尸引诱背尸者沉浸在一串一串的故事中,失口发问。
于是,借德觉桑布背上背着的如意宝尸之口,源源不绝,可以世世代代,永远讲下去,形成了西藏讲不完的故事。这些环环相接,有趣又充满智慧与人生哲理的故事,令背尸者沉浸其中,每每失口发问,“话一出口,‘噗哒’一声,如意宝尸便又飞回寒林坟地……周而复始,一如不断的轮回。
站在《西藏:说不完的故事》的叙事之外,借德觉桑布与如意宝尸之口,万玛才旦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叫做《石狮子开口》。
山脚下,住着一贫一富两户人家。穷人每天带着糌粑上山,他以打柴为生。山上渺无人烟,只有一个石狮子,穷人休息时,就坐在石狮子边上吃糌粑。
每次他都将一撮糌粑放到石狮子嘴里,恭敬地请“石狮子大哥”吃一点糌粑。
有一天,石狮子突然开口,吓了穷人一跳。石狮子想要报答这位贫穷的好心人,指点他在太阳出来前,带着一个口袋来找石狮子,要“给你装点东西回去”。
天没亮,穷人带着他平常用的糌粑口袋找石狮子,石狮子张开嘴,告诉他,里边的黄金在日出之前,他可以想掏多少掏多少,日出之后,它就会闭上嘴巴。
小糌粑口袋很快装满,石狮问他为何不拿个大口袋,穷人却说,这些金子他一辈子已经用不完了。他下山去,过上了“家畜满圈,五谷满仓”的好日子。

富邻看在眼里,便向老实的穷汉套话,知晓前因后果,富邻心里产生了嫉妒与贪念,于是他也有样学样,换上破衣烂衫,上山砍柴,每天喂石狮子糌粑,说些客套话。
如他所愿,石狮子终于开口了,邀请富人带好皮袋上山,还叮嘱他,“一定要记住,在太阳出来之前把手取出来。”
奈何富人带的皮袋太大,总也装不满,他掏了一次又一次,当他再一次把手伸进石狮子口中时,太阳突然升起来,富人再也无法将手抽出来。
文学梦,电影梦,梦是人的本能,也是每个人的故事。叙述者万玛才旦这样聊起西藏民间文学对他作品的影响,“大家都喜欢讲故事,马尔克斯的祖母也喜欢讲故事,所以马尔克斯听了非常多的故事。藏区也是,小孩听大人讲故事,受到熏陶,他们也会成为新的口头的讲述者。”
“它们就像藏族歌谣。比如塔洛唱的情歌,藏语叫拉伊,也是非常普及的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尤其在一些场合,男女表达爱情,拉伊是很重要的交流的形式。它有不同的步骤,有一套固定的修辞,拥有非常丰富的叙事性。”


西藏民间故事老少皆宜,文字朴实,故事主线简洁清晰的特点,大量使用对仗与反复结构,都影响了他的创作,让他“希望也通过最简洁朴素的语言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在《撞死了一只羊》中,电影开头与结尾形成一个轮回,正是受到了藏地民间故事中循环、轮回的世界观影响。

熟悉万玛才旦的观众知道,他一直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希望不带任何偏见地,如实讲述他的故乡西藏的故事,无论传说、风俗还是藏民生活日常,无论以写实还是魔幻主义的文学与电影手法,他都无比渴望以自己的方式,向藏地之外,介绍他心目中故乡真正的样子。
就像他曾在采访中的回答,“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02.身份与寻找
第二个故事叫做《鸟衣王子》:一户人家有三个女儿,有一天,她们分别上山寻找走失的奶牛,三人都偶遇了一只白鸟。白鸟说,
“吱吱吱,吱吱吱,
给我一点糌粑,我说一句好话;
给我一点酥油,我说两句好话;
给我一点干肉,我说三句好话;
要是做我伴侣,好话全都告诉你。”
只有小妹决定满足它的愿望,走入白鸟在山洞里的家。谁知山洞里,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小妹答应留下来,和白鸟王子一起生活。
直到有一天,小妹在赛马场上看到了一个骑青马的小伙子,暗自倾心。回家路上,一个老太婆告诉她,小伙子其实就是白鸟,只要偷偷烧掉他的鸟衣,就可以永远和那个英俊的小伙子在一起。

小妹听言藏在了门后,待鸟衣王子脱下鸟衣,王子骑青马而去,小妹趁机烧掉了鸟衣。
当小伙回来发现鸟衣被烧掉,他万分惊慌,原来他是一位背负诅咒的王子,“只有穿上鸟衣,妖精才不能害我。”说着,一股妖风卷走了王子。小妹日夜不停,哭泣着,找遍了整座大山的每一条沟壑。
终于有一天,王子终于显形告诉她,只要找齐一百种羽毛,织就一件新的鸟衣,便可以为他招魂。就这样,鸟衣王子变成一只羽毛华丽的小鸟,回到了小妹的身边。
“身份”和与其对应的“寻找”,是万玛才旦电影中最为显现的主题,“就像电影《塔洛》里的主人公。电影里很多人不记得他的名字,只记得他的辫子,所以叫他小辫子,他自己也不记得他的名字,小辫子就成了他的‘名字’,成了他的一层身份的象征。”

关于他对身份的感受,导演也曾在访谈中,反复谈及,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两套价值观的影响与冲击。
“您是否存在某种身份焦虑?存在某种民族文化的焦虑?”
万玛才旦无法以确定的语言,让这一问题落地,也许是因为它的答案将太过复杂与宏大,他只能沿着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沿着答案可能的形状尽量地勾勒它。从小在藏地文化环境中成长,眼看着所有新的东西进来,如此迅猛,根本来不及消化,在万玛才旦的观察里,无疑“形成了很多很荒诞的东西”。

新事物带来文化冲击的反面,是旧事物在他身上的天然存在和无法抗拒。比如,万玛才旦没有皈依,因为他并不需要——“对我们来说,没有皈依这样一种说法,不用特意通过形式感的事情进入什么”。特定的信仰与文化与他们共生,顺其自然地如同万玛才旦的名字。
万玛,是莲花的意思。万玛才旦的家乡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创始人是莲花生大士白玛桑巴瓦。很多人的名字里,都会带有莲花生大士名字的一部分。
他的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也与文字有关。“乌金”翻译自藏文,它是莲花生大士的出生地。因此,当地人只要通过名字,就能分析出一个人来自藏传佛教的哪一教派,来自什么地方。天然价值观也是通过很多方式,例如民间故事的流传,深刻地烙在当地人和万玛才旦的脑海中。


另一种价值观来自教育,“之前我接受了一种价值体系的熏陶,上学之后,又接受另一套价值体的熏陶,它们在互相参照里,会形成一种很复杂的有些荒诞的东西。”
塔洛并没有找到“一百种羽毛织就的新羽衣”的鸟衣王子那样幸运,在《塔洛》故事的结尾,被大家叫做“小辫子”的孤儿塔洛,最终连自己的小辫子也失去,同时也失去了他最后的“身份”,成为了导演去捕捉当代藏人某种真实精神境遇的载体。
03.觉醒与无常
万玛才旦讲述的第三个故事很简单,据说它在藏地家喻户晓。
很久以前,有一个女人,因为失去孩子,每天都陷入在痛苦中。有一次,她去拜见释迦牟尼佛,讲述了她身处的痛苦,但释迦摩尼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出劝导,只是让她回家去,并让她在回家路上,问询路上她遇到的每一个人,“你有没有失去过亲人?”
女人突然开悟——走在路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经历过与她同样的痛苦,对无常的领会,让她又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领悟无常,达到觉醒,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的电影《气球》也是在讲藏地女性的觉醒,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气球》是导演在2020年上映的作品,也是万玛才旦在世时正式上映的最后一部长片,曾获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获最佳影片提名。这部电影中的主人公达杰一家,尤其是女主角卓嘎,在传统的轮回生死观念、传统婚姻观念,生育政策与现实经济条件以及女性生育选择共同构成的夹缝中,进行复杂而艰难的抉择。


万玛才旦通过《气球》看到了一位女性,尤其是藏地女性觉醒面临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于是,他为主人公卓嘎赋予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觉醒包括许多的外部条件,电影里开放式的结尾,就是因为她的两难造成的,她很难像一个现在的女性做到彻底觉醒、出走,给自己一个明确的选择,我认为那是做不到的。”

“但我很难替这样一位女主人公,找到一个很明确的出路。我只是展示了这个人物所面对的困境,并且为卓嘎缓慢的女性觉醒,安排不同人物与她形成对照。”带着理解与共情的视角,导演触碰到了一位藏地女性,在几层身份叠加与迷失的困境之中,处于进行时的一场勇敢而懵懂的觉醒。

“释迦牟尼佛是觉醒者,佛在藏文里亦是‘觉悟’的意思,是从一个认知到另一个认知的过程。对生命的体会,在佛教中,觉醒与开悟,是在讲对于生命与世间万物的无常的领会”。

万玛才旦说,“这就是所谓的向死而生。然而,开悟需要一个过程,就像释迦牟尼自己,他原本是一个王子,过着原本荣华富贵的生活,见不到世间的生老病死与各种痛苦。有一天他出去了,看到并且意识到贫穷、衰老、生死的存在,他才突然开始醒悟,最后在菩提树下悟出了时间的真理,成为了佛,觉醒是一种过程。”


很遗憾,在无穷无尽的藏族故事中,万玛才旦的故事却戛然而止,感谢他曾经带来的每一个故事,和故事里每一次引发的微小开悟,加深了我们对于无常的领会。
文 | 孟希
图 | 艺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