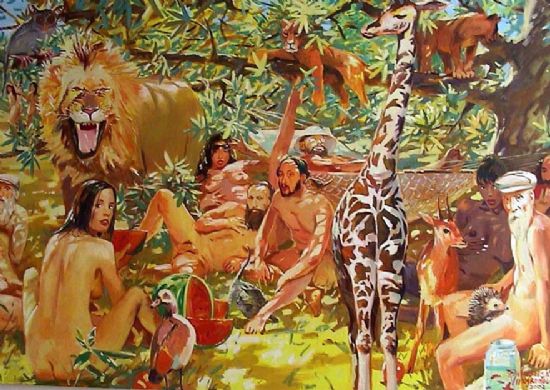
博物馆教学是一门艺术。目前中国的博物馆美术教育大部分还仅仅停留在导赏员介绍作品和为小朋友提供场所进行美术创作和体验的层面。关于博物馆中的美术欣赏教育该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方法,有何种教育模式?目前的教育模式有哪些优缺点?什么是好的教育并且如何引导我们和我们的同事来始终围绕着这样的教育模式进行博物馆教学?这些是博物馆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目前,美国博物馆欣赏教育研究倡导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即导赏员单方面介绍作品背景及作者状况的模式,转向对话式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在美国的众多博物馆中,博物馆的教育人员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教授不同的项目。每位博物馆教育者在教授艺术的过程中都会融入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风格迥异。比如:有的博物馆教育者带领学生面对一件美术作品,在整个时段都启发学生用自己的眼光描绘和感受这件作品。这样的博物馆教育者把自己的课程建构在观察和理解学生的观点之上,并相信通过共同的体验,艺术品更高的含义将会展示在人们面前。第二种博物馆教育者会通过激发学习者的信心来引导他们观察不同作品中的相同的特征,让主题随后出现。这两种方式在某些方面非常地相似,两者都使教育者和学习者集中精力,并激发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是在艺术品本身,并共同理解了整幅作品的含义。最后,当小组聚集在作品周围的时候,学习者仍然想继续这种探索的历程。由此,教育者知道他的学员和艺术品之间的沟通不是一个终结,而是开始。
一、解读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中的“对话”
对话作为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的一种隐喻:游戏
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中的对话,已经不限于语言领域,而是一个具有博大内涵的“隐喻”。作为隐喻的对话,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方法、一种形式、一种活动,更是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它可以用伽达默尔提出的另一个隐喻“游戏”来加以表征。在伽达默尔看来,任何一种对话的进行方式都可以用游戏概念做出描述。
伽达默尔将游戏描述为理解的基本方式,并深入地论述了对话与游戏的关系。在他看来,首先,游戏与对话是异质同构的,对话无疑包含着游戏,人们之间的对话在许多方面都暗示出理解和游戏的共通性。从本质上说,语言就是对话,而进行对话就像做游戏,意义理解通常就存在于一个起作用的语言游戏框架内,而且总是以参与语言游戏为前提的,因此,对话中所发生的相互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因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1]
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感知、想象、理解是三个逐渐深入的阶段。这三个阶段需要欣赏者参与其中,对作品进行积极主动、持续不断的提出质疑,积极参与到理解作品中,也就是身入其中,而不是以观察者的身份置身其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问质疑所要理解的问题,然后通过观察期待事物自身确定它如何“回答”,这正是伽达默尔提出的问答对话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对话就是对话双方在一起相互参与着以获得真理”。[2]在艺术博物馆中导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也正是导览员带领观众一起参与到对作品的理解中,“纯粹的讲述方式(就传统的观点而言),是将博物馆资讯呈现给观众功效最差的一种方式。可惜,它也是众多博物馆导览员所采用的一种方式。导览员常以为他们应该把握时间,尽可能把最多的资讯告诉观众。”[3] 然而这样的讲授方式是占有式、掠夺式的主体主导,不能存在于真正的游戏中。对话式的导览就像做游戏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游戏者一样,对话者之间也是一种完全平等、民主的关系。游戏精神就是一种对话精神,真正的游戏就是一场自由平等的对话,而真正的对话也正是一个游戏的过程,游戏的规则就是游戏者之间的约定性,决定对话意义和进程的不是对话者,而是对话本身。人在游戏中与世界构成了意义的整体,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得到生长,世界得以扩展和丰富。
对话作为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的一种态度:积极介入
对话作为一种态度,是指一种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介入、互动和合作的“意识”。艺术博物馆的导览正如Edwards所说:“(导览)是一种资讯服务;一种指导服务;一种教育服务;一种娱乐服务;一种宣传服务;一种具有探索性的服务。导览的目的是为了要给人们新的了解、新的洞察力、新的热忱、新的兴趣。一名称职的导览员,就像一位让人着迷的花衣魔笛手,带领观众轻松地进入一个新奇又迷人的世界,一个他们的感官过去从未穿透的地方。导览员需要具备三种基本的态度:知识、热忱以及亲和力。”(Edwards,1976,P.4)
不仅导览者(教师)的态度如此,观众(学生)在欣赏中的思维状态更是一种“参与性理解”,对话者不是以观察者的身份置身其外,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我们远非被动接受经验的主体,我们是能动的理解者,在接受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自身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极大的。”[4] 正如游戏是参与者充分的、自主的参与而不是被动参与一样,它同样也是对话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游戏中,游戏者之间是充分互动的,没有互动就没有游戏。同样,在对话中,只有参与是不够的,惟有充分的参与和互动,才能达致对话境界。对话的实质就是通过对话双方的互动达致理解和成长。对话表现为解蔽、敞开,在相互沟通和交流中平等交换,深入对方的思想世界,相互接纳,从而产生理解。因此,在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中,强调“观众的经验”的重要性,也就是,理解只有通过观众才有意义,只有通过让观众的积极介入才能看到的意义。那么在对话中,任何一方都不是被动地接受意义,而是主动参与到对作品的理解之中,参与意义的建构。
对话作为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的一种存在方式:体验
“以往博物馆总是将一大堆东西摆在一个房间里供人参观,但这几座博物馆决定摆脱这种无趣且无法让参观者参与的展示方式。比方如果让儿童观看成千上万双钉在玻璃盒中的昆虫,只会让他们觉得这真是一种无聊之极的学习;唯有导览员才能让这类展示品使人产生兴趣,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展示品本身根本无法引起儿童任何的注意”[5]
这显示了人们存在于博物馆中的重要任务是体验,没有体验的观赏带不走任何认知与兴趣,而体验与对话则息息相关。人,是一种对话的存在,对话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断地言说,言说是人存在的本性。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本身就有一种渴求与他者对话的需要。人的生存需要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与文本对话、与世界对话。罗杰斯说:“如果我能将自己的内心实在传达给别人,从而与对方建立密切的‘余—汝’关系,我就感到非常高兴。”[6] 因此,对话就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启发性的对话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更会扩展观众的情感体验。
在艺术博物馆中面对作品的对话体验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个失去体验与感悟力的欣赏过程只会始终活在“它”的世界里,为其所奴役,而无缘意识到“你”的奥秘。因此,没有体验的对话是不存在的。
对话作为博物馆美术欣赏教育的一种学习过程:建立学习和认知的过程
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指出:“为了理解对话实践的意义,我们不得不抛开把对话简单地理解为纯粹是一种技巧的想法。对话并不表示我想精心构建且需借助另一人的才智才能实现的虚假途径。相反,对话的特征表现为认识论关系。因此,在此意义上,对话是一种认识途径,并且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让学生投入到某项具体任务之中的纯粹的策略。……对话是学习和认识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7]
由此,对话是一种学习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对话式学习让博物馆教育者和观众积极参与到对话场域中来,这种经历磨练着我们的知觉、完善着我们的思维,并连接着我们已知和未知的领域。把对话理解为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亦更加促进教育者以纯然的好奇之心对待学生的认知过程。鼓励他们把生活阅历转化为知识,并把早已获得的知识用做发现新知识的过程。知识、概念、认知的学习在对话中自然建立起来。
二、对话,作为教师内在化成长的方式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教育部工作二十多年的Rika Burnham 在她的文章《博物馆中的艺术教学》(The art of teaching in the museum)中说:“真正的对话是通过博物馆教育者自身对问题的敏感和理解而触发的。老师需要有技巧的做好演习和先前准备,才能了解过程会出现的观点并懂得如何推进对话的发展。”是的,教师对作品潜在理解的把握是博物馆教育的重点之一。每一幅作品的含义都会不同,每一个团队的对话也会不同。博物馆教师在教学之前的充分准备会让对话的次序和形态自然而慢慢展现,这才是赋予对话意义的方式。
为“对话”而作前期准备
在组织博物馆对话式美术欣赏教学前,教师要做些什么前期准备呢?
首先教师要足够了解作品,并长时间仔细的审视作品。正如在《培养优秀的导览员》一书中,Grinder和McCoy写到:“仔细地审视那些已经非常熟悉的文物,然后,用一种‘崭新的眼光’再看一次。”[8] 老师必须花数小时来观察作品,包括从不同角度和远近来看作品;必须让自己像第一次见到作品的学生一样来观察作品,必须放下所有的负担。也许会发现自己被画面上的动作感到疑惑,也许会因画面丰富的表情和姿态而猜测其中隐含着一个故事。要细致的体会画家如何运用主色调,如何运用光,如何运用笔触……,为了能理解作者是如何构图的,也可以画个草图。这样,画面就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了。
接下来的准备工作是做研究。博物馆教师要仔细的阅读博物馆中相关藏品的介绍,并和自己的同事讨论作品。好的教学是以对艺术品充分的了解为前提的。信息和观察的结合能触发灵感。博物馆教育家通过对作品的充分了解把观众和艺术品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教师应该如何运用从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呢?获得的资料应该是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而不是将已经建立的研究成果强加于他们的意识之上。她会介绍作品和其创作背景之间的联系,从而给予学生们关于当初画作是如何产生、创作、当时社会是如何来审视它,以及画作对不同年代的读者意味着什么。
在博物馆教学中,教师对艺术品的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他通过这个过程是如何激发潜在对艺术品的理解。教师开始形成对作品的了解: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寻常的,以及作品的内容是什么。通过研究和经验,教师发掘出作品可能隐藏的意义。基于这些可能性,教师要设计课程计划,让不同的思想和见解来引导对艺术品的理解。课程的框架取决于作品的数量和类型,可松可紧。内容可以包括指引式的提问和之后一系列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或者是建议。教师所提出的建议是有可塑性的。教师应该把课程计划看做是灵活的,带有开放性和带有试验性质的。
为“对话”而作后续反思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G.J.Posfl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知识,因此提出了“成长=经验十反思”的教师发展公式。这意味着教师的成长绝非经验的简单积累,只有在经验基础上进行自觉的反思,教师的成长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文认为,反思对于博物馆教师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反思能够达成教师角色的改变与确认,能够让“对话”内化为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方式。因此,博物馆教师首先应从过去的“讲解员”、“导览员”转化为“反思性实践者”。教师在博物馆日常的专业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学习、反思,对自己的专业发展状态作出诊断和评价,便可以形成一种自我更新。博物馆教师的自我更新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博物馆教育的潜在动力。
如果经由“反思性实践者”升华为“研究者”,则是博物馆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高级表现。“未来教师与其说在被训练为富有组织创造性参与性和训练性学习使命的教育家,不如说在被训练为各学科的研究者。”[9]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来理解博物馆教育研究,都不得不承认博物馆教师充满了丰富的研究机会。当然,教师成为研究者,并不是要教师在博物馆教学之外去承担额外的负担,而是主张教师在对话中研究,在研究中对话,使对话教学与研究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博物馆教师在行动中对自身实践活动做一种批判式的反思,通过反思,才能发展为“研究者”,进一步变成真正的“对话者”。
综上所述,艺术博物馆中的对话式的理解性欣赏教学是一个学习过程。长期以来,以传授为中心的记忆教学仍在广泛被使用,博物馆中所发生的真正的艺术欣赏是需要观者把对情感、知识与技能的认知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仅由单向的接受是不能够完全激发每个人内在的潜能的。美国基础教育委员会的James Howard在国家广播电台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教育就是在你忘记你从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你所剩下的东西”。这样的观点可否用在博物馆导览欣赏上,博物馆欣赏教育就是当你忘记所听的导览内容后,你所剩下的能感受到的东西。
因此为了激发观者艺术欣赏的真实发生,博物馆导览和欣赏教学必须能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博物馆内必须环绕着精彩对话的光辉。当博物馆教师用精心设计的、充满思想性的问题轻轻推进学生的回答时,这激情、这光芒只会闪烁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频繁,燃烧得越来越猛烈。
[1] [德]席勒著,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第90页。
[2] [德]伽达默尔,夏镇平译:《赞美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69页。
[3] Alison Grinder、E. Sue McCoy著,阎惠群译:《如何培养优秀的导览员——博物馆与相关文化教育机构导览人员养成手册》,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5,第132页。
[4] 保罗·黒利著,《境遇合理性和解释学理解:伽达默尔对合理性的探索》,《天府新论》,1997,第60页。
[5] 同33注,第33页。
[6] [美]马斯洛著,《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第147页。
[7] [巴西]保罗·弗莱雷著,顾建新等译,《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8页。多纳尔多·马塞多为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的纪念版引言,引自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 “A Dialogue: Culture, Language, and Race” i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5, no. 3, fall 1995, p.379
[8] Alison Grinder、E. Sue McCoy著,阎惠群译:《如何培养优秀的导览员——博物馆与相关文化教育机构导览人员养成手册》,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5,第116页。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第2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