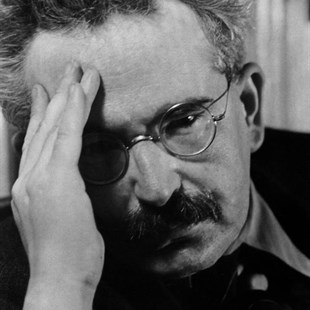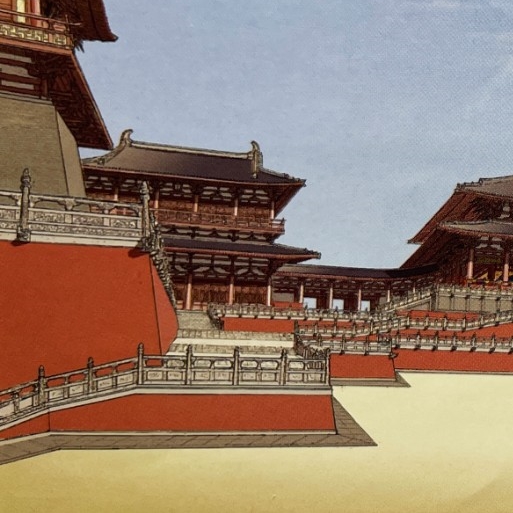从1840年开始,《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妙法莲华经》(Lotus sūtra)、《道德经》(Tao Te Ching)和《奥义书》(The Upanishads)等读物影响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对于宇宙本质的自我整体性的探寻。艺术家们经过慎思弃绝了欧洲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转向亚洲,期待用一种可以定义现代及现代思想新的存在和意识的先验论理解,来打造一种独立的艺术家身份。东方宗教(印度教、密宗、禅宗、道教)、古典的亚洲艺术形式以及现场表演传统吸引了先锋艺术家。日本艺术和禅宗佛教居于主导部分,这是因为历史上美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比中国、印度等主要资源国的联系更为牢固。伊斯兰艺术和思想的重大影响则超出了我们的议题范围。从产生于波士顿先验论者圈子的19世纪晚期的美学运动开始,我们的研究阐明了形成诸如抽象艺术、概念艺术、极少主义和新前卫艺术等主要运动的亚洲影响,就像它们在纽约和西海岸所展现的。我们也涉及到诗歌、音乐、舞剧(Dance-theater)的发展。这呈现了在美国工作的艺术家是如何选择性的改造东方观念和艺术形式,不仅创造了新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关于静观体验和艺术自我改造角色的一种新的理论定义。亚洲维度也给现代和新前卫的前提提供了一种普遍主义逻辑,即认为艺术、生命和意识是一种被存在的具体性所整合的互相渗透的现实。
一般而言,将美国艺术中亚洲影响的叙述局限在19世纪的日本风(Japonisme),这是已有史记的实践,即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受浮世绘木版画(Ukiyo-e woodblock Print)、日本屏风画(Screen Paintings)和纺织品(Textiles)的启发,并正式采用于绘画和装饰艺术中。“第三种思想”从视觉形式到结构观念入手叙述,当时美国现代主义对“异国情调”的兴趣,已经从执著于色彩平涂、简单的形式以及与日本艺术大胆的轮廓转向跨越五千年亚洲文明的玄学、哲学和美学等高级系统的集中考察(即使是折衷主义的)。把艺术作为针对一种经验行为的视觉愉悦的对象,是展开在时间还是空间中,现代主义者在这两者之间摇摆,这一定程度上可通过美国文化中亚洲思想的知识史来评估。
美国艺术家对亚洲艺术与思想感兴趣的同时,后者已很难不受重视并需严谨的研究,定义东方哲学和美学的术语由此出现于美国,或以一种个体历史考察的编年形式记载关键艺术家的生平及知识邂逅的重大叙事。这并不奇怪。因为思考现代美国艺术与亚洲古典艺术和哲学体系之间的相交点,需要熟悉它们的主题及不同话语。传统上,这些职能分属不同的学院和博物馆。即使是约翰•凯奇(John Cage)这样的被看作是浸染于亚洲文化的艺术家,也会发现其著名的“偶然行为”(Chance Operation)经常被肤浅和错误地描述为“禅意”。事实上,他的不确定性系统是基于《易经》,这是一本占卜之书,也是儒教“五经”之一。凯奇故意使用《易经》投掷硬币或木棒的方法来决定作品的结果,这是他消除艺术意图的方式。艺术意图是随机性或意外因素的对立面,就像“禅意”一再误导并暗示。
不只是美国发现了亚洲艺术和思想。在欧洲,从对可见物的再现到被俄裔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Vesily Kandinsky)叫做“自然的内在精神”的对可见物的表现,这种受东方启发的表现可追溯自19世纪晚期。对欧洲迅速工业化和物质主义的反抗,使受知识分子思想支配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力图寻找替代的方向。有些人主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象征主义者寻求神秘学和民俗,间或也援引东方意象。其他人则重新发现一种东—西神秘主义——忘我的、直接的、先验性的存在经验,有关上帝或者被设想为无限虚空和无休止过程的终极实在。纽约的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由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于1875年与人合作创立,该学会激励了对印度教、佛教训练兴趣的高涨,他们将宇宙抽象为精神开导的直观手段。在《秘密教义:科学、宗教和哲学的综合》(The Synthesis of Science,Religion,and Philosophy,1888)中,她改进了密宗静坐方法,实现了无色界禅定(Arupa-dhyana),这是一种超越自我与自然之区别的冥想状态,完全不受形式和形象的约束。康定斯基从神智学(Theosophy)中得到启发,阐发了他的革命性宣言,即抽象艺术(无形的形式)在表达宇宙法则上有巨大的潜力。艺术作为一种神秘的内部结构内含着一种改变观众思想状态的能量,这一艺术观念对美国前卫艺术家有一种深刻的冲击,康定斯基的抽象理论对亚洲逻辑的借用不是一种迷失。
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玄学的比较研究,为艺术家们通过当代话语过滤器来邂逅亚洲思想提供了丰富语境。至少从1827年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就将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空无崇拜”(Cult of Nothing)和佛教涅磐相联系:一切事物的原则,根本的最终的目标和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从浪漫派到后现代主义,西方思想家热衷于将吠陀(Vedic)和佛教经典作为一种质疑和对比方法。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从1919-1921年一直在中国和日本旅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及其他众人,都把一系列亚洲玄学作为哲学思想的范例。这种“东—西方”的交流可以是相互的。例如,海德格尔对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禅宗颇感兴趣。
1954 年,海德格尔与日本的手冢富雄教授进行过一次短暂的对话。海德格尔请教了语言本质、日本人的感性审美、表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并试图同自己的理论建立联系。手冢富雄也请教了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看法,以西方视角谈到了诗的功用和诗人的职责。由于关注意识的原始结构,这些哲学家从印度教和佛教领悟了存在与意识及其反映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统一性。这种直观的“纯粹经验”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种个人思维主体的站在外部并脱离知识对象的反身的自我意识)相对立。因此,某种现象学观念如纯粹意识、非媒介经验开始与东方哲学相联系,反之亦然。卡尔•荣格(Karl Jung)关于“超验机能”的理论,有关一种浸透于神话和现实的个体的“集体无意识”,激发了对现代心理学和亚洲心灵科学之间关系的丰富思考,这种思索立足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身体、自我与自然之间的二元性克服。最终,像尤金•赫里格尔(Eugen Herrigel,1920年代他在在日本教授哲学)写的《箭术与禅心》(Zen and the Art of Archery,1948),和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Robert M. Pirsig,1950年代早期他在印度教授哲学)写的《万里任禅游》(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1974)等畅销书,都建立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将东方的现实概念看作是心灵的反映。“第三种思想”关注的美国艺术家与东方思想的邂逅,产生的一系列反应。一些艺术家将他们亲近自然的方法进行重新排序,驳斥了西方拟人论和形式主义的说法,即认为艺术可以被事物仅仅是其本身的人工线痕所阐明。其他人则将时间的延续性和虚空植入新音乐、表演艺术和装置艺术模式中。披头士乐队将“禅宗迷狂”(Zen Lunacy)的肆无忌惮的自发性理想化,并且为意识流散文打下了新的基础。还有一些人则趋向一种特定的精神修炼,像拉•蒙特•杨(La Monte Young)的拉格(Raga);或者冥想技巧的高级专家像阿德里安•帕珀(Adrian Piper)的瑜伽。精神修炼和冥想技巧都成为他们个人哲学的中心,并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新。
到20世纪80年代,“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主义公式这一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支持的有关艺术的自我指涉功能的目的论定义已式微。艺术家们感兴趣于多样性、短暂性、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概念、语言的使用以及艺术家身体作为艺术,这已模糊了传统界限,并导致了偶发艺术、表演艺术、概念艺术、多媒体和互动装置的兴起。在此过程中,艺术变成了关于注意力的行为,即一种正念的状态,这种注意(Mindfullment)状态可以恰当地假定一种有关存在和意识的亚洲概念的某种文化流畅(Fluency)。
一、亚洲作为方法
与“第三种思想”的美国人文基金会咨询委员会成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构建这一课题的方法形成。这使我们将亚洲的影响作为一种历史、产品及其概念是如何被中介、解释和使用的政治加以系统化。结果是,这个项目不是关于亚洲本身,而是揭示了一系列方法,艺术家和作家们用这些方法为他们的创新策略及受制于历史条件的世界观收集想法。
艺术史学家柯克•瓦恩多(Kirk Varnedoe)对我的学术训练,有助于我早期对美国艺术家和亚洲的关系的思考,这一关系具有一种创造性来源和文化想象的复杂性。我首次向瓦恩多谈及此想法是在90年代早期,他当时持怀疑态度。作为备受争议的1984年现代艺术博物馆“20世纪艺术中的‘原始主义’:部落与现代的密切关系”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他对于一个有关西方和他者关系建构的展览极其谨慎。那个展览将现代派作品和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的部落艺术并置在一起,显示了“直接影响”、“巧合的相似性”或者“基本的共同特征”对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等形式创新艺术家的影响。
批评人士猛烈抨击部落艺术和仪式的简约再现,托马斯•麦克埃维(Thomas Mc Evillet)将其描述为现代派“为了纯粹形式的崇拜而牺牲事物的完整性”,这只能证明“西方利己主义仍然像在殖民主义和怀旧主义(souvenirism)世纪中一样放纵”。瓦恩多质疑我如何才能使人们在一个展览中“看到”亚洲影响。他的质询使我的叙述结构以及对阐明这一主题的作品选择变得清晰,也帮助我确定这次研究绝对不像早期展览一样彼此雷同。凡•高将他崇敬的日本大师称之为“野蛮的”,高更用“原始的”来形容像柬埔寨、埃及、波斯、秘鲁之间不同的风格,19世纪有关东方主义、日本风以及原始主义的艺术运动,根本上不同于我们的主题。
至少1900年左右,所谓神秘的东方在知识上和概念上的摇摆,已经将现代主义者把非西方对象作为文化护身符去“收集”的痴迷,转化为体现一种优越感的玄学体系的“内在化”。一个不断膨胀的经典亚洲文本图书馆形成了在西方包括美国的亚洲文化展示。梭罗(Thoreau)对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克里希纳(Krishna)和阿朱那(Arjuna)探索形成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最著名部分的冥想的玄学对话的赞赏代表了相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于东方神圣文本的感受:《新约》(The New Testament)因其纯净的道德而引人注目;《印度经》(Hindoo Scripture)的绝佳因其纯净的知性。读者不可能再被唤起并保持一种比《薄伽梵歌》(Bhagvat-Geeta)里面更高的、更纯粹的、更“稀有”的思想领域……与《薄伽梵歌》庞大的天体演化的哲学相比,甚至我们的莎士比亚有时候似乎是幼稚和缺乏历练。在整个研究期间,这些杰出的人物,像阿南达•肯提什•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阿瑟•韦斯莱•道尔(Arthur Wesley Dow)、欧内斯特•芬诺洛萨(Ernest F.Fenollosa)、荣格(Jung)、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南希•威尔逊•罗斯(Nancy Wilson Ross)、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铃木大拙(D.T.Suzuki)、梭罗(Thoreau)和亚瑟•威利(Arthur Waley),都对亚洲哲学、玄学、诗歌和美学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评述和改编。
艺术家们通过友谊、一种师徒关系或者著作邂逅这些关键人物,这种邂逅是这个计划的叙事核心。这种知识史模式也包括在尾崎中川(IKuyo Nakagawa)的年表和参考文献中,“第三种思想”使用这些历史文本作为邂逅亚洲的主要观点。这些读物还给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政治反抗的逻辑,这种对抗被视为是西方道德和精神衰落的回应。
默顿(Merton)记述《薄伽梵歌》晚于梭罗一百多年,他声称:
它带给西方一种有益的暗示,即我们高度放任及片面的文化正面临危机,并最终可能以自我毁灭告终,因为它缺乏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意识。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度,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主张只是空话。
我们并不是暗示这个叙述中那样的研究对象没用。美国私人藏家和艺术博物馆掌有的非凡的亚洲艺术品,是世界上此类藏品中最多最好的,而且大量报道讲述了艺术家邂逅经典亚洲作品时的欢欣。布莱斯•马登(Brice Marden)将他向姿势的(Gestural)、书法的(Calligraphic)绘画(脱离了他的极少主义的、单色的木板绘画)的转变归功于1984年在纽约亚洲博物馆和日本博物馆举办的日本宫廷、文人和禅宗书法展“8到19世纪日本书法大师”,这次展览的作品来自美国的藏品。
他回忆说:
一个大坝决口了……我只是停下来说:我再也不会画那种画了—我要画这种画。然后我不得不想明白这种画是什么……我对于这个主意动心了—这些家伙们坐在风景之中,他们写诗,他们画画。
在他以唐代隐士诗人寒山命名的《寒山研究》(Cold Mountain Studies,1988-1990)中,他以对联形式的仿书法来结构他的作品,由右至左移动。但是除开这种借用的风格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和极少主义),马登还被书法笔触的纯粹心理感染力(不同于超现实主义的焦虑)及其空间留白原则所吸引。对于马登和许多艺术家,观看书法就像眼睛在追寻个体内在精神的轮廓。
我们展览的标题提到“垮掉的一代”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和布莱恩•吉森(Brion Gysin)的“剪拼”(cut-ups)作品。这份手稿是由随机的文本和图像组成,作者重组这些文本和图像,来创造一种概念的和视觉的类似拼贴画的叙事,他们总结说,成为一种不同于两位策展人总和的东西:即1+1=3。这个想法还唤起了一种折衷但是蓄意的方法,美国艺术家经常通过这种方法挪用亚洲材料,从而在他们的艺术中创造新的形式、结构和意义。误读、误解、否认和想象性投射表现为一种个人化、跨文化过程中的重要复述。一些艺术家认同非西方和前工业化体系的智慧,这正适用于颠覆和批判资本主义西方的精神枯竭。其他人则参与到一种融合的、东-西方普遍主义的后乌托邦话语,这符合他们的前卫议题。
从先验论、神智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默顿受启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基督教和佛教寺院神秘主义的整合,以及鼓吹在全球化时代仍持有活力的亚洲精神心理学的新时代运动,他们采集一种新的文化特性。另外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吸取和任何使用有益于他们特别的创造性冲动的因素。有些人则更诡异,如弗兰茨•克莱因(Franz Kline)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们从东亚借来单色的、书法绘画的视觉和姿势结构,但拒绝承认与其边缘的、弱势资源的直接关系。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如何进行传达和解释作品。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提出所有的阅读都是创造性的阅读,对一个体存在(being-in-the-world)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言。
他认为:
一个文本的真实含义,它对阐释者言说的方式,不取决于作者和他最初的公众解释的随机性。至少,它还没有被他们说尽。它也总是被阐释者的历史语境共同决定。文本的意义不是偶尔而是总是超越作者。
这种概念是如何在东西方幻影的迁移之间被传达、重组和再按排的创造性的历史现象,我们称之为“第三种思想”。这次展览选择的艺术家从事着一种挪用东方的策略,这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主体性、世界观和创造性想象的基础。
我们的挑战是推进把东方建构为一种美学、哲学和文化概念的简化套牌进程的批评。我们对现代美国艺术中有关亚洲的使用及阐释的分析框架来自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开创性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他发起了一种对“东方主义”话语严厉的、福柯式批判,这种话语使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侵略合法化了。他主张“东方”(Orient)是一种西方概念,是一种为证明西方“统治东方”正当化而设计的“意识形态虚构体系”。虽然萨义德的理论意义深远,但他对西方关于东方主题的研究、评论和创造性解释的整个雄心的贬义性倾向是有问题的。最近,有些批评者已经指出了萨义德著作的模糊性和局限性。
1830年代,“东方主义”这一描述文化多样性的术语首先在法国出现,它用于一些东方主题的使用:亚洲奖学金(从考古学到语言学到动物学);被拜伦(Lord Byron)推广的浪漫-幻想(romantic-fantasy)文学类型;被尤金•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ome)和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推崇的近东区域的一种绘画风格。萨义德对中东(他的巴勒斯坦血统的某种反映)的关注,只是部分与南亚有关,而在某些重要方面,根本不适用于东亚和东南亚,在这些地区,是日本而不是西方行使了最残酷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明治时代的教育家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1882年号召日本行使“天命”,把亚洲从西方列强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对亚洲的领导,这一号召在1940年由于极端民族主义者实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而达到高潮。这一共荣圈达到最高点时,统治了亚洲大陆的四分之三和南至密克罗尼西亚的太平洋半岛,正如约翰•詹姆斯•克拉克(J.J.Clark)所说,萨义德对西方再现东方的批判,其中西方对东方的知识,“通常来说,其显现的……来自文化的反感”,缺乏对东方及其产物的浪漫或积极的态度。
克拉克提倡一种“积极的东方主义,试图表明西方竭力将东方思想整合到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知识关注,事实是,并不能完全理解‘权力’和‘统治’的术语。”克拉克对于西方的批判不是西方如何诋毁东方,而是佛教、儒教、印度教和道教对于现代西方思想传统的有证据确凿的影响仍然很少被承认。我们对于美国现代艺术中亚洲艺术和思想的丰富使用的赞赏,乃是对克拉克主张的共鸣。
批评者还指出,萨义德忽略了对美国东方主义和被约翰•R•艾派尔耶希(John R. Eperjesi)称作亚洲和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想象研究。萨义德的分析集中在英国和法国的东方主义及其与中东相关的项目,美国与亚洲特别是太平洋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效果并未被广泛研究。此外,最近将萨义德的批评用于对印度或者中国绝大多数强调19和20世纪早期文学、哲学和宗教的研究,东方主义和现代西方艺术的主题,尤其是现代美国艺术,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最后,萨义德的论文没有将东方主义的影响归于它声称要描述的亚洲人的自我意识。《东方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1903)和《茶之书》(The Book of Tea,1906)的作者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以及斯里•拉马克里希纳(Sri Ramakrishna)的大弟子,与冈仓天心同一时代的欧洲与美国的韦丹塔协会(Vedānta societies)的创始人辨喜(Swami Vivekananda),都是例证。
正如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和哈里•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所描述的,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分别提升了日本和印度文化特殊的精神性,因为它们被西方的东方主义者看做是一剂治疗侵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药方。这段历史被伯纳德•福尔(Bernard Faure)称之为“次要的东方主义”(Secondary Orientalism)。
当代亚洲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根据西方术语在改写哲学传统中的角色,美国禅宗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禅宗的知性根源是现代日本哲学的京都学派(Kyoto school)。这一学派的哲学家以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ō)的著作为基础,为西方思想提供了基于东方逻辑尤其是日本禅宗的替代物。通过在现代西方哲学术语中定位“空”(Sūnyata)(空或无,Emptiness or Nothingness)的基本概念,西田和他的追随者们,包括铃木,创造了一种世俗的、美学化的、普遍的禅宗理论,这种理论省略了禅宗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在历史上、文化上和学理上的复杂性。通过铃木和久松真一(Hisamatsu Shin’ichi)(《禅与美术》(Zen and the Fine Arts)的作者,1957年;1971年被译为英文)的著作,西田禅宗哲学的简化概念进一步本质化为唯一一套独特的有关禅宗艺术的特征。这些哲学家推广了对于禅宗和日本文化的解释,促进了对禅宗思想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水墨画和书法的禅艺术、茶的艺术与表演(茶艺)等的广泛消费,没有剧场,园艺设计成为对“无形自我的自我意识”的经验的、心理的、审美的化身,这种次要的东方主义的重复叙述滋养了一些美国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这反映了“调和的过程”,而不是禅宗的历史现实本身。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使用“东方主义”作为这个展览和书的主题,因为太超重了。我们更愿意思考“亚洲作为方法”。1960年,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发表了“亚洲作为方法”的演讲。他比较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是对西方的直接反应,它的发展基于“简单的二元对立”,中国的现代化来自内乱和1912年清朝瓦解后的改革,以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为纯粹,因为它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愿望“立足于亚洲原则”。他援引了孟加拉语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e)的话,泰戈尔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访问过日本和中国,他很欣赏泰戈尔关于“东方的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思考了“内、外一代文化之间的区别”。如果亚洲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球的平等,它就必须普及它的文化价值,这被他称为“亚洲作为方法”。竹内写到:
为了进一步提升西方自我生产的普遍价值,东方必须改变西方。这是今天的东西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马上成为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议题……当此反转发生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然而,或许这些价值观还没有实际存在。我宁愿怀疑它们作为方法的可能,也就是说,作为主题的自我构成的进程。这是我所说的“亚洲作为方法”。
二、亚洲介入的遗产
这个项目中,“亚洲”这一术语是指地理上的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王国);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太平洋势力,一个多世纪来,它都和东亚有激烈的地缘政治的争斗。1898年,它把菲律宾群岛变成殖民地,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利不少,并且在1930年国民党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满洲的占领时支持国民党。亚洲太平洋战争由于日本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而升级。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打击显示了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事实上的军事和殖民强国地位的上升,并且使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不情愿地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年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在世界上尚属首次。而日本无条件投降再次巩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虽然冷战经常被认为是苏联和西欧、北美之间势力范围冲突的投射,其实大多数的军事行动发生在亚洲前线。美国1945-1951年对日本的占领以及战后和日本缔结的安全公约;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的中心作用,以及后来对韩国的长期驻军;它参与了1961-1973年的越战并且损失惨重,越战有270万美国军人参加,其中5.8万多人丧生,所有这些都证实了历史上亚洲的深远影响以及美国人民的心态。亚洲移民,尤其是西海岸移民,也都体现了美国经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的移民潮来自中国南部和日本,他们在美国西部边疆从事开矿、修铁路和农业生产。这些移民中有朱沅芷(Yun Gee,来自中国)和国吉康雄(Yasuo Kuniyoshi,来自日本),他们将他们的经验用绘画表现出来。其他人,像纳特瓦•巴哈瓦萨(Natvar Bhavsar,来自印度),草间弥生(Kusama Yayoi,来自日本),或白南准(Nam June Paik,来自韩国),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在二战后几十年参与到纽约的国际先锋社区。在60年代,在另外一次亚洲移居浪潮中,特里萨•鹤卿(Theresa Hak Kyung)从首尔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她冥想的行为艺术,反映了她文化身份的间性(In-between)状态。
美国对亚洲持续征战的遗产之一是其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这个项目不涉及文物收藏的伦理学,特别是那些从考古遗址获得的藏品,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阐述被少数有影响的学者馆长指导的鉴赏模式是如何形成美国艺术家们对亚洲艺术的接受,以及他们对艺术的绝对目的和本质的思考。1860年,新英格兰开始了对于亚洲艺术的鉴赏,这种鉴赏源于中国贸易。与法国对于日本风(这种日本风集中表现在当代木版画中,日本人认为这种画毫无价值,并且仅将其销售范围限于本地古玩商)的狂热不同,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学者和爱好者社群建立了一种标准,这种标准最终成为高级亚洲艺术的西方标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芬诺洛萨(Fenollosa),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馆里,放满了芬诺洛萨和波士顿人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William Sturgis Bigelow)、爱德华•西尔韦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和查尔斯•戈达德•韦尔德(Charles Goddard Weld)等人收藏的东亚佛教艺术、浮世绘和水墨画作品。1890年芬诺洛萨被任命为亚洲艺术馆长。他写的插图丰富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的纪元:东亚设计史纲》(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1912)阐述了艺术史的轨迹和偏见以及几代美国人的东亚艺术口味。芬诺洛萨有意回避了出口艺术和现代艺术,推广了一种视觉文化修辞学和民族身份,民族身份以“国宝”这一准则为中心,“国宝”被定义为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经久不衰价值的物品。按照芬诺洛萨的分级,平安时代的天台宗佛教绘画和室町时代的风景画都是日本独特的表达能力的顶点,这种表达能力使“打开自然事实与精神存在的‘天眼’”成为可能。他的著作影响了很多人,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包括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 Whistler)在内的唯美主义艺术家;道尔(Dow),(他的流行手册《构图》(Composition,1899)依据了芬诺洛萨的观点;还有庞德,他的关于中国诗歌翻译的现代派的书《华夏》(Cathy,1915),就基于芬诺洛萨的笔记。道尔和惠斯勒都欣赏芬诺洛萨称赞的他喜爱的室町时代大师雪舟等杨(Sesshu Tōyō)的水墨画中蒙胧的、单色调的、不对称的结构和接近消失的难以捉摸的形式。
芬诺洛萨的继承者是冈仓天心,他推广了日本茶艺的“乡村的”、“自然的”艺术。而出生于锡兰,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以一名馆长和作家的身份活动,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传统上对于东亚艺术的关注拓展到对印度次大陆的艺术,包括对舞蹈的关注上来。和芬诺洛萨与冈仓天心一样,库马拉斯瓦米把一种世俗的和普世说的人文主义传统灌注在他的美学理论中。也就是说,他把图像学和形式抽象到一种精髓,即传达一种永恒的“此在”(now-ness),这种“此在”吸引了艺术家们。在《“湿婆”之舞》(The Dance of Siva,1918)中,他用创造和毁灭的婆罗门舞的一种代表性雕塑形象描述了“理想的再现”活动。库马拉斯瓦米描述了印度艺术和思想的特征,即设想出一种形式作为某种先进的形而上学系统的化身,他声称这是所有小乘和大乘佛教文化的源头。艺术的目的是包含和传达一种神圣情绪或一种思维状态,库马拉斯瓦米将其描述为是某种正念经验的触发,排空某种散漫的意识,使人感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艺术不关心创造客体或为美而美的表演,它们的审美原则,实际上是它们的艺术目的,是崇高的、概念的、动态的和心理的。库马拉斯瓦米理论的内在观念是:“理想”的艺术是使观众的精神陷于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艺术经验的核心。在西方艺术中,画面通常被认为是在一个画框或通过一个窗户的观看,因此朝向观众,但东方图像实际上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心中,因此付诸于“空间”……湿婆之舞发生……在信徒的心里。
受库马拉斯瓦米亚洲艺术理论影响的有荣格学派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他1942年介绍凯奇阅读了库马拉斯瓦米有影响力的文集《艺术中自然的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in Art,1934),这本论文集比较了东方和西方艺术与精神性。这次邂逅改变了凯奇审美哲学的路线,并为他后来和铃木对禅宗的研究做了准备。凯奇终其一生,援引库马拉斯瓦米的训诫:艺术是以她的运作方式模仿自然。从这个训诫中,凯奇产生了排除西方结构化的作曲方式这一想法,为了聆听精神对自然自身的凝视,一种自我认识或“祷念”的自己。他把这种革命性影响的做法称为“作为过程的作曲”(Composition as Process)。
很清楚……结构是没有必要的……它不再是作曲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不是一种目的在于整合对立面的活动,而是一种以过程和本质上无目的为特色的活动。尽管被剥夺了控制力,心灵仍然存在。它能做什么?无所事事吗?一个曲子是无目的手段时会怎样?
芬诺洛萨、冈仓天心和库马拉斯瓦米在美国打下了亚洲艺术收藏和研究的基础,二战后数十年间,李雪曼(Sherman Lee)成为新的领衔人物。作为一名职业博物馆馆长,李雪曼加入了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的艺术与古迹部门,日本战败后,久负盛名的日本藏品以及日本通过当时对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和占领累积的亚洲艺术藏品,变成可以销售给美国个人和机构藏家。李雪曼为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收藏的收购,使得古代和经典的“国宝”(National Treasures)得以永存。这种姿态有助于抑制冷战时期对亚洲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感,因为它把亚洲文化呈现为本质上前现代的、静态的、温良的。李雪曼对于像高棉雕塑、北宋山水画等艺术形式本质上深思的面貌和简约风格的强调,影响了当代艺术家对于亚洲艺术的想法。阿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回顾了1954年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他写到:它们是有组织的和有机的,气韵盎然而又静止(Atmospheric and airless),内在而又超验……完整的、自制的(Self-contained)、绝对的、理性的、完美的、平静的(Serene)、缄默的、不朽的,以及宇宙的。莱因哈特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对于他来说,这些永恒和理想品质的中国水墨画,是他有意去解释并运用在他激进简约的单色画范式。莱因哈特把亚洲艺术定义为象征一个整体体系的——哲学的、冥想的、美学的、道德的——反映了美国有关亚洲艺术鉴赏的遗产,并证明艺术家如何将其和自己的创造目的互动。莱因哈特对中国山水画记述道:东方的角度源自于对“无法估量的广阔”(Immeasurable Vastness)和“事物无尽”(Endlessness of Things)之外的意识。并且当事物越近,它们就变得越小,观者最终在他们自己的心中迷失了自我。
三、关于传播
策展人依据作品和艺术家的文字来构建展览主题,这个项目(“第三种思想”主题展)也不例外。它依照艺术家的陈述和史实来呈现美国文化自我形构中关于亚洲想象的阐释和技巧。它不是全面的、详尽的,或者最权威的,由于物理条件的限制,将一种历史俯瞰转化成现实空间的展览,即使是附属的展览图录,都要求一种武断的分割和变化。我们的重点是视觉艺术,也突出了现代诗歌和散文、音乐、舞蹈的特定表达。建筑、设计、陶瓷、时装和流行艺术没有在这个项目的范围之内,部分是因为这些形式的亚洲影响被更广泛地接受。至于被遗漏的不少艺术家,希望未来的学者们能以这次研究为出发点,推进它众多潜在的发现方向。
展览按时间顺序和主题分七个部分。每部分探讨相互关联的艺术群体,他们共享了源自亚洲资源的特定的美学策略,从而形成艺术创作的概念方法。这些来源所包括的亚洲艺术风格或实践,在特定时间内流行于亚洲艺术、诗歌、哲学和玄学的翻译、评论和写作中。每部分展览的逻辑是从19世纪唯美主义到当代表演和装置艺术的艺术史运动的标准分类,比如从一个艺术家选择的视角,观看这个时期援引亚洲作为灵感的文献。图录章节符合这个展览布置的设计,从“唯美主义与日本:东方崇拜”开始。这部分是一组通过自然新宗教来发现亚洲哲学的艺术家专题,这种自然新宗教被波士顿周围的独神论派信徒(Unitarian,属于不信仰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派别)和先验论者所提升。这个圈子的成员都生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他们和一种特别亲近日本的唯美主义运动相联系,对日本的特别亲近源于康莫•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在1853-1854年到达日本。一些人受到了波士顿藏家和弗里尔美术馆亚洲艺术的藏品——在芬诺洛萨的劝说下收藏——的启发。一些人前往日本旅行,如约翰•拉•法厄(John La Farge),他提倡一种把日常生活的美理想化的风格,他借鉴了一种提升并使日常性和功利主义脱俗化的日本方法。(这样一种美学和哲学被冈仓天心吸收到《茶之书》中,这本书他题献给“拉法厄老师”。)
弗里尔的圈子包括托马斯•威尔墨•杜因(Thomas Wilmer Dewing)和流亡国外的惠斯勒,他的水性涂料的薄薄的外层使得人类和风景的形式接近于非物质的,唤起了“精神物质”,并与弗里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和日本的文人画与禅画的“气”相联系。《心灵的风景:关于自然的新观念》(Landscapes of the Mind: New Conceptions of Nature)追溯了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艺术家社团,他们提升了美国现代和抽象艺术的地位,同时援引了东亚的美学和哲学,后者认为自然尤其风景是意识的反映。这克服了传统西方观念把风景作为不朽的和永恒的形制,这些艺术家从中国和日本获得了把风景作为短暂形式和动态过程的观念。他们挪用了像水墨笔触的实践技术和来自中国山水画(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多视点的构图方法,中国山水画达到了一种暗示某种存在之外的超自然神秘和奇妙事物的力本论(Dynamism)。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教师与日本艺术专家道尔(Dow)来说,艺术家革命的核心所在处于中国与日本的传统艺术之中。他的手册《构图》影响了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一代学生,包括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她早期的水彩抽象系列(1915-1919)的私密尺度、色调层次和将风景作为内空间的诠释方法,都是来自于道尔的训练。这部分的高潮是以马克•托比(Mark Tobey)为中心成长的西北画派的画家群、实验性的康沃尔艺术学院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创始者理查德•E.富勒(Richard E. Fuller)。他们都把亚洲看作一种新文化的迫切资源和一种替代性价值,后者被莫里斯•格雷弗斯(Morris Graves)称之对“西方世界被高度技术化、理智化头脑”的拯救。
在1910年,美国对于经典亚洲文学、舞蹈、戏剧的翻译成为艺术家挪用和创新的另一种资源。“艾兹拉•庞德,现代诗和舞蹈剧:转译”(Ezra Pound, Modern Poetry, and Dance Theater: Transliterations),将庞德对中国和日本经典诗歌有潜在重要性的翻译连接起来,他的翻译以芬诺洛萨的笔记为基础,带来了现代英语文学的革命,抛弃了维多利亚式的过分渲染风格,转向简洁、具体的意象语言。庞德接受了中国和日本诗歌,将诗歌强有力的、独有的现实感的瞬间视觉化,并创造出概念的透明性,影响了伊藤道雄(Itō Michio)、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野口勇(Noguchi Isamu)的隐喻文学和舞蹈剧美学,他们在大战期间合作过。野口勇是下一部分《战后抽象艺术的亚洲维度:书法与玄学》(The Asian Dimensions of Postwar Abstract Art: Calligraphy and Metaphysics)的关键环节。书法笔触(Clligraphic Brushstroke)是抽象绘画的一种方法,它关注的是艺术家手的自发姿势(Spontaneous Gesture),这是习自论禅宗及其直接行动伦理的流行著作中有关笔墨(brush-and-ink)绘画和书法的东亚艺术。萨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菲利普•格斯顿(Philip Guston)、克莱恩•罗伯特•马瑟韦尔(Kline Robert Motherwell)、波洛克(Pollock)、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托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油画、水墨画和雕塑作品揭示了这一跨文化话语是如何启发了战后时期的创造性文化。在“行动绘画”统治抽象话语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松散的艺术团体,他们通过一种不同的抽象画风格,赋予亚洲关于存在与意识特定的玄学概念以一种普遍主义形式。西海岸,李•马利坎(Lee Mullican)和戈登•昂斯洛•福特(Gordon Onslow-Ford)打造了一种折衷主义的视觉哲学,他们想规避“自我表现”的快速姿势,这种“自我表现”试图恍惚似的呈现一种宇宙现实的简约秩序。
《佛教和新前卫艺术:凯奇禅,垮掉禅和禅》(Buddhism and the Neo-Avant-Garde: Cage Zen, Beat Zen, and Zen),介绍了三组重叠的艺术家和作者,他们保持了即使是与禅宗和大乘佛教的折衷主义联系,构成战后新前卫艺术的方法论和哲学影响。我们把这群体命名为“凯奇禅”,通过凯奇的调和性观念,联接了新达达、激浪派和偶发艺术;垮掉禅,叙述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以及其他参与垮掉运动的人创造的自发性写作和主体性模式如何挪用了佛教;起源于凯奇式和后垮掉派的旧金山湾区的概念艺术,把禅宗作为一种方法使用。禅宗修辞学给了这些艺术家和作家丢弃艺术意图和创作结构的理论框架;制造了关系动力学和以艺术行为作为中心的心理学的、美学的原则;并建立了纯粹的、未经调和的艺术如生活的本质经验。提莫西•李瑞(Timothy Leary)和金斯堡断言,迷幻药可以产生像“三昧”一样的神秘经验,这种经验使东方宗教和冥想的技巧与60年代的反文化结合起来。
《感性经验的艺术:纯粹抽象与狂喜的极少主义》(Art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Pure Abstraction and Ecstatic Minimalism)追溯了60年代美国艺术中亚洲修辞学新的复述,重新把艺术对象作为思考的焦点,其目标在于转变观者的意识状态。尤其是莱因哈特,他通过对佛教艺术、中国画、禅宗和道教哲学正式的学术研究,得出这样一种激进的结论。他的术语“纯粹抽象”描述了一种简约形式的单色调(Monochromatic Hues)美学以及单一的、重复的要求宁静专注的行为技巧,这种专注给诸如极少主义艺术家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和约翰•麦克劳林(John McLaughlin)等人的作品提供了一种精神阅读,观众的站位与艺术作为“场所”的遭遇,其特征我们称为“狂喜的极少主义”,即那些非字面主义者(Non-literalist)的极限主义,包括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沃尔特•德•马里安(Waltere De Maria)、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和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这些艺术家改变了从光效应事件到现象学过程的观看概念,并使持续性时间(物体的注视)成为本体论意识的一种媒介—一种洞悉狂喜的经验。相关的发展是极少音乐(Minimal music)。
《现代作品中的亚洲结构:音乐与哲学》章节,概述了东亚和南亚的音乐形式、作曲原则和乐器演奏法是如何有助于20世纪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尤其是北印度强调旋律发展而不是和声对比的器乐风格的冲击,对于约翰•科特兰(John Coltrane)的印度爵士乐风格是决定性的,他在1957年戒除了海洛因,遵照拉马克里希纳(Ramakrishna)的精神教导,和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一起研究印度器乐和即兴创作原则。一定程度上,通过科特兰,印度斯坦的拉格成为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特里•莱利(Terry Riley)和杨(Young)极少音乐的试金石。杨通过低音和声学、长时间延续的、持续的音符和有机的、即兴的风格改革了音乐会音乐。对这些艺术家来说,音乐经验是一种意识转化行为,将演奏者和听众带入到一种杨称其为“心灵的低沉状态”。
我们的历史结束于《行为艺术和经验的在场:存在的不规则方式》(Performance Art and the Experiential Prensent: Irregular Ways of Being),这部分集中在七八十年代。这部分艺术家是一种亚洲祷念戒规和冥想技术的高级实践者,他们已经在亚洲国家度过一段时间;或者像金•琼斯(Kim Jones)那样,服务于越南。像谢德庆(Tehching Hsieh)、林达•蒙塔娜(Linda Montano)、帕珀(Piper)和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这样的艺术家,则探索对冥想的虔诚技巧和政治抵抗体系的极端容忍性——他们宣称身体是一个经验地带。随着60年代反文化的艺术家时代到来,这些艺术家反对亚洲前线的冷战政策,他们使用被美国作为打击靶子的极其哲学的、精神的或者政治的原则,并批判整个殖民冒险。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是这段历史的中心人物,从1958-1968年,他住在日本京都,致力于禅宗冥想、神道教仪式和能乐的研究与实践。拜尔斯折中地吸收能乐缓慢的、风格化的运动和超自然领域的戏剧,创作出一种当代表演艺术,这种表演是非常隐喻和仪式化的。
《詹姆斯•李•拜尔斯之死》(The Death of James Lee Byars)(1982/1994)呈现出一个黄金叶室——这使人联想到桃山武士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著名的黄金茶室——在这里,艺术家表演了他的“死亡”,他懒洋洋地躺在一个黄金叶石棺上,然后留下水晶作为一种身体的痕迹。这个微微发光的空间唤起一种非规则存在的超俗状态的沉思—不仅是超验的死亡,还是对奇异东方的祈灵。所有参展艺术家都生于1960年以前。对于包括在此次展览和图录中的这些艺术家,海外旅行是一种转化性经验,他们的研究是国际化及深深内在化的。当植根于一种东方主义传统,他们的旅行部分是逃避,部分是受启。东方传统通过观念、实践、关系和再现为一种替代性的更高一级“他者”的器物的选择性挪用,来寻求自我优化。1990年以后,艺术家的旅行大多不是为了个人研究,更多是为参加过去20年激增的双年展及其他国际展览。这种发展与全球化并行,结果知识传播的方式被转变。早期一代艺术家将知识理想化,当代艺术家更重视信息。
正如欧文所说:
以前,艺术家们感兴趣的是制造艺术。90年代以后,他们的兴趣是制造文化。
从知识到信息、从艺术到文化的这种转变,是理解本次展览中美国艺术思想轨迹的关键。另一种因素是后殖民理论和东方主义批判的兴起,它支持了展览为何结束于此。它们对定义东方学过程的介绍,有助于把现象历史化,从而影响它的结束。
我们邀请安•汉密尔顿(Ann Hamilton)用古根海姆博物馆中央大厅的实地装置来回应这个展览计划。她的作品《人类的运输》(human carriage,2009年)的组成有两个因素:“重物”(Weights)由许多切碎的书和镶嵌在一个白色丝制的“响铃支架”上的一对西藏铜钹制成,沿着圆厅螺旋式楼梯倾泻下来,用它随机的钟声唤醒观众。她把《人类的运输》描述为被大量吸收的阅读文本和旅行被纳入心灵接受中的传输和转换过程的隐喻。在早期的电子邮件中,她想到的是这一委托正在激发她的创造性想法。她深思了“关于传输的中心问题”:核心是身体识别—或许连接词—吸收—被传输的东西的组成是如何成为可以被大量吸收的具体化知识。说来似乎很简单,但这难道不是对如此复杂的展览计划的挑战?我们怎样—以何种方式,我们才终至于认识什么正被传输的东西?—“身体“去向何处?汉米尔顿关注于“阅读和翻译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阅读的传播……它没有留下物质痕迹,但它可以永远的改变你。”她的洞见提供了一种呈现在“第三种思想”中对艺术看和理解的钥匙。它没有说明其文本来源,它只是体现它们。亚洲作为方法,揭示为一种在体验时间中的自我和空间中心灵的一种革命性方式。
作者: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ra Munroe)
译者:朱其,姚远
原文出版: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2009
译文来源:《当代艺术理论前沿》(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