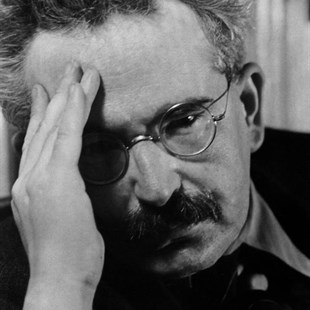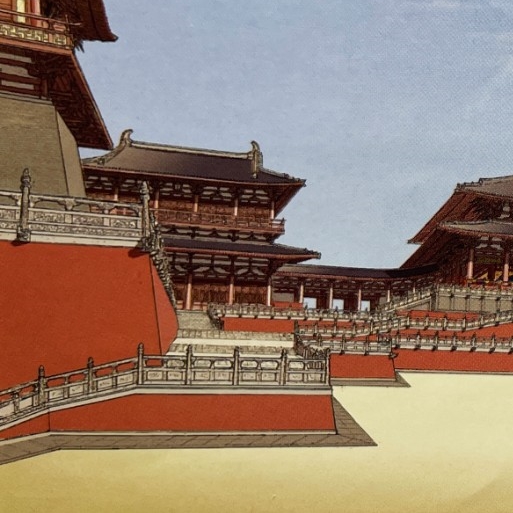现代主义远不止是文学和艺术之事。如今它几乎涵盖了我们的文化中尚有活力的一切领域。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种历史性地出现的新鲜事物。西方文明并不是回过头来质疑它自己基础的第一个文明,不过它确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文明。我将现代主义等同于始自哲学家康德(Kant)的那种自我批判倾向的强化和加剧。由于康德是第一个批判批判手段本身的人,所以我将他视为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者。
就我所知,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一个学科的特有方式批判学科本身,不是为了颠覆它,而是为了更为牢固地奠定它的能力范围。康德运用逻辑以确定逻辑的边界,尽管他从逻辑旧有的管辖权范围撤回了不少,但在仍然属于逻辑的范围内,它的基础却更为坚固了。
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来自启蒙运动的批判传统,但并不等同于这一传统。启蒙运动从外部实施批判,就像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所做的那样;而现代主义却从内部展开批判,通过被批判的东西的方法本身加以批判。这种新兴的批判方式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哲学就其定义而言就是批判;但18世纪以降,这种批判开始进入许多其他领域。每一个正式的社会活动领域都开始被要求奠定在更为合理的理由之上,而康德式的自我批判,作为率先在哲学领域中出现的对此种要求的回应,最终被召唤要在远远超出哲学的诸领域内来满足并诠释这种要求。
我们知道像宗教那样的活动领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宗教本身不利于康德式的、为了证明自己而发动的内在批判。艺术初看起来与宗教相似。启蒙运动拒斥了艺术所能承担的所有严肃任务,艺术似乎正在被同化为纯粹而又简单的娱乐,而娱乐则跟宗教一样,似乎正在被同化为一种治疗功能。唯有通过展示艺术所提供的那类经验拥有的自身所特有的、无法得自于任何别的活动领域的价值,艺术才能从这种降格中拯救自己。
于是,每一种艺术都得实施这种自我证明。需要展示的不仅是一般艺术中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而且还是每一种特殊艺术中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每一种艺术都得通过其自身的实践与作品来确定专属于它的效果。诚然,在这么做时,每一种艺术都会缩小它的能力范围,但与此同时,它亦将使这一范围内所保有的东西更为可靠。
每一种艺术独特而又恰当的能力范围正好与其媒介的性质中所有独特的东西一致。于是自我批判的任务成了要从每一种艺术的特殊效果中排除任何可能从别的艺术媒介中借来的或经由别的艺术媒介而获得的效果。因此,每一种艺术都将成为“纯粹的”,并在“纯粹性”中找到其品质标准及其独立性的保证。“纯粹性”意味着自我界定,而艺术中的自我批判则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界定。
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艺术掩饰了艺术的媒介,利用艺术来掩盖艺术;现代主义则运用艺术来提醒艺术。构成绘画媒介的局限性——扁平的表面、基底的形状、颜料的属性——在老大师们那里是被当作一些消极因素来加以对待的,只能含蓄地或间接地得到承认。在现代主义作品里,同样的这些局限性却被视为积极因素,而且得到公开承认。马奈(Manet)的绘画由于其公开宣布画面的平面性的大胆直率而成为第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马奈的启发下,印象派画家放弃了绘画底色与半透明色,使赤裸裸的事实暴露在观众眼前:他们所使用的色彩就是由从颜料管或颜料盒中挤出来的颜料构成的。塞尚则放弃了逼真性或正确性,以便使他的素描或构图更为明确地吻合画布的矩形形状。
然而,正是对绘画表面那不可回避的平面性的强调,使现代主义绘画艺术得以据此批判并界定自身,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关键。因为只有平面性是绘画艺术独一无二的和专属的特征。绘画的封闭形状是一种限定条件或规范,与舞台艺术共享;色彩则是不仅与剧场,而且与雕塑共享的规范或手段。由于平面性是绘画不曾与其他任何艺术共享的唯一特征,因而现代主义绘画就朝着平面性而非任何别的方向发展。
老大师们已经意识到保护被称为图画平面的完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要在三维空间最生动的错觉之下保证平面性的持久在场。这里涉及的明显矛盾对他们的艺术的成功来说极其重要,事实上,它对于一切绘画艺术而言都极其重要。现代主义者们既没有回避但也没有解决这一矛盾;毋宁说,他们颠倒了其中的关系。观众在被迫注意到平面性所包含的东西之前,而不是之后,首先就注意到了绘画的平面性。人们在看到绘画本身之前,往往先看到老大师画中所画的东西,而人们看到的现代主义绘画首先就是一幅画本身。当然,这是观看任何种类的绘画,不管是老大师的还是现代主义的绘画的最佳方式,然而,现代主义却将它强化为唯一的和必然的方式。现代主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是自我批判的成功。
最近的现代主义绘画并没有从原则上抛弃可辨认对象的再现。它从原则上加以抛弃的只是可辨认对象得以占据其中的那类空间的再现。抽象性或非具象性,就其本身来说还没有证明自己是绘画艺术自我批判中一个完全必然的时刻,尽管像康定斯基(Kandinsky)和蒙德里安(Mondrian)之类的杰出的艺术家认为如此。就此而论,再现或描绘并没有削弱绘画艺术独一无二的特性;削弱这一特性的倒是对被再现之物的诸种联想。所有的可辨认现实(包括绘画本身)都存在于三维空间中,而对可辨认现实的最微妙的暗示都足以引起人们对这类空间的联想。一个人体或一只茶杯不完全的轮廓就会引发这样的联想,并通过这种联想将绘画空间从真实的二维空间中抽离出来,恰恰是这一二维空间才构成绘画之为一种艺术的独立性的保证。因为,正如我早已说过的,三维性属于雕塑的地盘。为了获得自主性,绘画首先已经使自己从可能与雕塑共享的一切中剥离出来,而且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而不是——我再重复一遍——排除再现性或文学性的东西,使绘画走向了抽象。
与此同时,现代主义绘画表明,恰恰是因为它对雕塑的抵抗,才使得它仍然牢固地维系于传统之中,而这一点与表面上看起来的正好相反。因为对雕塑的抵抗可以追溯到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很久。西方绘画,就其自然主义特征而言,得益于雕塑者甚多。雕塑最早教会了绘画如何运用明暗及立体造型法来产生浮雕错觉,甚至教会了绘画如何在一种深度空间的互补错觉中来安排这种浮雕错觉。然而,西方绘画的某些壮举却源于过去的四百年中它从雕塑中摆脱出来的努力。这种努力始于16世纪的威尼斯,其后是在17世纪的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最早是以色彩的名义进行的。18世纪的大卫(David)试图复兴雕塑式的绘画,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将绘画从装饰性的扁平化过程中拯救出来;不断地强调色彩似乎必然会导致这一扁平化过程。但是,大卫本人最好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那些肖像画),其力量恰恰在于它们的色彩。他忠实的学生安格尔(Ingres),尽管比大卫更为一贯地贬低色彩,却画出了14世纪以来西方成熟的绘画中最为扁平、最少雕塑性的肖像。因此,到19世纪中叶,绘画中所有野心勃勃的倾向都集中于反雕塑的方向,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
现代主义在使这种反雕塑方向持续下去的同时,也使它变得越来越自觉。马奈与印象派画家以降,这个反雕塑的问题已经不再被定义为一个色彩对抗素描的问题,而是纯粹视觉经验对抗由触觉联想校正或修正的视觉经验的问题。正是在纯粹而又真实的视觉经验,而不是在色彩的名义下,印象派才着手瓦解明暗法、立体造型法,以及绘画中所有似乎意味着雕塑的东西。而且正是在雕塑的名义下,伴随着明暗法与立体造型法,塞尚以及追随着他的立体派画家起而反对印象派,正如大卫反对过法拉戈纳尔(Fragonard)一样。然而,正如大卫与安格尔的反动,悖论性地在一种比过去更少雕塑性的绘画中达到顶点一样,立体派的反革命最后也以一种比乔托(Giotto)和契马布埃(Cimabue)以来西方绘画史上的任何绘画都更为扁平的形式而告终——它是如此扁平,以至几乎无法包含任何可辨认的形象。
与此同时,绘画艺术的其他主要规范也已随着现代主义的攻击而走上了一条即使还不能说是惊人却同样彻底的修正之路。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展示绘画的封闭形状或画框的规范是如何为连续几代现代主义画家们松动、收紧,接着又松动、分离,随后又收紧的整个历程,也无法展示关于绘画的最后加工与颜料质地,以及关于明度与色彩对比的规范是如何得到修正与再修正的。所有的这些规范都经历了挑战,不仅是为了新的表现,而且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将它们当作规范来加以展示。通过展示这些规范,它们也就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证明过程并没有完成,而它变得越来越深入这一事实,解释了最近的抽象绘画中那种激烈的简化现象,也解释了这些绘画中同样激烈的复杂化现象。
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都不是任性或任意之举。相反,一个学科的规范越是严格地得到界定,它们也就越不可能任由人们走向多个方向了。绘画的本质规范或常规同时也是一幅画必须遵守的、绘画被当作一幅画来加以经验的限定条件。现代主义已经发现,这些限定(边界)可以被无限地向后推——直到一幅画不再成为一幅画,转而成为一个任意的物品时为止;但是,现代主义也发现,这些限定(边界)被推得越远,它们也就必须越是明确地得到遵守和显示。蒙德里安的那些交叉的黑线与色块似乎很难构成一幅画,但是它们却通过如此紧密地呼应图画的框架形状,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力量与完整性,硬使图画的框架形状成为一种调节规范。随着时间的消逝,蒙德里安的艺术证明了,它远不会招致任意性的危险,相反却似乎是过于规矩,过于传统,在某些方面依然受到常规的限制。一旦我们习惯了它彻底的抽象性,我们就会认识到,例如它在色彩的运用和对边框的服从上,就比莫奈(Monet)的后期作品更为保守。
在勾勒出现代主义绘画的基本原理时,我不得不作些简化,稍作夸张,我希望这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主义绘画走向的平面性绝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平面性。对图画平面的高度敏感性或许不再允许出现雕塑式的错觉,或逼真画(trompe-l'oeil),但它确实而且也必须允许出现视觉上的错觉。落在画布上的第一笔就会毁坏它真实的和彻底的平面性,而像蒙德里安之类的艺术家施加于画布上的笔迹的最终结果,也仍然是一种暗示着三维性的错觉。只不过如今它是严格图画意义上的和视觉意义上的三维性。老大师们创造了一种人们可以设想走入其中的深度空间的错觉,但是,现代主义画家所创造的那个类似的错觉只是可看的错觉,只能用眼睛来“上下游走”,不管是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
最近的抽象绘画试图实现印象派所坚持的观念,即视觉乃是一种完全且又彻底的绘画艺术所能唤起的唯一感觉。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也就能认识到,印象派,至少是新印象派,在与科学调情时并不是全然误入歧途。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康德式的自我批判如今已在科学而非哲学中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而当它开始被运用于艺术时,艺术在其精神实质方面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科学方法——比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贝蒂(Alberti)、乌切洛(Uccello)、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dellaFrancesca)或莱奥纳多(Leonardo)更接近科学。视觉艺术应该完全将自己限定在视觉经验中被给予的东西,却不参照任何别的经验秩序中被给予的东西,这乃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科学一致性的原则之上。
只有科学方法会要求或可能要求一种情境必须以与其被提出来的术语完全相同的术语来加以解决。但是这种一致性不会给予美学质量任何保证,而过去七八十年中最好的艺术都越来越紧密地趋向这种一致性,这一事实与这一规律并不矛盾。从艺术自身的角度看,它与科学的聚合只是一种偶遇罢了;艺术与科学都没有真的赋予或确保对方任何东西,这一点仍然跟过去一样。它们之间的聚合确实能够表明的,却是现代主义艺术隶属于同现代科学一样的那种特殊的文化趋势的深刻程度。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这一点极其重要。
我们还应该看到,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自我批判一直是以一种自发的,主要还是下意识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我早就指出的那样,它完全是一个内在于实践的实践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理论课题。人们能听到现代主义艺术中有不少所谓的“计划”,但是现代主义绘画的计划性并不比文艺复兴绘画或学院派绘画的计划性更强。除了少数像蒙德里安这样的艺术家例外,现代主义的大师们并不比柯罗(Corot)具有更多固定不变的艺术理念。某些倾向性、某些断言与强调、某些拒斥与节制似乎是必要的,因为通往更强、更具表现性的艺术的道路必须经历这些东西。过去现代主义者的直接目标首先是个人目标,现在仍然如此,而他们作品的真实性及其成功首先还是个人的真实性和个人的成功。只有当几十年过去以后,当人们已经累积起了大量的个人绘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出现代主义绘画总的自我批判倾向。没有一个艺术家过去意识到这一点,现在也是如此,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还能自由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艺术在现代主义条件下,跟过去一样向前推进。
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那就是:现代主义从来都不是有意要跟过去决裂,现在也一样。它也许意味着对传统的一种转移,一种阐明,但也意味着这一传统的进一步演化。现代主义艺术延续着过去,没有缺口,也没有断裂。无论它可能终结于何处,它都永远可以根据过去的东西加以了解。自其最初出现以来,图画的制作一直受到我所提及的那些规范的控制。旧石器时代的画家或雕刻家可以无视框架的规范,且以一种真正雕塑式的方法处理表面,只是因为他是在制像而不是在画画,他可以在某种基底,如一堵岩墙、一片兽骨、一只牛角或是一块石头之上工作,其范围和表面由大自然任意给定。但是,图画的制作却意味着画家首先是有意地制作或选择一个扁平的表面,而且是有意识地限制和划定它的范围。这种有意正是现代主义绘画反复述说的东西,亦即艺术的限定条件正是人类的条件这一事实。
不过,我愿重复一下,现代主义艺术并非对理论的验证。毋宁说,它碰巧将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经验上的可能性,在这么做时,它也检验了许多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艺术鉴赏的实际相吻合的程度。只有从这一点看,现代主义才可以被认为具有颠覆性。某些我们通常以为属于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本质的要素,却被如下事实证明并非本质:现代主义绘画抛弃了这些要素,却照样提供了不折不扣的艺术经验。这种展示并没有动摇我们关于艺术的大多数古老的价值判断,这一事实使得这一展示变得更具说服力。现代主义也许与乌切洛、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埃尔·格列柯(ElGreco)、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delaTour),甚至是弗美尔(Vermeer)的名声的复活有关。现代主义当然确认了乔托名望的复苏,即使这一点并非始自现代主义。不过它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莱奥纳多、拉斐尔(Raphael)、提香(Titian)、鲁本斯(Rubens)、伦勃朗(Rembrandt),或是华托(Watteau)的地位。现代主义只是表明了,尽管过去的人们欣赏这些大师确实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给出的理由却经常是错误的或不相关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艺术批评与艺术史滞后于现代主义艺术,正如它们也曾滞后于前现代主义艺术一样。人们已经写下的关于现代主义艺术下的东西,大多仍属于新闻报道,而不是艺术批评或艺术史。它属于新闻报道,属于那个千年情结,我们今天如此众多的记者们以及从事新闻业的知识分子们仍然忍受着这一情结之苦。这一情结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每一个新阶段都必须被呼唤为艺术中一种划时代的新开端,从而与过去的所有习俗和常规一刀两断。每一次,一种艺术被期望着要与过去的艺术如此不同,被期望着要跟一切实践的或趣味的规范说再见,以至于每个人不管他渊雅博洽还是孤陋寡闻,都能对它说个甲乙丙丁。而每一次,当人们所说的那个现代主义阶段终于又回到了趣味与传统的那种清晰可感的连续性之中时,这种期望都要落空。
没有什么比连续性断裂的观念更加远离我们时代的本真艺术了。艺术是,并且首先是连续性,没有连续性,艺术就无法想象。没有艺术的过去,没有想要维持卓越性标准的需求与冲动,现代主义艺术就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正当性。
后记(1978年)
上面的文字最早发表于1960年,是由美国之声(theVoiceofAmerica)出版的系列小册子当中的一部分,曾在同一年春天在同一家广播机构播出过。在经过极少许字眼的更动后,它重印于巴黎《艺术与文学》(ArtandLiterature)1965年春季号上,后来则被收入戈莱格里·巴特科克(GregoryBattcock)1966年主编的文选《新艺术》(TheNewArt)中。
我想借此机会更正一个错误,一个有关阐释非关事实的错误。许多读者(尽管远不是全部),似乎把我在这里勾勒出来的现代艺术的“基本原理”视为作者本人所采纳的立场,也就是认为作者所描述的当然也是他所宣扬的。这或许是文风或修辞之过。然而,仔细地阅读一下他写的东西,就会发现,他绝没有表示他赞成、信奉他所描绘的东西(在“纯粹”和“纯粹性”这两个词上打上的引号可以清楚无误地表明这一点)。作者试图部分地解释,过去一百多年里最好的艺术是如何产生的,但他并不是在暗示它不得不如此产生,更不是在暗示将来最好的艺术也必须如此产生。“纯粹”艺术只是一种管用的错觉,但这并没有使它不再是一种错觉。它继续管用这种可能性同样也不能使它不再是错觉。
有关我写了什么的演绎还有很多,多数都显得很可笑:什么我认为平面性以及对平面的划定不仅是绘画艺术的限定条件,还是绘画艺术的美学质量的标准;什么一件艺术品对一种艺术的自我批判推进得越远,这件艺术品就越好,等等。这种使我——事实上是使任何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哲学家或艺术史家,以这种方式做出审美判断,表达的更多的是他或她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我的意思。
作者: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译者:沈语冰
原文刊载于《油画艺术》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