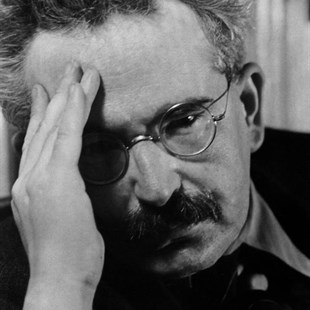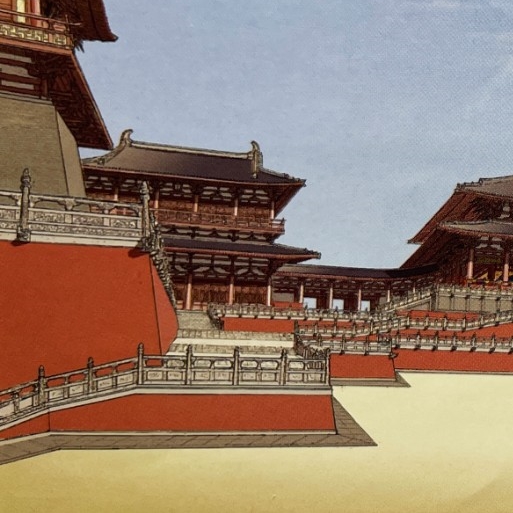四
我们在把艺术作品定义为一种“要求人们对之作审美体验的人工产品”时,首次碰到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别。科学家虽处理自然现象,但他可以立即着手分析这些现象。人文学家虽处理人类行动和作品,但他必须从事带有综合性和主观性的心理活动:他必须在内心重新体验人类的行动,重新创造人类的作品。实际上,正是通过这个过程,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真正对象才得以形成。显然,哲学史家或雕刻史家关注书籍和雕像并不在于它们是物质存在,而在于其中的含义。同样明显的是,我们只有通过复现,从而不折不扣地“领会”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雕像中所包涵的艺术观念,才能理解这种含义。
因此,艺术史家要时时对自己的“材料”进行理性的考古式分析,就象任何自然科学或天文学研究那样精确、广泛和错综复杂。但是,他凭籍直觉的审美再创造,组织自己的“材料”。【11】这种再创造包括对于“特质”的知觉与评价,如同任何“普通人”在观看图画或聆听交响乐时具有的那种知觉和评价一样。
如果说艺术史研究的真正对象是通过非理性的、主观的过程形成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将艺术史建设成一门应受尊重的学术性的学科呢?
当然,我们求助艺术史业已采用或可以采用的种种科学方法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对材料的化学分析,X光,紫外线,红外线,放大照片,诸如此类的手段都是十分有用的,但它们的用途跟基本的方法问题无关。一项指出一幅据称是中世纪的细密画使用的是19世纪以后才发明的颜料的陈述可以解决一个艺术史问题,但不是一个艺术史陈述。它虽以化学分析和化学史为基础,但不适用于作为艺术作品的细密画,而适用于作为物体的细密画,因而倒可用于伪造的遗嘱。此外,从方法上看,使用X光,放大照片等跟使用眼镜或放大镜没有差异。借助这些手段,艺术史家可以看到不用这些手段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他必须“从风格上”解释这些东西,跟解释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无异。
真正的答案在于,直觉的审美再创造跟考古式研究互为关联,从而又一次形成我们所谓的“有机情境”。认为艺术史家首先经过再创造的综合形成其对象,然后着手考古式研究一就象先买火车票后上车一样,这不符合实情。其实,这两个过程并非鱼贯而行,而是互相渗透。不仅再创造的综合可以成为考古式研究的基础,反过来考古式研究也可以成为再创造过程的基础:两者互相限定,互相修正。
任何人面对一件艺术作品。不论是从审美的角度对它进行再创造,还是从理性上对它进行研究,难免都会受到作品三个构成要素一物质形式、观念(即造型艺术中的题材)和内容的影响。依照伪印象主义理论,“色彩和形式就是色彩和形式,仅此而已”,这种理论完全不对。我们在审美体验中实现的乃是这三种要素的统一,它们会一起进入所谓的艺术审美享受之中。
因此,对于艺术作品再创造的体验不但有赖于观看者天生的感受力和所受的视觉训练,而且有赖于他的文化素质。现实中根本没有完全“纯真”的观看者。中世纪的“纯真”观看者必须学习许多东西,忘掉一些东西,才能欣赏古典雕塑和建筑,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纯真”观看者必须忘掉许多东西,学习一些东西,才能欣赏中世纪艺术,更不消说欣赏原始艺术了。因此,“纯真”的观看者不仅欣赏艺术作品,而且不知不觉地对它进行评价与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假如他毫不在乎自己的评价和解释正确与否,并且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文化素质,尽管水平不高,但实际上对他体验对象有帮助,那么就没人会责怪他。
“纯真”的观看者与艺术史家不同,因为,艺术史家意识到情境。他知道,他那不尽人意的文化素养与其他国家和时代的人们的文化素养不会融洽无间。所以,他尽其所能地增长学识,努力使之适应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创作环境。他不但要收集和考证所有关于创作手段,创作条件,创作年代,作者身份,预定日的等可用的实际资料,而且要将他研究的作品与其他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同时还要研究反映这件作品所属的国家和时代的审美标准之类的著述,以便对它的特质作出更“客观”的评价。他要阅读有关神学或神话学古藉,以辨认作品的题材,他还要进一步努力确定作品的历史地位,并且把它的制作者的个人贡献跟前人和同代人的贡献区别开来。他要研究形式原理,这种原理支配着人们对可见世界的描绘,或在建筑中支配着人们对所谓的结构特征的处理,由此建立“母题”史。他要考察文献资料的影响和独立的再现传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便建立图像公式或“类型”史。最后他要竭尽全力熟悉其他时代和国家的社会的,宗教的和哲学的态度,以便矫正他对内容的主观感受。【12】但是,在他从事这一切活动时,他的审美知觉本身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使之越来越适应作品原来的“意图”。因此,艺术史家不同于“纯真”的艺术爱好者,他并不是要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建造一种理性的上层结构,而是要深化他那再创造的体验,以跟他的考古研究成果相吻合,同时继续将他的考古研究成果对照他那再创造的体验进行检验。【13】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说过:“两弱相依汇为一强。”【14】拱的哪一半都不能独立,只有整个拱才能支撑重量。同样,考古研究如果离开审美再创造,便盲目空洞,而审美再创造如果离开考古研究,便缺乏理性,常常会误入歧途。然而,这两方面“互相依靠”就能支撑那“有意义的系统”即历史的纲领。
正如上文所说,对于人们“纯真”地欣赏艺术作品,即按照自己的看法不假深思地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价和解释,谁都不能加以指责。但是,人文学家对于所谓的“欣赏主义”[appreciationism]深表怀疑。欣赏主义教导无知的人们,要理解艺术,不要为那些古典语言,讨厌的历史方法及尘封垢积的故纸堆伤神费事。他们恰恰由于未加纠正纯真的缺陷而使其丧失动人之处。
我们不应将“欣赏主义”与“鉴赏能力”和“艺术理论”混为一谈。鉴赏家是收藏家,博物馆长或专家,他们献身学术,确定艺术作品的创作日期、作者和出处,评价艺术作品的特质和境况,从不驰心旁鹜。他们与艺术史家并无原则上的区别,只是侧重面不同,各有自己的明确任务,这颇似医学上的诊断家与研究者的区别。鉴赏家往往强调我上文试图描述的那个复杂过程中的再创造一面,把建立历史概念摆在次要的位置上:而从较狭义的,或学院的意义上说的艺术史家。其侧重面往往与此相反。不过,对“癌症”的简明诊断,倘若无误,便包含着医学研究者可以告诉我们有关癌症的一切,因而经得起其后的科学分析的检验;同样,对于“约1650年的伦勃朗的作品”的简明诊断,倘若无误,便包含了艺术史家可以告诉我们的一切,即关于这幅画的形式价值,主题解释,反映17世纪荷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现伦勃朗个性的方式;这个诊断不愧是较狭义意义上的艺术史家作出的批评。因此,我们也许可将鉴赏家称为寡言的艺术史家[laconic art historiam],而将艺术史家称为多言的鉴赏家[loquacious connisseur]。实际上,在这两种类型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为他们自认为非本行的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5】
但另一方面,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或美学相对——之于艺术史,恰如诗学和修辞学之于文学史。
由于艺术史家的对象是在一种再创造的审美综合中形成的,所以艺术史家在试图描述他所研究的作品中所谓的风格结构时,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困难。由于他必须将这些作品视作内心体验的对象,而非物质对象或物质对象的替身,因此根据几何公式,波长和静态方程表示形状、色彩和结构特征,或者运用人体解剖方法描述人体姿态都是无益的一即使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另一方面,艺术史家的内心体验不是主观随意的,艺术家的合目的活动已经为他确定了轮廓,他决不可仅限于描述他个人对艺术作品的印象,这跟诗人不同,诗人可以描述他对一片风景的印象,或对一只夜莺的歌声的印象。
那么,我们只能用一种再建构性[re-con-strutive]术语来描述艺术史的对象,而这种再建构性术语如同艺术史家的体验是再创造的一样。它既不能把风格特征描述为可估量或可确定的材料,也不能描述为主观反应的刺激物,它必须把风格特征描述为揭示种种艺术“意图”的明证。所以,我们只能从选择的角度概述这些“意图”:必须假定一种情境[situation],在这种情境中,作品制作者可以采纳多种创作程序,即,他面临着一个在多种表现方式中进行选择的问题。这样看来,艺术史家所使用的术语便将作品的种种风格特征解释为对一般的“艺术问题”的种种特定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我们现代术语的情况,而且连我们在16世纪著述中见到的rilievo[浮雕法],sfumato[渲晕法]之类的术语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说某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人物是“塑造性的”,某幅中国画中的人物“有体积而无块面”[having volume but no mass](因为缺乏“立体感”),那么我们是在把这些人物解释为对同一问题即可以概述为“体积单位(实体)[volumeteric units(bodies)]对无限延展(空间)[illimited expanse(space)]”的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将把线条用作“轮廓线”[contour]的方式和把线条用作——引用巴尔扎克的话——“le moyen par lequer l’homme se rend coupte de l’effet de la lumiere sur les objects”[描绘物体上各种光线效果的方式]区别开来,那么我们指的是相同的问题,同时特别强调了另一个问题:“线条对色域”。我们细想一下,便会弄清,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些有限的基本问题,它们互相联系,一方面产生无穷的其次与再其次的问题,另一方面最终都源于同一个基本的对立:分立性对连续性。【16】
把“艺术问题”公式化和系统化——当然这些问题并不限于纯形式价值范围,同时也包括题材和内容的“风格结构”——从而建立一种“艺术科学的基本概念[KunstwissensehaftlicheGrund-begrtiffe]体系是艺术理论而非艺术史的任务。然而,我们在此第三次遇到了我们所谓的“有机情境”。如上文所述,艺术史家倘若不用包含着一般理论概念的术语重构艺术意图,就难以描述他那再创造体验的对象。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艺术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果没有历史的例证,艺术理论依旧是一幅关于抽象的共相世界的粗陋图式。但另一方面,艺术理论家不论是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或新经院哲学家的认识论角度,还是从格式塔心理学[Gastaltpsychlogie]的角度研究他的课题,【17】倘若不求助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艺术作品,就无法建立一般概念体系;然而,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艺术史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果没有理论定向,艺术史依旧是一堆散乱的个体。
如果我们说鉴赏家是寡言的艺术史家,艺术史家是多言的鉴赏家,那么艺术史家跟艺术理论家的关系则可比作一对邻居,他们共同享有同一地区的狩猎权。一家有枪,一家有弹药。他们双方如果都认识到这种合作条件,就不至于愚蠢失策。有人认为,假如理论得不到经验学科的迎候,便会象魔鬼一样,从烟囱入室,搞乱家具,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同样,假如历史得不到处理同类现象的理论学科的迎候,便会象一群耗子,潜入地窖,钻洞毁基。
五
我们认为,艺术史理应列入人文科学的行列。可是,人文科学本身有什么用处呢?无可否认,人文科学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且也应该承认人文科学只关注往昔。有人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从事这种没有实际用处的研究?为什么要关注往昔呢?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我们对现实[reality]感兴趣。不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论数学还是哲学,它们看上去都没有实际用处,所以古人称之为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的生活],与vita activa[行动的生活]相对。然而,沉思的生活是否比行动的生活更不现实呢?或者更准确地说,沉思的生活对我们所谓的现实所作出的贡献是否比行动的生活所作出的贡献逊色呢?
某个人用1美元纸币交换25个苹果,他的行为符合某种信仰,服从了一种理论学说,正如中世纪人购买赎罪券一样。某个人被汽车撞倒就等于是被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撞倒。过着沉思生活的人必然要影响人的行动,正如人的行动的生活必然要影响人的思想一样。哲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历史学说和各种各样的思想与发现,都业已改变并且继续在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即使是仅仅从事传播知识或学间的人,也以其谦逊的方式参与着创造现实的活动,人文主义的敌人可能比它的朋友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事实,【18】我们无法仅从行动的角度想象我们的世界。正如经院哲学家所说,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行动和思想的合一”。至于我们的现实,只能将其看作是这两种生活互相渗透的一个产物。
但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往昔呢?我的回答与上面相同:因为我们对现实感兴趣。最现实的东西莫过于现在。一个小时以前,这个讲座属于未来,四分钟之后,它将属于过去。我说某人被汽车撞倒就等于是被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撞倒的时候,大可以说他是被欧几里德[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拉瓦锡[Lavoisier]撞倒的。
我们要把握现实,就得超脱现在。哲学和数学通过一种从定义上说不受时间制约的媒介,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藉以超脱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则通过创造那些我所说的“自然宇宙”和“文化宇宙”的时空结构而超脱现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接触到了可能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最基本的区别。自然科学观察有时限的自然活动过程,并试图理解这些过程赖以展开的无时限的法则。物理学的观察只着眼于某物“发生”之处,即,发生变化之处或通过实验方式使之发生变化之处。然而,这些变化最终也要用数学公式将之符号化。但是,人文科学没有这样的任务,无需捕捉转瞬即逝的东西,它们的任务是让失去生命的东西获得新生,要不然,这些东西仍旧会处于僵化状态。人文科学并不处理暂时的现象,并不让时间中止,而是进入了一个时间已经自动停息的领域,并且努力使时间重新运转。人文科学虽然盯着那些我所说的“源自时间长河”的静止不动的人类记录,但它们努力捕捉这些记录所赖以产生并成为现时状况的活动过程。
因此,人文科学并不是要将转瞬即逝的事件化作静态的法则,而是要赋予静态的记录以勃勃生机,在这一点上,人文科学服自然科学没有矛盾,反而互相补充。事实上,这两门科学互为前提,互有所求。科学——这里就这个术语的真正意义而言,是对知识的平静而自主的追求,而非某种屈从于“实用”目的的东西——和人文科学是孪生姊妹,她们共同诞生于我们可以正确地称之为对世界和人的发现(或从更广的历史角度来看,也可称之为再发现)的那个[文艺复兴]运动中。正如她们一起诞生,一起再生一样,要是命运注定如此的话,她们也将一起死亡,一起复活。如果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文明[anthropocratic civilization]走向——看来似乎如此——一个“颠倒的中世纪”,即把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颠倒为恶魔政治,那么,不仅是人文科学,而且连我们所称的自然科学都将消亡,残留的只有为次于人者的旨意服务的东西。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文主义的终结,普罗米修斯可以被缚,可以遭受酷刑,但他点燃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在拉丁语中,seientia和eruditio——在英语中相应的是knowledge[知识]和learning[学识]——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scientia和knowledge表示一种心灵财富[mental prossession],而非心灵活动[mental process],可以等同于自然科学,eruditio和learning表示一种心灵活动而非心灵财富,可以等同于人文科学。科学的理想目标大致近于精通[mastery],而人文科学的理想目标大致近于智慧[wisdom]。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在给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之子的信中写道:“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而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倘若一位七旬老人。因其阅历而被称誉为智者的话,那么,一个思接千载的人,该是多么睿哲!诚然,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是历经千古了。”【19】
注释:
【11】然而,讲到“再创造”[re-creation]时,重要的是强调此词的前缀“re”。艺术作品既是艺术“意图”的体现,又是自然物,有时很难把它们跟其物质环境分离开来,它们永远逃不脱物质退化过程。这样,我们从审美上体验艺术作品时,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并举,而这两个行为从心理学角度说又彼此消融在一种Erlevnis[体验]之中:我们建立审美对象的方式既通过按照制作者的“意图”重新创造作品,又通过自由地创造一套审美价值[就象我们赋予树木或落日那样的审美价值],当我们陶醉于夏特尔大教堂那风雨剥蚀的雕刻时,不禁欣赏起它们的柔美和铜锈,将这种物质当作一种审美价值。这种价值包含着对光线与色彩的特殊作用的感官愉悦和对“年代久远”与“原貌”的更富感伤性的愉悦,不过,它与雕刻的制作者赋予它们的客观的,或审美的价值了不相干。从哥特式石像雕刻者的观点来看,退化的过程并非全然无关,实际上很令人讨厌:他们试图在雕像上涂布一层颜色加以保护,要是雕刻上的颜色现在仍艳如以往,那可能会大大地破坏我们的审美享受。作为个人,艺术史家完全有理由不破坏Alters-und-Echtheits-Erlebnis[起初的真诚体验】与Kunst-Erlebnis[艺术的体验]的心理统一。但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艺术史家必须尽可能地把对于艺术家赋予雕像的意图价值的再创造的体验跟自然演变赋予古老石头的偶然价值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往往看似容易,其实不然。
【12】关于本节中的术语,参见E.Panofsky,《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lconology]的导论,重印在本书第26-54页(指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译注)。
【13】当然,这点也适用于文学史及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依照狄奥尼修斯·斯拉克斯[Dionysius Thrax](《语法学》[Ars Grammatica,P.乌利希[P.Uhlig]编辑,XXX,1883年,第5页之后;引文见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ay],《一个文人的宗教》[Religio Grammatici,The Religion of a man of letters],波士顿和纽约,1918年,第15页),文学史是一种诗人和散文家所说的基于经验的知识。他将其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可在艺术史中找到对应之处。“对于艺术作品的批评性评价”[critical appraisal of works of art]这个说法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艺术史跟文学史或政治史承认卓越或“伟大”有程度之分一样,承认价值尺度,那么,我们在此阐明的方法似乎并未考虑到第一、二、三等艺术作品之间的差别。我们如何为此辩护呢?价值的尺度,部分地关涉个人反应,部分地关涉传统。这两个标准(第二个相对较为客观)不断得到修正,每一项研究(无论多么专门化)都有助于这个过程。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史家不能预先区分他研究“杰作”的方法和研究“一般”或“低劣”作品的方法,正如,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不能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塞内加的悲剧。的确,艺术史的方法,作为方法用于研究丢勒的《忧郁》和无名作品及较不重要的木刻一样有效。在研究的过程中,当一件“杰作”和原本可与之比较、与之联系的许多“次要的”艺术作品相比较、相联系时,杰作的独创性、构图和技巧的卓越性以及使其成为“伟大”的其它特点便会自动显示出来,因为全部的材料都用同一方法分析和解释。
【14】《米兰安姆布罗西亚纳图书馆的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著作的阿特兰蒂斯抄本》[Il codice a tlantico Leonardo da Vinci nella Biblioteca Ambrosiana di Milano]G.Piumati编,米兰,1894-1903年,fol.244V。
【15】见M.J.Friedlaender,《鉴赏家》[Der kenner],柏林,1919年,和E.Wind,《美学和艺术学的对象》[Aestheischer und Kunstwissenschaftlicher Gegenstand],见前引书。Friedlaender正确地认为优秀的艺术史家是或至少要发展成“不情愿的鉴赏家”。[Kenner winder willen]。相反,优秀的鉴赏家可以称为“不情愿的”艺术史家。【16】见E.Panofsky,“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美学和普通艺术学杂志》[Zeitschrift fue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haft],X V M,1925年,第129页起,和E.Wind,“艺术问题的系统”,出处同前,第438页之后。
【17】参见H.Sedlmayr,“严格的艺术学”,《艺术学研究》[Kunst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I,1931年,第7页之后。
【18】参见《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X M,1937年,6月19日)上刊载的Mr.Pat Sloan的信。(原引信的部分内容略——译注)。
【19】在人文学者看来,“复兴”过去不是浪漫的理想,而是一种必要的方法。他们能表述A.B和C记录是相互联系的这一事实,但这只是大意的表述:作A记录的人一定熟悉B和C记录,或熟悉B和C类的记录,或熟悉B和C的来源X记录,或者他一定熟悉B,而B的作者一定熟悉C,如此等等。人文学者必然用“影响”,“演变线索”等词语来思维和表述,如同自然科学家用数学等式来思维和表述一样。 【20】Marsilio Ficino致Giacomo Bracciolini的信(《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全集》,莱顿,1676年,第I卷,第658页)。(原引意大利文略——译注)
曹意强译 范景中校
原文刊载于《新美术》1991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