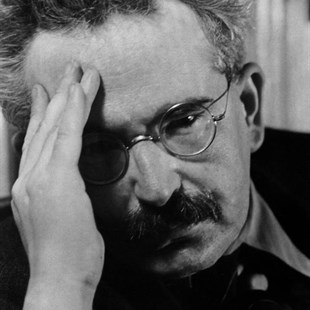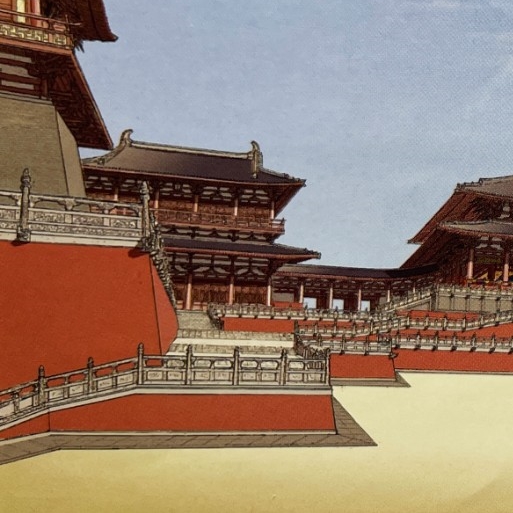三、文艺复兴时期
与屮世纪的观念相対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艺术的理论和历史文献,用一种也许从前章所讨论的观念中方可理解的不懈精神,来强调艺术的任务是直接模仿现实。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这看来多少有些奇怪,塞尼诺·塞尼尼——他的论文深深扎根于中世纪的作坊传统——建议那些想描绘山岳风景的艺术家拿几块未经琢磨的岩石,并按照适当的尺寸和明暗分布进行模仿;然而这剂药方意味着新文化的纪元的开始。当建议画家使用自然对象时(虽然这里所选的自然对象相当奇怪),艺术理论从一千年的湮没无闻中解救出一个概念:艺术品是现实的忠实重建。这概念在古典古代时期不证自明,后又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清除,而在中世纪的观念屮几乎不被考虑。艺术理论不但从湮没无闻中解救岀这一概念;还有意识地把这一概念提高到艺术纲要的地位。所有这一切是非凡的新鲜事儿。
从一开始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就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十五世纪伟大艺术家的创新和光辉成就正是要呼唤艺术,呼唤“过时的、幼稚地离开自然真相”,仅仅建立在因袭习惯上的艺术,并力图回归到“逼真”。当莱奥纳多·达·芬奇说“那幅画最值得赞美,它与被再现的事物最最相似,我这么说是在针对那种想对自然事物作出改进的画家”时,他表达了一种数个世纪以来没有人敢反驳的意见。
与“模仿”这个概念——包括对形式上和客观上的精确要求——相平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献中“高于自然”的思想也有位置,恰如古代艺术文献所做的。一方面,自然可以被随意创作的“幻想作品”所压倒,“幻想作品”对外表的改变大大高于自然本身变化的可能性,甚至能产生出诸如半人半马的怪物和吐火女妖那样完全新颖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自然可以被艺术才智所压倒。艺术才智能够,从而应该,使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实现的美可以看得见。那个经常重复的要忠实于自然的告诫,与那个几乎是强有力的从大量的自然物体里选择最美东西的告诫是相平行的,为了避免奇形怪状,尤其从比例而言,总的来说——在此声名不佳的画家德米特里[Demetrius]再一次作为训诫的例子——要追求高于自然的美。让我们听听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的话:
画家不但要表现各个部分的真实外表,而且要给各部分增添美,因为在画上,美与其说是令人愉快,不如说是一种需要,古代画家德米特里之所以没有赢得最高赞赏,是因为他尽力使物体跟自然相象,而不是尽力使之美丽动人。
因此,从所有美的物体上选取各个值得赞美的部分是有益的,而且人们必须永远以钻研和技能来学会超乎寻常的美;这点确实是困难的,因为理想的美并不是独自存在于一物体中,美的各部分是分散的,而且在许多物体中也难得见到,然而人们还是必须尽一切努力去研究它、学会它。会出现这样的事:习惯于追求并从事伟大事业的人会很容易做好小事情。任何事情都不会困难到通过学习和应用而无法掌握。
带着这种热情,有关麻雀和马的轶事便被传播开来,偶尔还有人用近代十分确切的例子对此加以补充,也是以同样的热情,人们重复着——甚至更为经常地——关于宙克西斯[Zeuxis]选择表现克罗托内少女们[Croionian maidens]的另一件轶事。关于这件轶事,甚至阿廖斯托[Ariosto]也没忘了吿诉他的读者。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要求它的艺术作品既逼真同时又美,正如古代时期所要求的(模仿的概念如同选择的概念那样。毕竟是从古代时期继承来的)。事实上,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出发,这两项要求只是一项基本要求的两个部分——只是到了后来才变得互不相容:要求艺术家在毎件艺术品中重新面对现实,让每件作品作为修正者或模仿者。提防对其他艺术大师进行“模仿”的吿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但是到当时为止这类吿诫并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是因为那类模仿常常暴露出模仿者缺乏理念;直到“理念”成为艺术理论的主要观念,那种告诫才会变得重要起来。更确切地说,提出那些告诫只不过因为自然比画家的作品丰富多采,结果模仿其他画家之作品的人会降低他本人,当他本可以作为自然的儿子时。他却将自己降低为自然的孙子。
真正“艺术理论”的诞生
艺术家被逐出了禁闭的,但受保护的居住区,来到广阔无边的、尚无人向津的乡间,在那里必然要出现在今天通常被叫做艺术理论的那个部分,在许多方面艺术理论建立在古代基本原则之上,不过总的来说它还是很现代的。它不同于较早期关于艺术的文献,不再回答“怎么做它?”这类问题,而是要回答完全不同的,非中世纪的那个问题:“每当艺术家被要求去面对自然时,是什么能力,首先是何种知识使得艺术家有信心去这样做?”
就艺术态度而言,文艺复兴在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因为这个时期把对象从艺术家想象的内在世界里清除掉,并把对象坚定地置于“外部世界”里。这个通过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所拟定的差距来实现,很象在艺术实践中透视法在眼睛与事物之间所定的距离——距离同时使“对象”客体化,又使“主体”人格化。
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基本上新奇的观点会立刻引起一个问题,这问题至今一直作为有关艺术的科学思想的焦点:问题是关于“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自发性与感受性之间的关系,给定的物质与主动的形式能力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为了陈述简洁起见,可以把这个向题叫做“主客观问题”。但是情形正相反。十五世纪发展起来的艺术理论其目的首先是实用,其次才是历史和争辩,而决不是纯理论。换句话说,它的用意仅仅在于:一方面认为当代的艺术作为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的真正继承是合法的,并通过列举它的显贵和功绩为它在人文学科里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给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提供严格的。在科学上有根据的法则。不过,要达到第二个、且最重要的目的,只能基于此先决条件(普遍认可的),即:在“主体”以及“客体”之上有一种普遍的、绝对有效的法则体系、艺术规则必然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而理解这些法则成了“艺术理论的”特别任务。
这门新学科是那样天真地提出了既要准确又要美这两项要求,它那样天真地相信它有能力为它们达到目的铺平道路、指明方向。形式的和客观的准确看来是有保证的,如果艺术家一方面遵守透视法的原则,另一方面遵守解剖学、心理学、生理学、运动学和观相术的原理。艺术家如果选择要创造美,努力避免“不雅”、“矛盾”,并给外表赋予那种被看作是色彩、特性,尤其是比例之间的按推理探知的和谐,他就达到了美。比例的学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来确定什么是和谐的,因而是令人愉快的,以及什么东西构成愉悦的基础。答案可能以一种个案表现出来,但却可表明艺术家主观的和个人的判断都不足以认为好的比例是“好的”:如果作者没有求助于数学的或者音乐的基本原理(在那个时代两者差不多意指同一种东西),他们就求助于圣贤之言,或求助于古代雕像的证明。其至连这方面的学者,不论是批判论的还是怀疑论的,诸如阿尔贝蒂或莱奥纳多,至少努力从根据舆论判断或根据“专家”评定而精选出来的材料中抽取一种准则,并把这一准则跟仅仅依据个人品味的判断进行对照。
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真正艺术理论的非柏拉图倾向
中世纪的思想在艺术创造中之所以没看出问题,是因为它根本上既否认“客体”乂否认“主体”:艺术仅仅是形式的特质化,它既不依赖实际的“客体”的外象,也不是由现存的“主体”行为创造的;相反,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先行形象预先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来说,这个问题也不可能明了,他们认为“主体”的本质和行为以及“客体”是由一定的规则所决定的,这些规则或是先前有效,或是凭经验可以论证。这说明一个特别事实:在十五世纪新出现的艺术理论原则,首先几乎完全独立于在同个时期、同个佛罗伦萨文化界所发生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复兴之外。因为这个形而上学的、甚至神秘主义的哲学,设想柏拉图不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宇宙论学者和神学研究者,它不企图辨别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它努力尝试一种神圣的伟大的结合体,即柏拉图式与柏罗丁式、后希腊宇宙论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荷马史诗的神话与犹太教的神秘哲学。阿拉伯文化的自然科学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结合体——这样一种哲学可能给有关艺术的思辨学说以多种多样的刺激(恰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后来确是如此);但是这种哲学对于一种实用的、着重理性主义的艺术的理论,诸如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要求和设计的理论,不可能有什么本质的价值。
这类艺术理论,到当时为止,并不是为诸如菲奇诺[Marsilio 于icino]从柏罗丁和伪丢尼修那里获得并塞进柏拉图体系里的那些观念作准备的。由于它的自然主义倾向,它本会被迫抛弃一个学说,根据这个学说人类心灵中有一种由神的精神印记在人类心灵上的完美人、狮子或马的概念,根据这个学说心灵判断自然的创造物正是依据上述概念。在这类艺术理论里平淡无奇且符合逻辑地例举了“动机的七种可能性”,这跟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学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直接动机代表神的创始力、间接动机代表神的创作的继续,循环动机代表神与它本身的一致性。
对称美
西塞罗曾一度把美解释为“物体跟理念更明确的相似物”或“神的理性高于物质的胜利”,这跟柏罗丁几乎相一致。他一度把美叫做“上帝面上的光辉”,这光辉首先照耀天使,然后照亮人类灵魂,最后照亮物质的世界,这差不多接近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阿尔贝蒂完全赞同他的同辈理论家的观点,并认为艺术理论确立地位已达一百多年之久。他以古希腊时期纯属现象的美的定义来反对这种对美的形而上学的解释:
……就一定的数,比例和秩序,如和谐要求(即,绝对的、基本的自然法则)而言,我们可以说美是各部分之间的某种呼应和协调。
换言之:人们必须注意单各部分构成完美的整体,而且如果尺寸大小、颜色等协调相称并形成一种统一的美,它们就会构成完美的整体。比例的协调以及颜色和质量的协调——这就是阿尔贝蒂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艺术理论家所理解的美的本质。恰恰是阿尔贝蒂促进了那个美的定义——柏罗丁曾强力地反对那个定义。因为它只抓住了现象的外部特征,而没有抓住美的内在本质和意义——并赢得持久性的胜利:美来自于各部分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的比例,加上愉快的色彩。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放弃对美的任何形而上学的解释,因而它的认可第一次解除美[pulchrum]与善[bonum]的古老联系,尽管一开始是通过默默地禁止而解除这种联系。审美经验的自律,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证实,而在过渡时期,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再次成为经常争论的问题,它即使到当时为止也没被认为是定论,也没被认为是事实。
所以人们可以声称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几乎没有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复兴的影响。艺术理论家可以接近欧几里德[Euclid],威特鲁威[Vitruvius]这一边,也可以接近昆体良[Quintilian]和西塞罗那一边;但是他们没法接近柏罗丁或柏拉图,只冇作为画家的阿尔贝蒂才引述柏罗丁或者柏拉图。实际上、柏拉图第一次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在帕乔利[Luca Pacioli]的《圣神的比例》[Divina Proporzione](1509年版)一书里,帕乔利、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个艺术理论家,不如说是个数学家和宇宙论学者。
只有在一个方面,柏拉图思想的复兴似乎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艺术理论:首先人们仅仅在孤立的情况下,在相对不重要的地方,而渐渐地越来越经常并越来越强调,人们面临着那个艺术“理念”的观念。但是,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么个事实更清晰地说明艺术理论的最初前提与柏拉图主义的最初前提之问深深的本质差异,这个事实便是:要想尽可能使理念的理论与艺术理论结合起来,就只能牺牲它们双方某一方理论的某些方面、共或任大多数情形下要牺牲上述二种理论的某些方而。那个理念厩念影响越大,它就越接近它内在的(即,形而上学的)意义(它首先发生在所谓的“风格主义”时期),而艺术理论便更进一步放弃了它最初的实际目标和最初的不成问题的前提。反过来也是这样,艺术理论越是坚持这些实际的目标和不成向题的前提(在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确是如此,以及在后来的“古典上义”时期又是如此),理念概念越是失去它最初的形而上学的,或至少是先者的有效性。
菲奇诺
根据柏拉图学派的观点,如菲奇诺结论性地系统阐述的那样,理念是形而上的现实。它们作为“真正的实在”存在者、而人间万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意象(即,具有真正生命的那些本质的意象);除了它们的实质之外,理念被看作是“简单的,静止的、没有冲突的混合物。”它们是上帝头脑中固有的(偶然也在天使的头脑中),根据柏罗丁和基督教兴起初期的作者,它们被叫做上帝心灵中的范例。人类的意识之所以能够认识,只因为理念的“印象”(拉丁语:于ormulae)已先存在于人类超此的灵魂中。象来自神性的初始乏光所产生的火花那样,这些“印象”因长期静止不动而“几乎泯灭”,但是它们可以通过“训导”而复活,并可以根据理念之光使它们重新闪现,就象所见的光线来见闪烁的星光:
最后,柏拉图又说道,在受到这种影响的头脑里真理之光不是慢慢地以人类情爱的方式,而是突然地点明。可是它们来自何方?来自火,即来自上帝,这火喷发出来,放射出火花。通过火花照出理念……并且还这样照出这些我们生来就有的理念的印象[于ormulas],以前由于不使用而僵化了的这些理念的印象。现在又被脑海的轻风重新煽起来,它们因理念而发出光来,就好象眼睛因星光而闪烁。
对一般事物的认识是如此,对美的认识(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尤为如此。美的理念也作为印象铭刻在我们的头脑里,并只有依靠这种天生的概念——也就是我们身上最为精神性的东西——我们才能够领悟到看得见的美,因为我们把它与看不见的美联系起来,并享受肴在我们眼前呈现的理念故胜实体。我们尽可能与美的理念相一致,通过将感觉外象归回它在于我们心里的印象,从而领悟这种一致性。
阿尔贝蒂
阿尔贝蒂把完全不同的物质归因于理念概念。在讨论美的前提之中,随着对古代写实画家德米特里的责难,就在那个有关宙克西斯和克罗托内的少女的故事盛传之时、出现了一种尖锐的抨击,仿佛是对走极端的一种警告,抨击那些相信不对自然作任何研究便可以创作出美的事物来的人:
但是,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人们应该避免某些蠢人的习惯,他们自夸自己的才能,企图单单凭借自己的资力得到画家的美名,他们完全不要他们可以用眼睛和心智迫随的一种自然模式。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好好学习画画,可是他们使自己习惯于自己的错误。那个美的理念,连最富经验的头脑也难以理解它,当然也就完全被这些无经验的头脑忽略了。
宙克西斯,最杰出的画家,当他打算作一幅画,公开展示在克罗托内人的生育女神神殿里时,他并不象当今的每个画家那样愚蠢地相信他自己天生的才能;因为他认为他无法在单个物体上找到他所探求的全部美。……
“那个美的理念,连最富经验的头脑也难以理解它,然也就完全被这些无经验的头脑忽略了,”毫无疑问,这一陈述证实阿尔贝蒂在某个方面受到了柏拉图思潮的影响,因为画家和雕刻家内心的眼睛所感觉的美的理念概念完全是非中世纪的。但是,那些认为阿尔贝蒂可能是个真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人一致对这个陈述保持缄默,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基罗和柏罗丁用来论证艺术才能的无限力量和它与外在经验无关的本质独立性的那同一种理念概念,在此是用来警告不要对艺术才能作过高的估价,并要把艺术才能唤回到对自然的沉思。“那个美的理念,连最富经验的头脑也难以理解它,当然也就完全被这些无经验的头脑忽略了。”这正是意指文艺复兴的理论,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为了理念概念而牺牲它那来之不易的现实主义信条,便将理念概念改变到足以与那个现实主义信条相一致,甚至可以用来支持那个信条。彼特拉克[Petrarch],一个真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懂得只有依据神的先见,才能通过色彩和线条看见美;阿尔贝蒂相信理解美的心理能力只有通过经验和实践才能获得。而事实上,即使琴尼尼[Cennini]以及他之后的莱奥纳多承认艺术家常变化和发明把自己从现实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也没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敢象狄翁和西塞罗那样把美看作是幻想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意大利艺术理论家才对理念概念重视起来——甚至过了更长一个时期,他们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重要性。据我所知,莱奥纳多从来没有使用过“理念”这个词。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在他的一书里用完全柏拉图式的颂词解释爱、歌颂爱,他把对艺术的评判建立在适当模仿的标准之上,这并非不是文艺复兴盛期对艺术的典型态度。
拉斐尔
只有拉斐尔在1516年写给卡斯蒂廖内的那封著名信中,用了理念概念;但是他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不如阿尔贝蒂关于我们如何理解“理念”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所表达的思想。确实,他明确拒绝讨论这个向题。他在信中写道:“为了画一个美女,我得观察许多漂亮妇女,而且这是在可能帮助我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不过由于漂亮妇女寥寥无几,可靠的判断也极少,我只能利用进入我头脑的某种理念。我无法说出它是否有任何艺术价值、我只是非常尽力地要得到它[那个理念]。”这么些妙句不应该受认识论评判的苛刻检验。这些妙句证明,一方面拉斐尔知道他只能通过“内在概念”,不再依靠具体的个别物体来创作一个完美女子的形象,另一方面他既不把合于规范的有效性,也不把形而上学的渊源归于这个内在概念。实际上,他只能用某种理念这种措词来指出它的性质。不知怎么地它进入了人的头脑,但是它是否具有任何价值或是否正确,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如果问到他、它是从何处进入他的头脑,他大概不会否认感觉经验的总和以某种方式被转变成了内心的形象,如同丢勒[Durer]谈及秘密收集成的情感珍宝的那种相似方式,只有当艺术家以大量来自生活的图画装满他的头脑,以及由于他的充实,他能够在心里创造出某一事物形式时,这秘密收集成的情感珍宝才显示出来。然而,拉斐尔的最后回答可能是:我不知道。
瓦萨里
瓦萨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新的风格上义艺术理论的影响,虽然总的来说他的艺术理论观点有些怀旧,在他的《名人传》第二版中他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依然没有超出陈述情境,他不提供对这种情境的哲学分析、也不从这种情境中引出理论上的结论。阿尔贝蒂——我们回想起来,拉斐尔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曾认为那个美的理念是由“经验”决定的,对阿尔贝蒂来说那个美的理念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形而上学的灵光,但是他却不曾说过它来源于“经验”。他认为理念常在熟悉自然的头脑里,而不在缺乏具体观察的头脑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它是自然事物的“抽象化”。瓦萨里说:
设计,我们三项艺术的鼻祖……从许多事物中得到一个总的判断: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形式或理念,可以说,就它的比例而言是非常规则的。因此结果是设计不但在人体和动物体方面,而且在植物、建筑、雕塑、绘画方面,清楚地认识到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比例,以及各部分相互间的和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例。由于从这个认识里产生了某种判断,它在头脑里形成了那个后来通过行家制作的、被叫作设计的东西,人们可以推断出这个设计只不过是人们在理智上具有的、在头脑中想象的、在理念中建立起的那个概念的视党表现和分类……。
这点说明理念不是先于经验,而实际上起源于经验;理念不光能够与对现实的观察很容易地结合起来,它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观察,通过从多数中选取个别及随后将个别选中的东西组成一个新的整体这神精神活动而得到阐明。这一解释相当于是对“理念”重新下了定义,既根据它的本质又根据它的作用。既然理念不再以先者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里(即:理论不先于经验),而是作为后者由艺术家产生(即:理念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理念不再是感觉现实的竞争者,更谈不上是感觉现实的原型,相反是现实的派生物。因为同样的原因,理念不再作为人类认识的特定内容,甚至不再作为人类认识的超验物,而是作为它的产物,这个变化甚至从纯语义学的观点来看也是清楚可辨的。从这时起,理念不再是如西塞罗和阿奎那曾说过的,“留存于”或“先存于”艺术家的心灵里,更不必说对艺术家来说是“天生的”,如真正的新柏拉图主义曾表示的。反之,它进入他的“头脑”,“出现”,它是“获得的”,而且是被“作成的和雕刻成的”。在十六世纪中叶,人们不但用“理念”这个词来指称艺术想象的内容,而且用它来指称艺术想象的能力,这点甚至成了惯常之事,因此这个术语近似想象这个词。于是瓦萨里可以在引录的这段文章里写道:概念由理念而生。在别处我们又看到如下这样的话:事物在理念中想像出来,物体的形式在理念中才让我觉得稳固,创作者和设计者的理念赋予物体以形式,等等。
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理论对理念的再界定
很清楚。根据上述的论述,对“主客体问题”进行基本阐明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当“主体”一接受任务去以他自身的努力从现实中获得艺术创造的规律,而不是让艺术创造的规律凌驾于现实之上(和凌驾于主体之上)时,就必然出现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以何种理由他可以声称这些规律正确无误。然而——这点特别有意义——结果是一个明确的“风格主义”学派首先获得对这个问题的基本阐明,或至少有意识地要求如此。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可能认为,“主客体”问题在其被明确阐述之前已经(由他们润色过的理念学说本身)解决了。由于在艺术家头脑里形成的,在他的设计里表现出来的“理念”井不真正地来源于艺术家本人,而是通过一般判断从自然里得到的,那个理念即使实际上被“主体”所认识和实现,似乎还是可能在“客体”里被预示。特别是,瓦萨里把得到理念的可能性建立在这一推论上,因为自然本身在结构上这么有规律且始终如一,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它的个别方面来认识事物的整体。这个想法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系统提出的,其实是后来所为。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艺术家从观察中所获得的那个理念同时揭示了自然“根据规律而造”的真正目的。拉斐尔也许会说——恰如一百年以后有古典主义倾向的圭多·雷尼[Guido Reni]所说的——因为他缺乏十分美的模特儿,他就利用某种理念。因而后来的一个西班牙人,虽然完全充满了古典主义精神,却能够系统地阐述观察自然与形成理念之间相互补充的特殊关系,他说,好画家必须通过观察自然来“调整”或“修正”他的内在概念、怛是在缺乏这种观察的地方。他可以利用“他已经获得的美的理念”,“因为完美便存在于从理念到自然模式以及从自然模式到理念之中。”
在文艺复兴盛期,艺术理论上的理念学说,就美于美的向题来说(就这点而论,它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的理念学说),很象是从前的选择理论的更加精神化的形式——这种精神化便是:美的获得不是由于各个部分的外部结合,而是由于内在想象力把个别经验合为一个新的整体。尽管选择理论対古典主义思想家来说平常之极,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将“理念”等同于从最美的事物中挑选得来的典范。他们不是把理念想象成思想与自然之间的中介物,而是把理念想象成使思想独立于自然的一种保证。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根据一种根本上新颖的艺术观点来理解理念槪念,这种艺术观认为理念世界就是提高了的现实世界。尽管这种思想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出现之前,还没有明确的系统阐述,但“理念”这个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被转变成“理想”这一概念。这种转变剥去了理念自身形而上学的高贵,不过同时使理念跟自然保持美的,且差不多有机的一致。由人的思想产生的理念,非但不是主观的和任意的,它表现出包含在毎一客体中的自然规律。理念凭直觉的综合基本上获得阿尔贝蒂、莱奥纳尔多和丢勒曾试图推出的结论。当时他们把由观察得来的,并由专家判断认可的丰富资料进行概括和分类,使之系统化为有关比例的理论。
瓦萨里,在以上引录的文章里,与其说回答了实现美是否可能的问题,不如说回答了艺术再现美是否可能的问题:绘画构思的问题。在中世纪盛期的哲学里,事实上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标志,“理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准理念”——跟美的理念这一概念(它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中复活了,接着发展为“理想”)没有联系,但跟“纯粹的艺术概念”有联系,不管这个概念的内容是“美的”还是“不美的”。很清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发觉他们自己无法放弃这个较为广义上的“理念”,即他们后来把“理念”这一词语运用在大约和“思想”或“概念”相同的意义上。不过也很清楚,他们不得不给“纯粹的艺术概念”重新界定为跟较狭义上的“美的理念”有一样功能的和经验之后的某种东西。看来使艺术家“发明”或“设计”任何艺术作品的东西就是那个使艺术家想象出美(或者相反的丑)的一般判断。受理念的保证。“表现源于自然观察,乂超越自然物的形式”的可能性,和设想一种同样来源于自然观察又独立于自然观察的形式的可能性,是相一致的。
另外,“理念”这个词语,根据它的不严格用法可以指概念的想象力(也就是说,不指形式或概念,而指思想或想象),它在十六世纪也有两个在艺术理论上根本不相同的意思:
(1)当阿尔贝蒂和拉斐尔使用这个词时,“理念”意指美的心象,它超越自然,即大约相同于在后来一段时期里“理想”要表示的那个东西。
(2)当瓦萨里和其他人使用这个词时,“理念”意指艺术家头脑里构想的任何形象,即大约相同于“思想”和“概念”等词语,这些词早在十三、十四世纪就这么用了。这用法在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占优势,但在十七世纪,当“理想”概念被明确地提出来时,它趋向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理念”这一词语指称艺术家头脑里构想的每一个概念都先于实际描绘。它甚至可以指称我们通常叫做“主体”或“主题”的那个东西。
这两个意思经常没有明确的区别。它们不可能有明确的区别,因为两者中较为广义的第二个意思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包含第一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当“理念”作为第一个定义的意思而使用时,有时在这个词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象美的或好的等。最终,这两个意思毕竟相一致,因为在两个领域内——美的实现以及艺术再现本身——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质上相似。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中,理念的形成与自然的观察被联系起来,理念的形成被安置在一个领域,尽管还不是独特心理学的领域,然而也不再是形而上学的领域。这是通向承认现在所叫做“天才”的第一步。文艺复兴早期的思想已经预先假定了实际的艺术“主体”作为实际的艺术“客体”的对应。就象灭点透视的发现同时假定了可见的“事物”和理解的“眼睛”一样。但是如我们所知,规律也被认为是那样存在着,既是超主体又是超客体,似乎能控制创作过程,几乎好象是由高一级的法庭传下来的。承认这种超主体的和超客体的规则,跟那种认为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自由地遵循他自己天才的见解,是基本上相对抗的,所以它们的有效性逐渐受到艺术理念概念的限制。人们以为艺术家的头脑能够直觉地把现实转变为理念,完成客观材料的自发性综合,并且这样的头脑不再需要如数学法则,立论的一致,古代作者的文字根据等这样的规则,来获得有效认识或经验认识,相反艺术家的特权和责任是以他自身的努力去获得对可知客体的完美认识,正象在十六、十七世纪里“理念”的用法,根据布鲁诺[Giordano Bruno]那种几乎是康德哲学的叙述,只有艺术家创造规则。布鲁诺的叙述只有与理念的学说联系起来,才能被全面理解。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完全达到明确地阐述“理想”概念,同样也没有完全达到明确地强调艺术家天赋。文艺复兴对天赋与白然之间的冲突,和对天赋与规则之问的冲突一样所知甚少:而且这两个对立物的和谐共存——那时二者还没有分离——由文艺复兴时期重作解释的理念概念清楚地表达了出来:这个概念给艺术家的头脑以自由的保证,同时相对于现实的要求又限制了这种自由。
姚晶静译 邵宏校
原文刊载于《新美术》199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