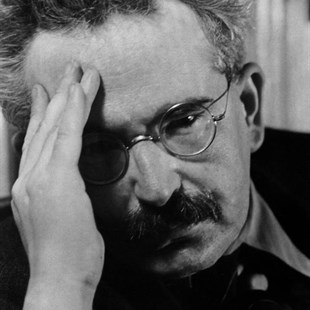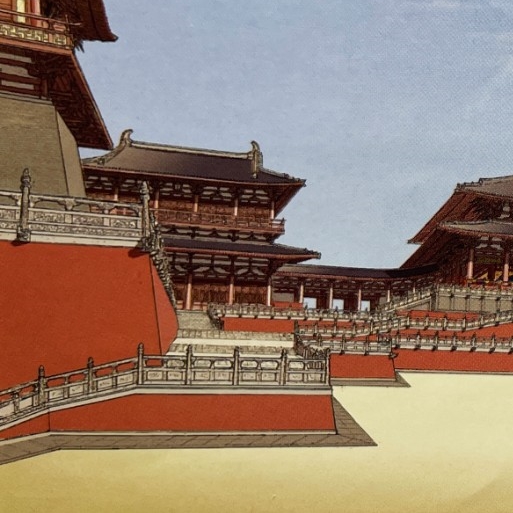二、戴文进的传记及评论
戴文进的传记资料能举出许多,但记载红袍钓士事件及谢环的进谗,依我所见应以陆深《春风堂随笔》为最早。可以想象,也许是这随笔中的记事传播开来后,而被转载于其它书上。陆深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十八岁时去世。他和天顺六年(1462)六十五岁时去世的戴文进之间,相距约一个世纪。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说:“本朝画手当以钱塘戴文进为第一。”这大概是明代画坛以戴文进为第一的最早说法。【13】
比陆深稍退的郎瑛(1487-?)在《七修续稿》中为戴文进作传,这篇传记不仅较陆深所作的戴文进传记要详细,而且还对戴文进的作品也有所评论。虽然他象陆深那样,也把戴文进归入职业画家,但他也承认戴文进具有高尚的人品。除了李在、林良、吕纪、吴伟等时代相近的宫廷画家,以及周臣、杜堇等所谓院派画家外,和夏等文人画家相比较,戴文进获得“兼美众善”的评价,并有“画中之圣”的称号。【14】郎瑛的论述未免让人有夸张之感,但他所据的文献,是戴文进的同乡贺荣所撰的墓志铭,这与后人所撰的戴文进传记相比,自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郎瑛为了证实戴进具有多方面的画技,就将上述李在以下的画家说成是他们各自继承了戴文进画技中的某一方面。这一见解对探讨戴文进画迹与画风,显然是有启发性的意义;对弄清浙派即戴文进派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开先(1501-1568)对郎瑛所撰戴文进评传中涉及到的一些画家,进行了具体地研究。他在《中麓画品·后序》中说:“文进画笔,宋之入院高手或不能及,白元迄今,俱非其比。宣庙喜绘事,一时待诏如谢廷询、倪端、石锐、李在等,则又文进之仆隶舆台耳。”他还说:“平山(张路)粗恶,人物如印板,万千一律。”两相比较,对职业画家偏见较少的李开先,其倾向戴文进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李开先对浙派画家的评论,以及他对南宗画家的看法。
在《中麓画品•画品一》中,李开先说:
“戴文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
“吴小仙如楚人之战钜鹿,猛气横发,加乎一时。”
“李在如白首穷经,不遇于世之士。蹇滞寒陋,进退皆拙。”
“丁玉川如十金之家,门扉器物,不得精好。”【15】
“钟钦礼如僧道斋榜,字大墨浓,惟见黑蠢。”【16】
“王㩲、王谔如五代之官,帽则乌纱,身则屠贩。”
“林良如樵背荆薪,涧底枯木,匠氏不顾。”
这些评语虽然不一定是全面肯定浙派画人的业绩,但和同一《画品一》中所述“沈石田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别无所有”,即对吴派文人画巨擘沈周的激烈批评相比,李开先对戴文进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
犹如文人画派神圣地看待董源、巨然、黄子久等一样,李开先也把戴文进绝对化了。他在《画品一》的续集《画品二》中,论述了绘画的“六要”,揭示了独创的全部要诀,并且举出一些佳作加以说明。所谓“六要”,即神笔法、清笔法、老笔法、劲笔法、活笔法、润笔法。他所举与这六要素相应的作品,便是戴文进与吴小仙的。很明显,李开先把戴文进作为明代画坛上的绝对存在,而把吴小仙当作其后继者。他认为戴、吴画风上的相异点,只是吴比戴“更逸”。“片石一树,粗且简”。【17】李开先承认吴伟与其后继者在画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却几乎没有考虑戴、吴之间的断层。
以上是李开先对戴文进绘画的评价,而且这些评价不只限于山水画,还涉及到人物、花卉。然而,据我所见,戴文进的花鸟画作品并不多,人物画也很少。甚至几乎没冇遗存。因此,李开先对戴文进的评价是否正确,只好通过山水画作品来验证。
李开先认为戴文进的绘画风格,是折衷了宋代绘画,并加以消化而形成的。其源头不只限于北宗画派的马远、夏珪、李唐,甚至可以追溯自范宽、米元章、关同、赵千里、刘松年,以及元朝的高房山、赵子昂、盛子昭、黄子久等人。【18】根据明末“南北宗论”来看,上述画家横跨了南、北两宗;根据画家的身份来看,这些人中有职业画家,也有士大夫文人画家。从这点上,我们可以推测出戴文进画风的错综复杂。
李开先的上述见解,初看会飴人一种奇异的感觉,但对戴文进作出这样的评价,却并非只李开先一人。后文所提到的孙承泽、李日华等,都持有相似的看法;图绘宝鉴续编》的作者韩昂,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评价;【19】还有姜绍书亦接受这种观点。【20】
当然,对戴文进的评价,我们不仅要考察诸如李开先那样偏重戴、吴倾向的意见,此外还必须考察吴派文人对他的看法。吴派文人画家中与文征明关系亲密的祝允明(1460-1526),曾对戴近的画作过几首诗。【21】他在《怀星堂集》中这样写道:“有明画家推钱塘戴生,笔墨淋漓以雄老特名。”【22】这表明把戴文进推为明代画家第一的看法,直到嘉靖初年为止,都被一般人所公认。
另方面也不可否认,以嘉靖时期为下限,人们对戴进绘画的评价出现了本质的差别。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吴宽,【23】接着便是嘉靖时期的何良俊。何良俊只认为戴文逬的画技局限于人物画,然而人物画却随着山水画的强盛而衰退了。擅长人物的画家“可数而尽”。【24】因此,他最终还是把戴文进的评价归纳到职业画家那精巧细致的技法上。何良俊提倡“行利家论”,他认为文征明是兼有行、利二家,而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能兼利”,其原因是戴文进在“人品”上受到限止。【25】何良俊称文征明是位行利兼善的画家,这未免太主观了,因为他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基于对文氏绘画作品的分析上。在《四友斋丛说》中,我们到处可见何良俊对文征明人品的倾倒敬慕之情。以这一时期为界,在文人评画者之中,出现了按画家身份地位来评介其作品优劣的倾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表明自古以来士大夫画家的定义再次被用到明代画坛上。基于这种倾向,人们在评论戴文进时,当然地把他划入“行家”这一系谱。所以,这就导致了所谓职业画家人品低的偏见,即使其作品的技巧再高明,别人总以为其表现内容是低俗的。
诚如后文将要叙述那样,根据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看法。即使在人品方面获得较高评价的戴文进,因为他是画院的画家,而被归为“单是行耳”,其原因正在于文人评画者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引起人们对戴文进个人评价的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出现了到明末为止戴文进传中所没有的新传闻。清代的厉鹗(1692-1752)在他的《东城杂记》中,有戴文进是银匠的说法,【26】毛先舒(1620-1688)的《戴文进传》就有戴文逬是铁匠的说法,【27】对他出身的这些传说,在明代后半期是相当普遍了。光凭其出身匠人,以及入画院为画工这两点,人们就足以推测出戴文进不具备“利家“的品格。
总结嘉靖以来的画论,正是关于戴进、吴伟评价中两种相反意见流行的时代。这两个极端的意见,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折衷化了。一方面,出现了王世贞那样的见解;另方面,出现了孙承泽(1592-1677)在跋戴进《灵谷春云图》中那种更具冇代表性的看法。【28】
王世贞在跋《七景图》中评论道:“予初阅之,以为沈启南作。见题字不工,及验其印章,而始知为文进也。然无一笔钱塘意,苍老秀逸,超出蹊径之外。【29】这段文字说明王世贞充分认识了钱塘画,即浙派画,而且他注意到戴文进画中具有与通行的浙派风格相异之处,王世贞对戴文进的评价还可以散见于其它篇章,如跋戴文进《山水平远图》等。【30】这些文章不仅涉及戴进绘画的艺术价值问题,并目令人注目的是,与前面所述李开先诸文一样,它们还表明了戴文进画风的多样性。
在明末,说明关于戴进画评的折衷见解已经形成的是孙承泽《庚子销夏记》。【31】他在指出戴文进画风多样性的同时,试着否定了戴文进画与其它浙派画家具有不同的价值。据孙承泽说,戴文进画的风格并不高尚,无非是继承了南宋职业画家马远、夏珪等人的院体画风而已。其中如《灵谷春云图》,如果没有落款,就不能被认为是戴文进的作品。他在文中还记述有人误将戴文进的作品,当成钱塘文人画家聂大年的作品。【32】聂大年山水画的风格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据记载,他是学高克恭,颇得清淡之趣。而高克恭的画风又仿米家父子。这就意味着戴进的山水画中具有米家山的水墨画法。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王世贞题戴文进《城南茅屋图》所述戴氏画风有米襄阳笔意,【33】徐沁评何澄之说,【34】李开先对戴文进的画评,【35】这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以事实表明戴文进具有南宗描写技法和南宗画风的文献资料,除王世贞跋戴文进《七景图》外,还有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六年(1608)七月九日,李日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戴文进《溪山清隐》,仿子久,粗笔亦疏爽。”【36】虽然,在未能见到《溪山清隐图》原作的今天,也许不应轻信李日华的话。但从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中表现出对绘画具有较深的见解水平来看,他关于《溪山清隐图》的看法应是可信的。与李日华大致同时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记述戴文进曾临摹过黄子久,王叔明的作品。【37】因而根据这些事实,即使明末的画论对戴文进的评价不如李开先那么绝对化,但人们也应该充分承认戴文进画风范围的广泛性。
和戴文进山水画风多样性相关联,人们对作为画家的戴文进之评价,也岀现了各种变化。一方面,象何良俊那样轻视行家的看法得到了改变;另外,发现戴文进与沈周绘画妙趣相合的王世贞,认为戴文进是行、利双兼,亦是很自然了。他把戴文进绘画的渊源看作是郭熙、李唐、马远、夏珪,但决不是以行家而告终;按通俗的说法,戴文进是“行家兼利”【38】王世贞的这种想法,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徐沁的《明画录》引用了。【39】
那些现存的冗长的戴文进传,以及对他作品的评介文字,主要是依据成化以后的文献资料。根据这些传记、评论可知,在浙派画家中,只有戴文进受到特别的对待,人们隐约地暗示其画风是不规则的院体,而且呈现出多元的姿态。此外,评价也从毁誉参半,而最终变成了折衷之见。总之,这些文人批评家或绘画史家们,充分认识了戴文进对后代绘画的巨大影响。但这些认识仍在根本上局限于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间横亘着的身分差异,这成为全面认识戴文进绘画的障碍。
戴文进对其后画坛的影响,应当根据绘画作品作具体的研讨。为了承认戴文进对画院和钱塘画坛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文献资料似乎象故事一样。因此,有必要对成化以后通行的戴文进传进行重新考察。尤其是所谓戴文进晚年穷死之说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这一说法依据的材料仅仅是以趣味性为旨的《春风堂随笔》。该书的戴文进传究竟有多少真实价值,尚有探讨的余地。所以,对依据贺荣撰墓志铭写的《七修续稿》中戴文进传,以及与戴氏同时代文人们写的诗文,进行充分的研究,则是非常必要了。
杜琼(1396-1474)《东原先生遗集》中有戴进的小传。据该文可知:戴进起初居于北京,以画见重,但并不显赫;晚年返回故乡钱塘后,名声日益变大,作品受到充分地尊重。【40】这段文字与《七修续稿》相同,可以说是暗示了有戴、谢争执之事,然而晚年结局却并非穷死潦倒。杜琼与戴进是时代大致相同的人物,因此《东原遗集》所记是可信的,至少比成化以后的诸评要具有真实性。关于戴文进晚年受到尊重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景泰十才子”之一刘溥《草窗集》、【41】叶盛《叶文庄公集》中的诗文得到证实。【42】在这几首略有夸张成分的诗中,刘溥《草窗集》中那首品评戴进绘画的长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戴进不仅仅只是职业画家,他还与文人们着有广泛的交往。这些事实在杨荣(1371-1440)的诗、【43】杨士奇(1365-1444)的七言诗中得到证实。【44】而且,王直(1379-1462)的一些诗暗示了戴文进的社会地位,【45】更有深刻的意义。王直的这些诗一是对戴文进的追忆,二是表明戴文进与嘉靖时期文人画巨子文征明的姻亲夏仲昭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经过这样的考察,历代戴文进传记与画评的变化过程就显得清楚起来。然而,主要是万历以后文献所载有关戴、谢争执之事,真相却难以确定。
即使戴、谢之争如已叙述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相信他晚年会穷死。可以推测,戴进与同乡、画院同事、画风相似的谢环之间,有着若干不和之处。王直、杨士奇、杜琼是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但据这些文人的诗作能够知道,【46】谢环的出身、社会地位较好,文人的教养也更胜一筹,不难想象,谢环会更受到恩宠。所以,在以画院为中心的很难期望成功吗!据《东原遗集》、《庚子销夏记》,以及其它与戴文进同时代诗人们的作品,可知戴文进作为画家而成名,无非是回到钱塘以后的事。因此不难估计,戴文进的画风在这里起到更大的影响。戴文进多元化的画风在下一代得以分化发展,也就可以理解了。
参注【3】【13】“本朝画手,当以钱唐叙文进为第一,宣庙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房。文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是《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钩于水次。画家惟红色最难著,文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庙阅之,廷很从旁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尔。’宣庙阅之,乃曰:‘大红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钓鱼,甚失大体。’宣庙颌之,遂挥去其余幅不视。故文进在京师颇窘迫。宋王士元画《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识者以为精虑入神,与《六经》合。孙酉皓进之,天子下图画院品第。高文进妒之,定为下品,止賜三十嫌。古今忌才,民曲艺亦然,可资浩叹!文进名亦偶同。”(陆深:《春风堂随笔》,见《俨山外集》卷五)
【14】“永乐未,钱唐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继而还乡攻其业,遂名海宇。镇守福太监进画四幅,并荐先生于宣庙。戴尚未引见也,宣庙召国院天台谢廷循平其画,初展《春》、《夏》,谢目:‘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丑,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又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是夕,戴与其徒夏芷饮于庆寿寺僧房,夏逐醉其僧,窃其度牒,削师之发,夤夜以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为作道、佛诸像,故今华藏、潮鸣,尚多手迹。吾友张济川家,亦有《天王斗圣》数十幅。继而廷循使人物色,戴闻云南黔国好画,因往避之。值岁暮,待门神至其府货之。其时石锐为沐公所重,石见其画,曰:‘此非凡工可为也。’询戴同郡人,遂馆毂之。然终不使之越己。又数年,谢死。而少师杨公士奇、太宰王公翱,皆喜戴画,归则老矣。先生循循愉愉,人乐与友,凡亲友不给者,每作数纸与之,人争货焉。其点染颜色,妙夺造化,铺叙远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水,较前人方出一格。其余诸家无不能。王、杨二公常称其画与古人相颉颃。卒年七十五,天顺六年秋也。字文进,以字行,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先生没后,显显以画名世者无虑数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吕纪之翎毛,杜堇、吴伟之人物,上官伯达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兼美众善,又何人欤,诚画中之圣。今得其片纸者,如拱璧焉,去后又何如哉。呜呼!公艺精而不售,展转为竞艺者所忌,卒死穷途,岂非其数哉。然而后世名画者,莫可与并,又岂非道理之不可诬哉。贺御医志墓,避时而不详,止云为艺所忌。于过横春桥,见其墓凄迷于苍莽之中,祀绝而将为人发矣。悲其亭,因掇其形,以书其传云。草桥子曰:退之有云,据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戴尝奔走南北,动由万里,潜形捉笔,几经春秋,无利禄以系之也。生死醉梦于绘事,故学精而业著,业著而名远,似可与天地相终始矣。究其当时,不过一画工而已。呜呼,世之赫赫目前,以富贵骄人者,名随身没,不知所自树,视此宁不愧诸!”(郎瑛;《七修续稿》卷六,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本)本文提到了一些事情,这是戴文进传中最详细的一篇。文中暗示了戴、谢之争,但不是红袍事件。又,后来虽然流行着戴进穷死说,但该文及戴支进同时文人们的诗中,却提到戴文进晚年返乡后,对钱塘画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推测,戴文进晚年应当是很有势力的。
提出穷死说,见于何乔远《名山藏》:
“戴进,字文进,钱塘人。临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媚自臻,凡一落笔,俱入神品,为本朝画流第一。宣庙善绘事,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及进入京,众工忌之。一日仁智殿呈画,进特以得意之笔上进,首幅为《秋江独钓图》,一红袍人垂钓水次,画家惟傅红色最难,而进独得古法。宣庙方阅,廷循从旁奏曰:‘此画佳甚,恨野鄙耳。’宣庙叩之,对曰:‘红,品官服色也,用以钓鱼,失大体矣。’宣庙颔之,遂挥去,余幅不复阅,放归,以穷死。死后而人始重之。(略)”(何乔远:《名山藏·艺妙记》)
显而易见,该文据陆深《春风堂随笔》编成。与《七修续稿•戴进传》相比,这些无非是以趣味性为旨的传说而已,以后的載进传却大多以此为底本,陆文时万历《钱塘县志》影响不深,但康熙《钱塘县志》则按陆文摘抄而成。兹陈示如下:
“戴进,字文进。画法诸家,尤长于马、夏,晚集大成。有宪使怒不供役,裸系,使先曲神荼。黄方伯见而请释之,舍所画神荼献神品画,德之也。《秋江独钓图》亦神品,入宣庙御览矣。谢廷循辈妒进,谓红衣非渔服,失体,遂挥去。困死,墓在九里松。子泉、婿王世祥,并善画,而方钺独称戴门顔子,其徒夏芷兄弟近弱,仲昂草率,皆不及钺也。”
这种说法,经过渲染,见于康熙《钱塘县志》,在戴文进传中,红衣钓士与困死之事,成为既成事实:
“戴进,字文进,宣德、正统时驰名海内。山水、人物、翎毛、花草兼法诸家。晚学纵逸出畦径,卓然一家。为人不耐拘束。时有贵官某强之画,进不肯,以微缠挛之,跪阶下.冇重进者解之,乃免。宣庙喜绘事,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妒之。一日呈画,进上《秋江独钓图》,一朱衣人垂钓水次,甚得古法。宣庙阅之,廷循从旁奏曰:“此画甚佳,但鄙野耳。’宣庙问之,乃曰:‘朱衣贵人服也,今以钓,不太亵乎!’宣庙颔之,遂挥去余幅,不复阅。进卒困死,死后而人始重之。子泉得家法,婿王世祥亦善画。”(康熙《钱塘县志》)
康熙三十三年的《杭州府志》去掉了戴文进受贵官侮辱之事,其余则与万历、康熙《钱塘县志》相同。民国《杭州府志》采入《七修续稿》戴文进传的一部分。
戴文进传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陆深较大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李诩的文章中见到其影响:
“宣德间,昆山画士谢庭循虽以画蒙宠,终日侍御围棋。时钱塘戴文进画法极高,与等辈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试,令戴画龙,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随常画龙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著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余十七人皆得用命也。盖为谢所轧云。苏州周东村说,宣宗又尝问谢曰:‘还有一載文进,闻画得好。’对曰:‘是秀才,画欠精致,是隶家画也。’卒不得进。上海陆子渊司业亦云,戴曾画山水进呈,宣宗称善,令谢视之,谢指槌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岂有穿红袍钓鱼之理?’遂弃去弗用。”(《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进不遇》,常州先哲遗书本)
李翊的生卒年及《戒庵老人漫笔》成书期皆不明确,但如《四库提要》所说,书中称世宗为“今上”,则该书的成书当不晩于万历初年。〔译者按:李翊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戒庵老人漫笔》是其晚年之作。见1982年中华书局版《戒庵老人漫笔•点校说明》。〕历代戴文进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该文所述与其它传记不同之处,在于谢环回答宣宗时,称戴进的画是“秀才”画,是“隶家(利家)”画,而不是风格“精致”的行家(职业画家)画。李翊的评画水平不得而知,但传记中所反映的见解,是与至今有关戴文进画评完全不同的。
至于戴文进为达官画门神的传说,也许是采自谢肇淛的《五杂俎》,谢文云:
“戴文进不肯为方伯作门神,方伯怒,襄以三札,右伯黄公泽,闽人也,见而问其故,笑而解释之;戴德黄甚,临行送画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笔,今黄之子尚留传其一云。技之厄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如此。”(《五杂俎》巻七)
【注释】
上述这些載文进传记的共同点,是承认載进为职业网家.其它如红袍钓士事件、受到有教养的文人画家的排挤,却具体记载有所不同,而这是他画家生涯的关键。
【15】【16】见《画品四》。该书评夏芷,丁玉川,钟钦礼,汪质、汪肇、王谔等人的山水画,认为“以上诸家,才力不甚相远,亦不须核论,总为一等”。
【18】【35】“文进,其原出于马远、夏珪、李唐、董原、范宽、米元章、关同、赵千里、刘松年、盛子昭、赵子昂、黄子久、高房山,高过元人,不及宋人。"(李开先:《画品五》)
【19】“戴进,字文进,号靜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人。山水得诸家之妙,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极其精致。喜作葡萄,配以钩勒竹、蟹爪草,奇甚!真画流第一人也。”(《图绘宝签续编》卷六,画史丛书本)
《续篇》的作者韩昂生卒生不详,似为成、弘间人,《续篇》编于正德十四年。
【20】“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人。山水得诸家之妙,凡人物、翎毛、花卉,无不擅长。宣庙时,进尝作《秋江独钓图》,(中略)迸于墨竹、葡萄等画,无不精绝,乃浙画之第一流也。”(《无声诗史》卷一,画史丛书本)
【21】阴崖万古悬,横出千岁松,中有落涧遥,怒跃数白龙。长年不闻声,发卷耳欲聋,远楚夕莽苍,町疃回照红。此域方物靜,尚有坐二翁,何必非夷布,破衣萧萧风。”(《怀星堂集》卷四《戴文进〈松崖〉》,宣统铅印木)
“峭壁遥撑落照危,蜿蜿曲陇绕修坡,前头径转峰回境,说与时人定不知。”(同上卷八《戴文进小幅》)
“黄陵庙下潇湘浦,西风作寒本作雨,鹧鸪啼舌到无声,谁管行人望家苦;钱塘书史胸蟠回,越山移过吴山来,淋漓元气口王宰,欲赋谁当老杜才。”(《枝山文集》卷西《戴文进〈风雨归舟图〉》,同治刊本)此七言律诗后半部见于《怀星堂集》卷五:
"柳州刺史幸不违,长沙太傅音尘非,翠蛾班管在何处,万古重华呼不归。”
【22】“有明国家推钱塘戴生,笔墨淋漓以雄老特名,少作花草红翠媚荣,忽复见此,藏之毛卿。丹黄交加,与石争廉棱。奇哉秀哉!亦如夸妍写冶宋广平。我思菊党陶冷陆野,故是铁石朋。戴史得其颜毛,子其同情也哉!”(《怀星堂集》卷二六《戴进画菊赞》)
“石田翁为王府博作此小册,山水、竹木、花果、虫鸟,无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时画家可以及此者,惟钱塘戴文进一人。然文进之能止于画耳,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翁当独步于今日也。”(《抱翁家藏集》卷五二《跋沈石田画册》,四部丛刊所收)
【24】“宋初,承五代之后,工画人物者甚多。此后则渐工山水,而画人物者渐少矣,故画人物者可数而尽。神宗朝有李龙眠,高宗朝有马和之、马远,元有赵松雪、钱舜举,吾松张梅岩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进,此皆可以并驾古人,无得而议者。其次如杜桎居、吴小仙,皆画人物,然杜则伤于秀娟而乏古意,吴用写法而描法亡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巻二八)
【25】“我朝善画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以沈石田为第一,而唐未如、文衝山、陈白阳其次也。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其人物描法,则蚕头鼠尾,行笔有顿跌,盖用兰叶描而稍变其法也,自是绝技。其开相亦妙,远出南宋已后诸人之上。山水师马、夏者亦称合作,乃院中第一手。”
“衝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而未尝不行者也。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能兼利,此则限于人品耳。”(同上卷二九)
“明宣庙召戴文进入京,为画院谢廷循所忌,逃归杭,隐于诸寺,为作佛教诸像,,今东城华藏、潮鸣二寺挂轴尚有存者。杭人相传,文进初为银工,所造钗朵种种花鸟、人物,精巧绝伦,思以是传于后。后见销银者,即己手制也,悔而学画,遂有名。其女亦工画。文进墓在西湖横春桥。"(厉鶴《东城杂记•戴文进画迹》,粤雅堂丛书所收)
该文许多地方是据郎瑛《七修续稿》而成,但《续稿》中却无戴文进出身银工之说,这部分当引于其它资料。
【27】“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进字文进,钱塘人也。宣宗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进《秋江独钓图》。画人红袍垂钓水次。廷循从旁跪曰:‘进后极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钓鱼。’宣宗颌之,遂麾去,余幅不视。故进住京师,颇穷乏。先是进锻工也,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熔金者,观之,即进所造,忧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精,意将托此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阮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绿素,斯必传矣。'进喜,遂学画,名高一时。然进数奇,虽得待诏,亦穂轲亡大遇。其后疏而能密,著笔淡远,其国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钦进锻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赞略)”(毛先舒:《画苑三高士传•戴文进传》,见张潮:《虞初新志》,文学古籍刊行社本)
该传与《东城杂记》相同,主要依据郎瑛之说,再加一些其它资料。它所引的其它资料,可能与《东城杂记》所引来源相同。唯该传提到戴文进曾是锻工,而不是银工,这对研究其国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28】【31】“文进画在明初名甚噪,然其风格不高,马远、夏珪之流派也。予所收《灵谷春云图》,是其合作,设色布景苍秀,有宋、元大家风,使掩其款而阅之,未有信其为文进者,乃为聂双江大年所作。景.有一帖附后,字亦甚工,不似道学人笔。按,王文端直为冢宰日,曾以诗寄文进求画,且自序:'昔与静庵交,尝作一诗,至是十年始成之。’聂双江題其后云:’公爱文进之后,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贤,岂复有遺才哉!'文端闻其言,笑置之。未几,聂举为史官,困于讥谗,卧病旅邸,投诗于文端,有云’镜中白发难饶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千里故人分塗少,百年公论盖棺这’。文端得诗泣下曰:’是欲吾铭其墓耳!’聂果殁,文端为墓志,有云:’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拟荐,而乃止一校官耶!’前辈以道义相成如此。然双江讥文端好文进之画,观.双江与文进之帖,又何倾慕笃切耶!
"文进画有絶劣者,遂开周臣、谢时臣之俗。至张平山、蒋三嶽等,恶极矣!皆其流浪也。不有文、沈两公一起而继家、元之绝.学,风推不几扫地耶!世传宣届时召文进至京,令作《钓雪图》,一人衣绯。有潜者谓:’绯乃朝服,不宜钓鱼。'遂罢回。此三家村中语也。宣庙善画,尝见御制《雪山图》,一人衣绯策杖入寺,此岂朝服耶?其不取文进,定有在也。"(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三《戴文进〈灵谷春云图〉》,风雨楼刊本)
【29】“戴文进作图凡七帧,曰:《浣溪春行》、《卧听松泉》、《竹溪夜泊》、《雷峰夕照.》、《凭栏待月》、《西湖函霁》、《东篱秋晚》。予初阅之,以为沈启南作。见题字不工,及验其印章,而始知为丈进也。然无一笔钱塘意,苍老秀逸,起出蹊径之外,乃知此君与启南无所不师法,妙处亦无所不合耳。吾乡陆太宰全鄉各系以诗,其跋后乃云:’岁乙亥七月寒疾,卢院判宗尹愈之,未有以报。而卢君素轻阿堵物,乃举以遗之。选事稍暇,当为君每景赋,一诗以寄兴。’然则七诗盖为卢补书也。今年乙亥忽得此于友人,而予与陆公后先丁未进士,各一甲子,其事颇奇。陆公在政府尚能以其阂成此雅话,而金饱饭山镇中,其容卷惑耶,因感而火于后。"(王世贞:《弁州小人四部稿》卷一三八《文部•戴文进〈七景图〉》)
《七景图》不知尚存于世间否,孙鉱《书画跋跋》卷三有著录。
【30】“钱塘戴文进生前作画,不能买一饱,是小厄。后百年,吴中声价渐不敌相城翁,是大厄。然令具眼观之,尚是我明最高手。此卷奕奕秀润,境意似近而远,尤可宝也。”(《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八《戴文进〈山水平远)》)
本图亦与《七景图》一样,著录于孙鉱《书图跋跋》卷三。
【32】作为画家,聂大年的资料较少。限于管见,除《画史会要》有所记载外,其它书画著录并无他的资料。《画史汇传》中的聂大年传,是据《明史列传》《临川志》《画史会要》《詹氏小辩》《蓉塘诗话》等摘抄而成:
“聂大年,字寿卿,临川人。宣德末荐起为仁和训导,景秦乙次荐入翰林。山水宗房山,颇得清淡之趣。埒沙群书,笃志古文及唐宋诗。书法北海、吴兴。诗、文、书、绘,世皆珍之。初,父同文官翰林待制中书舍人,后燕王入京师,迎谒道喝死。后五月而生大年,母氏抚之。比母卒,归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贤行,上之有司,诏旌其门。尚书王直以诗寄钱塘戴进索嘉,自序:‘昔与进交,尝戏作诗一联,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題其后曰:‘公爱进画十年布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贤者,宁复有遗贤哉!’直闻其言不怒,亦不荐。及大年疾笃,作诗贻直,有‘镜中白发孰怜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基耳。’遂为之志。”(《画史汇传》卷六一)
这篇《聂大年传》没有引用《教谕聂大年墓志铭》这基本史料,该文见于王直《抑庵集》卷三四,亦收录于《国朝献征录》,其是《名山藏·聂大年传》及《庚子销夏记》、《明史列传》等有关聂大年传所本。一般认为他是诗人,叶盛《水东日记》有“聂大年诗为三十年来作家绝唱”之评。此后,《明诗综》、《明诗纪事》等皆收有聂大年传。如同姚夔《挽聂大年先生)诗所述,他笃志诗文(见《姚文敏公集》卷四),而对其画作,却未见谈及。注【28】所载孙承泽评戴文进画,我们虽不能据此而知道聂大年的具体画风,但据该文我们可以知道,聂氏画风宗高克恭,应是典型的文人画家,其与戴进、沈周、高克恭等有相同的笔墨艺风,则当为无疑的。
【33】此图乃钱塘戴文进作,有程南云篆额、杨文贞诸公题咏。文进自谓仿陈仲梅,而中间大有米襄阳笔意,唯落色稍过浓润耳。茅屋中红袍人,岂《秋江独钓》例耶!文贞二绝作古隶,颇峻整。吴余庆及南云皆以书名,而不能佳。有鲍相者,书甚婉媚有韵,而不以书名。皆所不可晓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八《城南茅屋图》)
【34】关于何澄的画,在汪氏《珊瑚网·画录》等二、三种书中有所著录。但画的内容却不得而知。而其传记资料,在《明画录》、《常州府志》中有简略的记载。此外,尚有二、三种别集载有泳其画的诗歌。关于何澄的画风及其与戴进绘画的关系,拟在后文讨论戴进画迹与画风时进行研究。兹将上述有关何澄的资料介绍如下:
“何澄,字彦泽,号竹鹤老人,江阴人。官衰州守。工山水,宗米元章,烟云窗霭,雾气浮动,而不免浙派之目,要非通论。”(《明画录》卷三)
“何澄,字彦泽,江阴人。永乐间举于乡,初以部郎言事件旨,该武当。已复上声激切,下诏狱。宣德间荐摧衰州牧,与民休息,岁歉不闻告遗。正统中乞休。”(光绪《常州府志)卷二三)
“竹鹤老人天下稀,笔端云物写心机。黄茅海绩孤舟雨,犹是衷州解印归。”(张琦:《白斋诗集》卷三《何太守山水画〔何公澄尝守哀州〕》,四明丛书所收)
“宣阳太守多公暇,肆笔云山出潇洒。层峰受翠凌苍空,英英玉气浮鸿术。缥缈漪漫浑无迹,妙逼房山高克恭。(略)”(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五七《萧启御史赴山东金宪,以何澄所画云山求题》,明刊本)
【36】“万历三十七年七月九日(略)。戴文进《溪山清隐),仿子久,粗笔亦疏爽。”(《味水轩日记》,嘉业堂刊本)
【37】“临模古画,着色最难。(略)国朝戴文进临幕宋人名画,得其三昧,种种遥真,效黄子久、王叔明画,较胜二家。(略)”(屠隆:《考集余事》卷二《临画》,宝颜堂秘菠所收)
【38】“明兴,善丹青者何含数百家,然其最驰名者,不过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禽鱼不过数种,而吾吴大约独踞其太半,即尽诸方之烨然者不敌也,聊志于后。画院祗候至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绘事,而是时戴文进被征,独见谗放归,以穷死。文进,名琏,钱唐人,死后始重之,至以为国朝第一。文进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珪,而妙处多自发之,俗所谓行家兼利者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五)
【39】“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人。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珪,而妙处多自发之,俗所谓行家兼利者也。神像、人物、杂画无不佳。宣德初征入画院,见谗放归,以穷死。死后人始推为绝艺。”(徐沁:《明画录》卷二)
【40】“右画卷口口共二十余纸,皆本朝永乐、洪熙间名士之所为,为吴人沈启南之所集者也。间尝示予观,既且请识焉。予虽不晓画意,然画者之平生颇知之。(中略)戴文进作画,通诸家,一一臻妙。初居北京,以画见重,无所荐达。晚乞归杭,名声益重,求画者得其一笔,有如金贝。其女、其婿颇似之而不及。”(《东原先生遗集》)下《影沈氏书卷》,道光刊本)
【41】“近代何人画山水,松雪仙游大痴死,眼前虽有十余辈,各妙一家而已矣。戴公家数合精粹,波绿妆青无不是,荆关董郭迭宾介,奴隶马夏儿道子。问公何自得三昧,口不开言但摇指,想凭造化会精神,默运玄机故如此。人家往往见屏障,或但咫尺或千里,其间为状多不一,一一惊人俨何拟。或撑高哭出烟雾,或卓长剑空中倚,或付炊散秋淋漓,或布星阵围壁墨。微澜或似铺文笔,巨浸或又迷涯涘,或规秀蛾或细腰,或结琦璜或瑜珥。千奇万怪尤有甚,鬼物踉跄复喂垒,梵无龙象匝佛座,瀛海鲸鳌载仙履。响来我亦得一幅,解谷且徕切撼几,苍龙坑蜓华飞云,彩凤盘翔幸来止。紫芝埃草寓我意,白璧黄金只叛尔,高堂寿席光照耀,见者至今夸不已。钱唐自昔称都会,湖水清深天目峙,君家住在湖山中,茅屋萝窗带香芷。自从征来入艺苑,寻常粉墨都披靡,古来妒作必由类.丑拙今知赖奢碱。绿槐高柳长安阳,车马杂杳门如市,驱山走海春复秋,日月西奔水东驶。当今圣人念良弼,痞寐不忘思治理,烦公肖写傅岩臣,老去益推良画史。”(《草窗集》上《赠钱唐画师戴文进》,明刊本)
著者刘溥的生卒年不详,大致当与戴文进同时。此诗显然是戴文进晚年退隐钱塘后刘溥的赠作。
【42】“钱唐老戴绝世无,往往人家看画图,自言此幅不易得,夏珪马远真吾徒。苍然两山屹相向,稳卧虬龙势千丈,下有飞泉喷玉虹,百日喧喧起涛浪。石阑半倚莓苔青,两翁谁为双鬓星,清谈直穷点头处,余字有耳那能听。城中车马纷如簇,满眼利名终未足,丈夫出处贵有道,岂在区区万钟粟。关西公子廊庙人,我本山林旧日贫,相逢一笑未能去,且须对此娱心神。”(《泾东小稿》卷一《戴进画为叔简兄题》,嘉靖刊本)
叶盛生于永乐十八年(1420),卒于成化十年(1474)。至于叔简的情况,笔者浅学而不知。但此诗与刘溥、杜琼的诗不同,虽然从诗中不能断定戴进与叶盛有直接的交往,然而这是与我进同时的人评戴画之作,从中可知,作为画家,戴进晚年居于钱塘是负有很高的声誉的,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43】“戴君旧业家钱塘,幽斋剩种青筼筜。冰森玉立郁萧爽,佩珂时动音铿锵。一林遥接淇园绿,万个如临渭川曲。凉宵白昼风月清,翠影重重覆书屋。四时佳致迥不同,况兹清绝当严冬。朔风吹雪满空下,凝梢缀叶相玲珑。素娥冉冉来云表,皓鹤翩翩舞林杪。是时掩卷一凭栏,清兴满襟应不少。恍如玉壶照八窗,牙签玉轴生辉光。开径便宜同蒋诩,映书更觉慕孙康。一从寄迹京华地,翘首山房想初志。阳春桃李任纷纷,劲节贞心自无异。何人为君写此图,故乡景物浑不殊。兴来展玩对立久,一点尘埃窗外无。”(《杨文敏公集》卷五《竹雪书房为画士戴文进题》,明刊本)
这首诗所味也是戴文进归钱塘后之事,同《抑庵集•湘江雨意图诗序》一样,这首咏戴文进生活的诗洋溢着亲切之感。"画士”之称起源不详,但南宋及元代都有将职业画家称作"画士”的例子。该诗称戴文进为"画士",就表明戴文进是职业画家,其人格也得到充分地认识。可是成化以后,人们渐渐对职业画家产生偏见,我在本文中作了论述。"竹雪书房”不用说,应当是戴文进的书斋名,杨士奇也有题咏。
“纷驰名利不知劳,马首红尘十丈高,谁似钱塘戴文进,小斋无事玩湘皋。”(《东里续集》卷六二《题戴文进〈湘江雨意卷〉二首》,第一首略)
“分栽修竹已成林,每到严冬雪积深,斋馆相看不曾厌,只缘俱有岁寒心。
"此君高节净娟娟,况复瑶华相映妍。王子斋居足清兴,定知不棹剡中船。”(《东里续集》卷六二《题載文进竹雪书房二首》)
这些诗表明杨士奇对戴文进的倾倒之情。从诗中看,戴文进在书房周围栽有竹子,他与那些追名逐利的人相比,过着安宁的书斋生活;这些诗也说明戴进在京师仕途不遇后,便回到了故乡钱塘,杨士奇卒于正统九年,戴进的归隐应在宣德未,而不是正统初年吧。
杨士奇又有题戴文进为严御史恭画《梅边读〈易〉图》长诗,系戴文进贺严恭升任贵州参政所绘。关于严恭,可从杨士奇这首长诗中略知一二。
【45】“长林萧萧初过雨,春笋惊雷皆出土,东风浩荡天上来,一夜吹嘘长尺许。老竹苍然乃其祖,劲势峥嵘谁敢侮,眼前玉立见诸孙,变化终当拂云去。天生万物各有时,稚壮强弱常参差,何如此君虽异等,岁寒高节同襟期。戴公戴公能有此,披图一见心为喜,龙山道人久已死,遗墨至今犹在纸,平生故人吾老矣。”(《抑庵集》卷三《题戴文进〈公孙同节图〉》,隆庆刊本)
诗中“龙山”,大约是浙江杭其南卧龙山的别名,诗中“龙山道士”想必为戴文进了。唯“久已死”之句较难解样,因为王直、戴文进皆逝于天顺六年。或许这首诗作于王直临死前不久,在此之前,说不定戴进也在天顺六年早就去世了。
这首诗是王直逝世前的作品,那另一首就是王直在戴文进归钱唐时的作品:
"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履,半蒿烟水一渔簔。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从寻阳迹,满头白发愧蹉砣。”(《抑庵集》卷六《送戴文进归钱塘》)
“钱塘戴文进雅好竹,尝于竹间作屋以居,自谓不可一日无也。及来北京,而土不宜竹,居闲独处,盖未能忘于心。其友夏仲昭辈,欲娱适其意,为作三图,长皆逾二尺,而苍然玉立,隐见于烟雨空门濛之中,有潇湘千里之势焉,名之曰《湘江雨意》。文进甚喜曰:‘凡吾之托好于竹者,欲适意焉耳。今得此,意亦适矣,何必眷眷于旧哉!’少保黄公为之记,士大夫多为献诗。文进持以求予序。予以文进同其好者也,予家泰和城西溪上,旧有竹万竿,先大父作亭处其中,当时名公歌咏之。岁久芜废,近稍修复旧观,郁然可乐也。而予乃窃禄京师,不得以岁月处焉,其往来于怀,盖亦与文进同也。今年于私第作小轩,名之曰水竹居,求仲昭作巨幅置壁间,公事之暇,饮食起处必于是,宛然故园风致也。兹夏于文进见之,然则使予二人居京师而兼有林泉之适者,非仲昭之力欤!虽然,古人之托意于物者,冀有益于己也,故君子于竹拟德焉,以其清虚劲直可尚,已能取诸物以求益,虽似犹真也。不然,虽真奚适哉!故予于仲昭之画,盖以为德之砺而不敢忽焉。丈进与予同其好,亦必与子同此心者矣,故为序其诗而相与道之。”(《抑庵集》卷二一《湘江雨意图诗序》)
这首诗比上一首创作时期更早,大概是戴文进在京时王直所作。当时戴文进与诸名士交友,其中与王直、夏昶的关系较为亲密,而夏昶(仲昭)之女与吴愈所生的第三个女儿,即是文征明的妻子。这就使人不禁想起丈征明在嘉靖文人画坛的地位,必然也要联想到他妻子的祖父与戴文进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些情况,可能会改变后人对戴进的徧见。成化至嘉靖时期,吴派文人画坛存在的复杂姻戚或关系,亦可从中窥见一斑。
说明谢环家世情况有如下一文,作者梁潜生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卒于宣德五年(1430),可以想象,他是谢环的先辈。
“永嘉谢廷循,其先世尝以文学显于宋、元之间。至廷循,益好学而工于画。永嘉多名山,华盖、紫福、松台诸峰环城,远丘状如北斗,故世称为斗城。其尤秀者曰谢山,以晋康乐公尝游其间而得名者也,廷循家城中,筑楼高出城外,每图画之倦则凭高而望山,有足爱者,层岩重壑,或离立乎远空,或屹然近在几下,而云气之往还,光景之卷舒,蓊然耳深隐,辉然而明霁,使览之者爽然而目快。虽能赋之士艳襟发舒,然徒得之于其目,郁乎其中者,口固不能道也。由是好事者为题之曰诗意楼。廷循以求予记之。(略)”(《泊庵先生文集》卷三《诗意楼记》,抄本)
关于谢环受皇帝厚宠之事,可见于王直下列二文:
“永嘉谢庭循既读儒书,而尤精绘事,其言行不悠于礼义,温然有君子之风。永乐中有荐于上者,征至京师,校艺在高等,遂蒙宠用,隐然名动四方。宣宗皇帝嗣大宝位,讲道论治之暇,颇以书画自娱,庭循得日侍左右,凡所进御莫不称旨,遂摧为锦衣卫百户。未几,升千户,恩遇之隆,鲜有比者。宣德元年十月一日,上御文华殿,赐白金图书二,皆涂以黄金,嵌以青玻璃。其文一曰‘笔精入神’,一曰’谢氏庭循’。八年七月一日御斋宫,踢象牙图书一,文曰‘清泉白石’。前后凡三,皆镂‘大明宣德御踢’六字于其钮,而饰以金,使凡作画则用此为识。庭循既拜赐,宝而藏之若拱璧’。(略)”(《抑庵集》卷一三《御踢谢庭循图书记》)
“哀翰一卷,百户谢庭循之所宝者也。(略)陛下以是赐庭循,岂非欲其勉修巨节也欣!然庭循之心当何如哉!(略)”(《抑庵集》卷二七《恭题谢庭循所藏哀翰卷后)
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谢的评价要比戴文进高,既可见于《抑庵集》卷十三,也可见于杨士奇《东里续集》的一些诗文。现录其中一篇如下:
“雍容而夷坦,恬憺而静贞。弗伉弗妩,靡雕靡矜。抗浮云兮素尚,含清风兮雅咏。寄妙翰于林峦,亦自怡其情性。躬承当宁之知,日侍幾务之余。隆宠禄之屡进,执敬畏而若虗。所履之确,所存之厚,盖举世高其艺,而君子重其守也。”(《东里续集》卷四五《谢庭循像赞》)
从上述与谢环同时的文人们的诗文中,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他人品的评价。杨荣(1371-1440)《杨文敏公集》中的一篇文章,今有原文手迹遗存,藏于镇江博物馆,即《杏园稚集图》后杨荣题的《杏园稚集后序》(载于《文物》1963年第四期)。但手迹与文集所载文字略有异,不用说,当以《文物》所刊手迹为准。其《后序》称,正统二年三月一日,馆阁诸公访杨荣所居之杏园,浙江永嘉谢廷循亦来会。是日春景澄明,惠风和畅,华卉竞秀,诸人饮酒弹琴,赋咏作乐,而谢环精于绘事,作图记此胜状。与会者有杨士奇、杨荣、杨洋,世称“三杨”,又有王英、王直、钱习礼、周述、李时逸、陈循等,皆为当时名流。杨荣为谢环此图作序,其余八人皆有题咏。
至于该图的真伪,在未能亲见实物之前,以及图版照片欠清楚的情况下,难以判断。不知收藏者是否比较了其它谢环的遗作。
[日]铃木敬
任道斌译
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