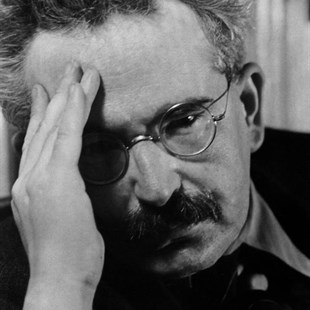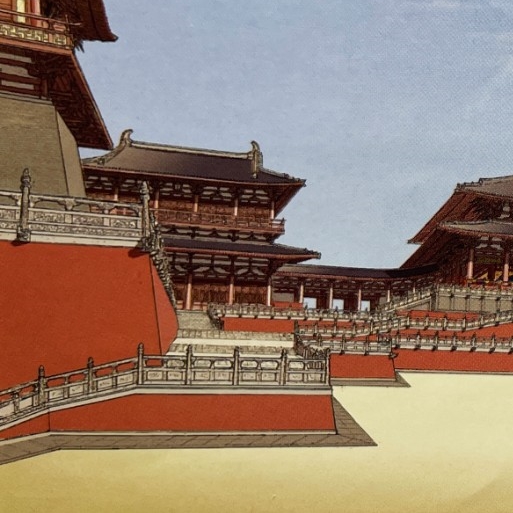严格地说,所有的视觉现象都是由色彩和明度造成的。规定形状的界线来自眼睛对属于不同的明度和颜色的面积进行区分的能力。造成三度形状的重要因素——明与暗的区分,也来自这同一根源。甚至于在用单线勾的画上,也只有通过墨水和纸之间的明度和颜色的区别,才可以看出形状。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把形和色说成是两种独立的现象。园形和角形是完全不受那使它们显现的特定明度的制约的。黄地子上的绿色圆盘和蓝地子上的红色圆盘都是一样地圆,而白地子上的黑三角形和黑地子上的白三角形还是一样的三角形。
形和色
由于形和色可以彼此区别开来,它们也可以相互比较。二者都可以完成视觉的两个最独特的功能:它们传达表情,它们还使我们通过对物体和情况的辨认而获得讯息。一棵高耸的白杨的形状带有一定的表情,跟一棵白桦的形状和表情不同。吉昂蒂酒的红颜色所具有的味道跟索特恩白酒的味道不同。形状使我们能够识别事物,但是,颜色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在看黑白电影的时候,我们往往难以辨别演员盘子里的奇形怪状的食物。在信号、图表和制服上,颜色是被当作一种通讯手段来使用的。
可是,形状是一种比颜色更为有效的通讯手段;另一方面,用形状却不能取得颜色的表情效果。形能造成如面孔、叶子和指纹所显示的那样千变方化、层出不穷,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的图样。文字用的是形状而不是颜色,因为形状为我们提供的符号,书写方便可靠,字体呈小,也能辨认;可是,如果把颜色的区别用之于相同的目的,我们能够放心依赖的色价不过半打。但是,就表情而论,最显著的形状的效果也比不上落日或地中海蓝的效果。
在心理学的实验中阐明了人们对颜色和形状的反应的差别的意义。在一种为各种不同的调查者所使用的装置中,要求孩子们从许多红三角形和绿圆形中选出那些和分开陈列着的试验图样相似的图形。试验图样或者是一个红园形,或者是一个绿三角形。不到三岁的孩子们好象更常以形为基础进行选择,而三到六岁的孩子们则挑拣颜鱼相符的图样。学龄前的儿童从事这些选择时毫不犹豫,而那些六岁以上的孩子则由于任务含糊而感到困惑,他们更多地用形作为他们选择的标准。维尔纳(Werenr)在评论这个材料时提出,年幼的儿童的反应是由运动习惯所决定的,因之,是由物体的“可把握的”属性所决定的。一旦可视的特征占了优势,学龄前儿童的大多数就会被对颜色的强烈的知觉要求所支配。但是,当教育开始对儿童进行实际技能训练的时候,这种训练对形的依赖更重于对色的依赖,他们就又更加倾向于把形作为辨认的决定性手段。
在色与形之间进行选择的情况也可以在墨点试验中加以研究。有些洛夏赫卡片为观察者提供了把对所见到的东西的描述建立在重色轻形或重形轻色的基础之上的机会。一个人可以按照图样的轮廓来辨认这一图案,尽管颜色和解释有矛盾;反之,另一个人则可以重色轻形,把两个并列的蓝色方形说成是“天空”或“勿忘侬花”。洛夏赫(Rorschach)和他的追随者们断言这种反应上的差别和人的个性特点有关。这种观察原来是对精神病人做的,洛夏赫发现,心情快乐的人易于对颜色起反应,而抑郁的人则更常常对形起反应。颜色反应占优势表明对外来刺激的一种开放状态。这样的人敏感、容易受影响,不安定,散漫,易于感情激动。一个偏向于对形起反应的人具有内向的性格,对冲动的控制力强,具有一种学究式的、不易动感情的态度。
为什么知觉态度和性格有这样的联系,洛夏赫对此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但是,沙赫特尔(Schachtel)曾经指出,色彩的经验类似感动或情绪的经验。在这两种场合下,我们往往是刺激的被动的接受者。一种情绪并不是主动进行组织的意识的产物。它仅仅预先要求一种开放状态,这种状态,举例说,一个抑郁的人是不会有的。情绪打动我们正如颜色打动我们一样。形,相反,仿佛需要一种更为主动的反应。我们察看对象,确定它的结构架子,把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同样地,有控制的心境起作用于刺激冲动,它应用原则,整理种种经验,并决定一系列的行动。广义地说,在色彩视觉方面,作用来自对象并对人发生影响;要看出形状,进行组织的意识就要对客体进行观察。
刻板地应用这理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色彩造成的是一种在本质上属于情感的经验,而形则相当于理性的控制。这样一种公式似乎太狭窄,如果将它用之于艺术,就更为狭窄。对于色彩反应来说,观者的被动状态和经验的直接性是更为典型的,而对形的知觉则以主动的控制为其特征,这或许是真的。但是,只有通过对色调变化的整体进行主动的组织,才可以画成一幅画或了解一幅画;另一方面,在观看富于表现力的形的时候,我们又不禁为之倾倒。我们可以更适当地区分对于视觉刺激的两种态度,用它代替色彩反应和形状反应的说法,其一是对视觉刺激的接受的态度,它适宜于色彩刺激,但也可以用之于形的刺激,另一种是更为主动的态度,它通常用之于对形的知觉,但也可以应用于色彩构图。更为普遍地或许是(色彩的,但也是形的)表情的性质自然地感动了被动地接受的意识,而图形的结构(这是形的特性,但色彩也有)则和主动地组织的意识有关。
人的性格的相应的特征也不必局限于感动的态度和理智的态度之间的区别。在前一类型中,不仅只有激情,而且还有我们得到的灵感——似乎不知从何而来——以及对于外在世界的开放状态,外在世界要通过感官才能感动人心。在第二类型中,不仅只有理智,而且还有人的意识的组织能力,这种意识的组织能力直觉地籍助于往往是低于有意识的推理水平的心理过程来指导我们和人们打交道,处理情况,解决任务。并且,这一类型,如洛夏赫所指出的,还包含由于致力于思考而形成的人的内省心理,人往往用预先想好的方法处理他的经验。
在艺术领域中对知觉态度和性格结构之间的这些相互关系进行探索,是有意思的。第一种态度(重色轻形)可以叫做浪漫的态度;第二种(重形轻色)可以叫做古典的态度。在绘画方面,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德拉克洛瓦的态度和大卫的态度。德拉克洛瓦不仅以动人的色彩配合作为他的构图的基础,而且也注重形的表现性能。大卫不仅主要地以形的语言进行表现,用形对人物作相对静止的刻划,而且还使用柔和概括的色彩。
马蒂斯曾经说过:“如果素描是属于心灵的,色彩是属于感官的、那么,你必须首先画素描,培养心灵并能够把色彩导入心灵的轨道。”他所表述的正是这样一种传统见解,即认为形比色彩更重要,更高贵。普珊说过:“绘画中的色彩好象是吸引眼睛的诱饵,正如诗歌中的韵文的美是为了悦耳动听一样。”这种见解的日尔曼翻版可以在康德的著作中找到:“在绘画、雕刻,实际上在一切视觉艺术中,在建筑、园艺中,就其做为美术这个范围而论,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设计构成审美趣味的基础,只是通过其使人喜爱的形状,并不是通过在感觉上令人愉快的因素。那装饰外表的色彩起的是刺激作用。它们可以使物体生色引人,但不能使它成为经得起观摩注视的美的对象。确切些说,色彩往往受到对美的形的要求的颇大限制,并且,即使是在容许色彩刺激的场合,也只有通过形才能提高色彩的作用。”接受这样的见解,我们对于把形看作男性的传统品德,把色彩当作女性的魅力,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依照查理·勃朗克(Charles Blanc)的说法,就是“必须把素描和色彩配合起来才能产生绘画,正如男女的结合才能孕育人类一样,但是,素描必须保持它对于色彩的优势。否则,绘画就要迅速走向崩溃;绘画由于色彩而衰败,正如人类由于夏娃而堕落一样。”
对色彩的反应
色彩能有力地表达情感,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论的。人们曾试图说明各种不同颜色的特殊表情并从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的象征性的用途来进行概括。但是,关于这些现象的由来,所知甚少。固然,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是,色彩的表情是以联想为基础的。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使我们想到火、血和革命的涵义。绿色唤起对自然的爽快的想法,而蓝色则象水那样清凉。但是,联想的理论在这里并不比在其他领域里更使人感到兴趣和鼓舞。色彩的效果非常直接并且具有自发性,不会只是由知识附加给它的某一解释所引起的。另一方面,还不曾有过可以说明色彩对机体的影响的这样的心理过程的假说。对形的讨论,我们倒是有比较坚实的根据。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把特定的图形的表情和更为普遍的属性如空间的定向、平衡、或轮廓的几何特征等的表情联系起来。我们甚至能够对可以说明某些形的特殊效果的脑部活动过程进行推测。
在色彩方面,却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强明度,高饱和度和相当于长波振动的色相可以引起兴奋。明亮的纯红比柔和的灰蓝芭更为活跃。但是,特定的强光对神经系统有什么作用,或者为什么振动波长度会对神经系统发生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资料。某些实验曾用实例表明人体对色彩的反应。费厄(Fere)发现,肌肉的机能和血液循环在不同色光的照射下发生变化,“蓝光最弱,随着色光变为绿、黄、橙和红而依次增强”。这一点和心理学上对这些颜色的效果的观察正好符合,但是,并没有讲明是否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感觉现象的一个次要的结果,或者是否光能对动作和血液循环还有更为直接的神经上的影响。高尔德斯坦(Goldstein)所做的观察也证明同样的情况。例如,他在治疗神经病的实践中发现一个小脑有病的患眷当她穿红衣服的时候,平衡感觉就发生混乱,头晕目眩,几乎要摔倒,当她穿绿衣服的时候,这些症状就消失了。高尔德斯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他要求有同样脑病的患者注视一张有颜色的纸,同时将两臂平举前伸。两臂被一块平放的板遮起来,以免病人看见。当恿者注视一张黄色纸的时候,由有缺陷的脑中心控制着的他的手臂就会偏离中线5公分。对红色,偏离度为50公分,对白色为45公分,对蓝色为42公分,对绿色为40公分。当他闭起眼睛时,偏离度是70公分。高尔德斯坦断定,相当子长波的颜色引起扩展的反应,而短波的颜色则引起收缩的反应。“整个机体··…由于不同的颜色,或者向外胀,或者向内收并向机体的中心集结。”
画家康定斯基对颜色的面貌的论述和这种肉体的反应是相符的。他断言,一个黄色的圆形呈现“一种从中心向四外的扩散运动,几乎是直逼观者而来”;一个蓝色的圆形“显示一种(象蜗牛缩藏在它的外壳里那样的)向心运动,并且离观者而去。”高尔德斯坦的试探性的研究结果值得加以贯彻。在关于颜色效果的这样的实验中,必须确定各种颜色在明度上要相同。普列赛(Pressey)在一次较早的调查研究中,让人们在不同的照明下从事简单的运动活动,如有节奏地轻叩手指等。他发现在暗淡的光下活动就减弱,而在明亮的光下活动就增强。不同的颜色并没有使动作发生变化。
冷与暖
对各种不同的颜色的表情进行更为概括的分类,还很少做过什么尝试。暖色和冷色的区别是相当普遍的。艺术家们使用这些术语,在关于色彩理论的书籍中也提到他们。但是,这些以它们的作者的主观印象为根据的简略的论述没有为心理学理论提供令人满意的材料。阿莱希(Allesch)关于这方面的实验观察,就他提到的简短的材料来判断,看来所得的结果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提出我自己的理论,或许是可以允许的。它还没有经过实验上的检验,可能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至少它将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射击目标。
“暖”、“冷”这两个词和纯色相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它们有关系,看起来红将是一个暖色,蓝将是冷色。纯黄看起来也会是冷的,但是,这就更不一定了。这两个词只有当它们指的是某一颜色偏向另一个颜色的时候,才获得它们的特有的意义。发蓝的黄或发蓝的红往往看起来是冷的,而发黄的红或发黄的蓝也是这样。相反地,发红的黄或发红的蓝则看起来是暖的。我的论点是,决定效果的不是那为主的颜色而是那略微偏离它的颜色。这将导致或许意料不到的结果,即发红的蓝看起来是暖的,而发蓝的红看起来是冷的。把两种等份的颜色调合起来,其冷暖效果就显得不明确。绿,这一黄和蓝的调合,会最接近于冷,而红和蓝的等份调合为紫,红和黄的等份调合为橙,则趋向于中性或含糊不清。只可是,在一个调合色中的两种颜色的平衡是很不稳定的。其中的一种颜色很容易弄得压倒另一种颜色。观察者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做到这点。在一定的的限度内,他可以使自己把某种橙看成是被黄减弱了的红或者被红减弱了的黄。我可以预言,第一种看法会把这颜色看成是冷的,第二种看法会说是暖的。同样地,把一种紫当作蓝红看会是冷的,而当作红蓝看则是暖的。对于绿,两种看法的结果都会是冷的。在一个调合色中,确立一种颜色对另一种颇色的优势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周围环境中其他颜色的影响。同化和对比现象往往突出一种颜色而压制另一种颜色。这样,调合色的不稳定就大大地减弱了,从而也就可以更确切地规定它的“温度”了。
如果这个理论是站得住脚的,就可以把它推广到一般的色彩表情上去。造成色彩表情特性的,可能并不是由于占优势的色相,而是由于它的“加塞儿”。也许,那些基本色相都是相当地中调色价,它们的区别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特定的表情,而是由于它们都是各具特色并且互相排斥。而只有当一种颜色由于倾向于另一种颜色而造成一种有力的紧张效果的时候,它才显示出它的表情的特性。纯红,纯黄和纯蓝可以作为色的零级,稍微有一点力度,因之稍微有点表情;但是,发红、发黄和发蓝的颜色,由子要拉着另一种颜色离开它自己的基本性质,就会造成紧张状态,没有这种紧张状态,就不可能有什么表情。我的意见或许是不严谨的,不过在一个如此缺少理论的研究领域里,提出这么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设似乎总比没有好,唯其如此,或可被容许吧!
但是,一般的颜色表情,特别是它的冷暖,不仅受色相的影响,而且还受明度和饱和度的影响。由于这一事实,情况就更复杂了。因此,色相的表情价值只是在另外两个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比较。例如,在太阳光的光谱中,所有的色相都是高度饱和的(虽说并不相等),但是在明度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光谱色中最大的亮度在黄色带,从这点起,向两边不断减弱,直到两端,即红色带和紫色带。有迹象表明、高明度往往使颜色发冷,而低明度则使颜色发暖。因此,为了确定,例如纯红比纯黄暖,我们必须拿同等明度的红和黄作比较。
饱和度,或色度,抬的是一种颜色的纯度。记住音乐里所谓的音色,可以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它的性质。一个完全纯的音调是由一种单独的波长的声音能量造成的。这样一个声音的单纯性相当于振动的简单波形,可以由一个规则的正弦曲线来表示。可是,在实际上,音调是由不同的波长的混合造成的。各种不同的波长的结合形成一个复合形状的曲线,因此,声调的声音是不纯的,同样地,一种完全纯的颜色是仅仅由一种光的波长造成的。光谱上的饱和色相最接近于满足这个条件。当不同波长的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的时候,形成的振动就变得相应地复杂了;其结果就是一种看起来比较暗淡的颜色。把颜色和一种完全无色的灰调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最低的色度。两种颜色合在一起可以造成这种效果的就是所谓互补色。一种合成色的组成颜色越接近于是互为补色,该合成色看起来就越灰。
可能达到的饱和程度随颜色的明度而各不相同。在最高明度和最低明度的极端上,色相和纯粹的白和黑差不多;在中间一段,是引向从高度饱和的色相引向具有同样明度的灰的适当数量的色价。但是,在这个中间区域内,由于绘画上和印刷上使用的颜料在可能达到的饱和度方面悬殊甚大,这就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在目前典型的印刷方法中,采用的红色的饱和度较黄色和蓝色为高。因此,在判断颜色的表情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它们的饱和水平。这一因素对颜色的“温度”的特殊作用尚待确定。规定的色相所确定的温度量有可能由于不纯而增强,使暖色更暖,冷色更冷。这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既是需要的,也是一个机会。
“暖”和“冷”这两个词原来指的是温度经验。用它们可以很好地表达颜色的一种表情属性,看来是值得注意的。显然,在这两个感觉领域之间,必定、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的语言习愤表明了许多这样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所用的这两个词,不应该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臆断,即颜色的某些属性唤起我们在温度方面相应的感觉并因为这一理由,便把它们称做“暖”和“冷’。当我们看到一朵玫瑰花的暗红色的时候,并不会想到一次热水浴或者夏天太阳的效果。换言之,颜色所造成的反应也可以由热刺激引起,之所以要用“暖”和“冷”这两个词来描述颜色,不过是因为上述的表情属性在温度感觉的领域内是最强烈的,在生理上是最重要的而已。体温关系到生存和死亡的事情,色温却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种皮肤感觉由视觉和听觉转移的问题,而是为这三种感觉所共有的一个结构特性问题。
如果我们试图对这一属性进行分析并推测它的根源,我们就得出这样一种理论,它既可以形成比较局限的公式,又可以形成更为概括的公式。只要我们仅仅是在感觉的各个分支的范围内考察这个现象;我们就弄不清热和光(还可以加上声音)的刺激对神经系统所造成的影响(不论其性质如何)是否在某些方面实际上相似或相同。这个理论,虽说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还毫不犹豫地使用“冰冷的人”、“热情的接待”、“热烈的辩论”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个理论就显得太狭隘了。由于在这些场合中,刺激并不是感性的,所以,就必须假定这里所讨论的特性并不局限于感官的一种属性。
一个冰冷的人使我们退缩。我们感到面对一个有害的力量,有保护自己的必要,于是就收缩并把门关闭。我们感到不安,思想和感情的吐露受到抑制。一个温暖的人使我们舒畅。我们受到吸引,愿意畅所欲言。这和我们对身体上的冷和暖的反应显然有相似之处。同样地,暖色好象在吸引我们,而冷色则要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冷与暖的性质并不仅仅是指观察著的反应。它们还表示物体本身的特性。一个冰冷的人待人接物犹如他感到冷。好象只关心自己,处于防守状态,不愿意给予,约束自己,不与人来往,收缩回避。温暖的人看起来活力充沛、精神焕发,他待人接物,关系融洽。在可以觉察出来的颜色作用中,也可以找到相似之处。我曾经提到属于长波的颜色的倾向,例如红、显得离观者更近,而蓝色的面好象处于更远的地方,阿列希曾注意到向观者而来和离观者而去的颜色所造成的更为有力的效果。这位实验者的发现,和康定斯基的意见一致,即某些颜色好象在向外扩展,而另外的颜色好象在收缩。
在评价这些结果时,我们必须记住,对效果有影响的,不仅是色相,而且还有颜色的明度。依照哥德的意见,一个暗的物体看起来比同样大的亮的物体为小。他断定一个在白底子上的黑圆盘看起来比在黑底子上的白圆盘小五分之一,还提到那常见的经验,即黑色的衣服使人显得瘦小。因此,当把黄说成是扩散的、前进的颜色的时候,必须调查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它的明度,而不是由于它的色相。
颜色的表情
颜色各有其不同的表情,这看来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在这个题目上,还没有做过多少实验工作。哥德用文字给主要的几种颜色所写的生动的速写象,仍然是最好的根据。它们表达的是一个人的印象,但是,它们来自一个诗人,他知道怎样表达他的观感。康定斯基关于这个题目所写的有点散乱重复的笔记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装饰家、设计家和医务人员曾经偶然观察到环境色彩对人的影响。哥德曾提到“一个俏皮的法国人自称,由于夫人把她的内室里家俱的颜色从蓝改变成深红色,他对夫人谈话的声调也改变了。”这个法国人的话可以作为这类偶然观察的代表。
由于这些都是语言的描述,因此不可能准确地断定他们所指的是哪一种颜色。不仅一种颜色的面貌在颇大程度上要依赖空间和时间的规定;还必须准确地知道所指的色相及其明度和饱和度。例如,哥德断言,所有的颜色都处于黄(“最接近于光的一种颜色”)和蓝(“总包含一些黑暗”)这两极之间。相应地,他把颜色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阳性的或积极的颜色,即黄、红黄(橙)、黄红(最低限度,朱砂),——它们呈现一种“积极的、活跃的、奋斗的”姿态。另一类是阴性的或消极的颜色,即蓝、红蓝、蓝红——它们“适合于一种不安的、柔和的、向往的、”情绪。在凯切姆(Kethcam)关于一个足球教练的报告中,可以找到与此有共同点的有趣的说明。这位足球教练“把球队的更衣室油漆成蓝色的,使队员在半场休息的时候处于缓和放松的气氛中,但是,外室却涂成红色的,这是为了给他做临阵前的打气讲话提供一个更为兴奋的背景。”不同的明度和饱和度对颜色的这些效果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估计是错不了的。
就未经调合的颜色而论,或许有一些表情上的区别。红被说成是热烈的、刺激的、兴奋的;黄是明朗而欢乐的;蓝是抑郁而悲哀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和加进调合色彩所形成的有动力的效果相比,未经调合的颜色是相对地中性的。我的这一论点也是有根据的。这种中性具有冷淡、空虚、平衡、庄严而宁静的形式。哥德在纯红中看到一种高度的庄严和肃穆,因为,照他的信念说,红色把所有其他的颜色都统一在自身之中了。通过一块红玻璃观察明亮的风景,他所得到的印象是令人想到最后审判那一天弥漫天地的那种光“不禁产生敬畏之心”。红色,由于其庄严安定的特性而被当作象征主权的颜色。哥德认为纯黄是欢乐而柔和可爱的,蓝色“毫不可爱”,空虚、阴冷,所表达的是一种兴奋和安定的矛盾感觉。
康定斯基说:“当然,每一个颜色都可以是既暖又冷的,但是哪一个颜色的冷暖对立都比不上红色这样强烈。”不管其能量和强度有多大,“它只把自身烧红,达到一种雄壮的成熟程度,并不向外放射许多活力。〔它是〕一种冷酷地燃烧着的激情,存在于自身中的一种结实的力量”。黄“从来不含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因此,它〕接近于一片荒芜。”确实,康定斯基也认为它能表现暴力,剧烈的疯狂,但是,他在这里所指的大概是很亮的黄。他认为这种很亮的黄“象刺耳的喇叭”,令人难以忍受。暗蓝浸沉“在没有涯际的、包罗万象的深沉严肃之中”,而最亮的蓝则“造成平静的安息”。
绿色是不是一种基本色,这一十分有名的争论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人坚持认为,它显而易见是黄和蓝的结合,另外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和红、黄、蓝并列的四个基本色感之一。不管究竟如何,看来,匀称的绿显示出纯的、未经调合的颜色才具有的那种稳定性。哥德虽说坚持前一种观点,但是,他说,绿色给人以“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它使眼睛和心灵“在这一调合色上,得到象在某种单纯的颜色上那样的休息。人们不想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也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样地,康定斯基在绿色中看到“完全的平静和安定不动”。这是“人间的、自我满足的安静,而不是庄严的、神秘的深沉。”正绿,“是所有的颜色中最安定的,它不向任何方向移动,没有相当于诸如欢乐、悲哀、或热情那样的感染力,它什么也不要求。”绿色的被动状态使康定斯基想到“所谓的资产阶级”,想到“一只肥壮的、动也不动地卧着的母牛,只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反刍,用两只迟钝呆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世界。”
为什么黄色不仅用来象征崇高的宁静——黄色是中国帝王的颜色一而且在传统上还被用来表现羞辱和藐视?哥德的解释是,这是搀合色引进的激动效果所造成的特色。他说,这个颜色对于搀杂极为敏感,有一点点发绿就象是难看的硫磺色。在康定斯基看来,黄略加一点蓝就“显得是一种病态色”。在哥德看来,当红色染上了蓝色就带上一种“令人难堪的面容”,他还暗示说、高级教士采用这个颜色,因为“它沿着不断上升的阶梯,不可抗拒地攀上红衣主教的红得发紫的服色的顶点。”
受到黄色的折磨的结果是什么呢?依照哥德的意见,黄红色引起难以置信的震动,简直令视觉器官难以忍受;它使动物激动恼怒。他说:“我认识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们,除阴天另作别论外,他们只要遇到某个穿猩红色外衣的人就感到不能容恶”康定斯基发现黄红色“引起有力量、有精神、野心、决心、欢乐、胜利的感情。”
康定斯基的这一描述接近于哥德的观察,即蓝色在得到红色而增强的时候,就增大了能量并且变得更为有力和华丽。红黄最适合于使眼睛得到“温暖和快乐的感情”,而红蓝与其说使我们活跃,不如说使我们不安。红黄色使我们感到不得不继续做更进一步的活动,而红蓝则使我们感到不得不走向一个休息的地方。在康定斯基看来,“紫,补为一种冷却的红,在肉体的和精神的意义上都具有一种脆弱的因素,悲哀的气味。这种颜色被认为适合于比较上年纪的妇女穿着,而中国人实际上也把它当作哀悼的颜色来使用。”
虽说这个证明是不充分的,但它可以说明我的意见,即未经调合的色相和对等成份调合色往往具有一种稳定性,其表情冲力是相当低的,而搀合色由于引进了强有力的特性而增加了表情。对这一分析值得继续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期找到暖色为冷色所改变或冷色影响暖色所造成的不向效果的指导原则。一种冷色搀到另一冷色中去,也会得到一种不同的结果。但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实验资料,对这些差别进行总结,还没有必要。
对颜色的喜爱
在这方面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关于人们喜欢的是哪些颜色。所以如此,一半是因为颜色制造者对这答案感到兴趣,一半是因为所谓实验美学的许多工作仍然是建立在艺术的主要功能在于娱人这样的观念上。我在先曾经指出过,为了取得对艺术的某些理解,我们可以承认,艺术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它满足需要,给人以乐趣,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弄明白这些需要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得到满足的。就我们的特定问题而论,所要求的资料是:人们在观看颜色时看的是什么,这样的经验是怎样适应他们的愿望和价值标准的。
某些研究表明,人们喜欢饱和的颜色而不喜欢不饱和的颜色;另外一些研究则提供了相反的情况。我们得知,光谱两端的颜色——即各种红和蓝——是受欢迎的,而对黄色的评价则通常是低的;对蓝色的喜爱,据说,男多于女。但是,对这些结果还无快进行评价,除非我们知道人们从颜色接受的表情特性是什么,这些印象又是怎样适合他们的需要的。
对颜色的喜爱或许与重要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有关。在这样的研究中,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定的颜色因其用途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应。一种颜色可以适用于一个男子的汽车,但是不适用于他的牙刷。当各种颜色在心理学家的实验室中笼统地展示给人看的时候,观者把它们和某种实际用途相联系的程度是没有一定的。结果可能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是由于不同的关联。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想的是墙壁的着色剂,另一个想的是夜礼服,他们的判断是没法比较的。为了控制这一因素,较可取的办法是不单用颜色“本身”做实验,而把它们和特定的自的联系起来,就象在市场调查方面所做的那样。用这样一种办法就有可能把决定对颜色的喜爱的许多动机中的某一个孤立起来。社会习惯本身也表现在颜色的选择上。如果在某一文化中,感情的自由表现受到压制,墙壁和家具的颜色就低沉暗淡。年轻人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以显示其生气勃勃,可以被认为是适宜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不合适。如果一个晚会要充分展示个人的吸引力,和一个计划表示庄严肃穆的晚会相比,它就需要不同的颜色。强调男女有别的文化所造成的颜色习惯和主张男女平等互助的文化以造成的颜色习惯是不相同的。一个妇女穿着什么才适合,这要看究竟她被认为是男人的伙伴或者玩物而定。因此,一旦将颜色的表情确实弄清,对颜色的喜爱所进行的研究就可能提出一幅文化环境的极为有意义的图画。
色彩反映个人性格也同样是确实的。洛夏奇发现那些抑制自己的感情的人们偏爱蓝和绿而回避红色。属于这一类的反应大都表现在人们的服装和房间装饰上。个别艺术家的独特的配色方法既可以和他们作品的题材相联系,也可以和对他们的性格的了解联系起来。在罗欧(Rouault)的画上占优势的红色和梵高的作品中对黄色的偏爱显然令人想到的是不同的人,而在毕加索的发展过程中,从“蓝色时期”到“粉红时期’的变化是和他的题材的情绪的变化相适应的。如果一个画家,例如,象芮敦(Redon)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限于用黑和白,那么,心理学家就会想到“恐色病”(Colorshock)。这种“恐色病”可以在某些人对洛夏奇墨点试验的反应中加以观察。
对和谐的追求
在视觉艺术中,表情的特性是色彩领域中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研究对象。对于称之为色彩构图的文法,即结构组织的规则也同样需要进行探索。那些绘画大师们以充分的创造性和灵敏性对待这些规则。如果让我们能够按照他们写的文章和谈话纪录中很少关于这一重要题目的谈论的情况来判断,他们取得这样的成就好象基本上是依靠直觉而不是依靠理性阐述的法则。
理论家向来关心的主要是所谓的色彩和谐。他们试图确定,哪些类别的颜色搭配能使各种色调变化在其中易于融洽地互相结合在一起。这些处方来自对所有的色价按照一种标准化的、客观的分类法加以分类的尝试。这些分法中最早的是两度的,它们用一个圆形或多边形来表述色的序列和某些相互关系。后来,认识到色要由三度——色相,明度和饱和度——来加以测定,于是就引进了三度的模型。兰贝特(Lambert)的颜色金字塔可以回避到1772年。温特(Wundt)提出了一个颜色圆锥,它是奥斯瓦尔德(Ostwald)在二十世纪所发展的颜色双圆锥的祖先。温特还提出了一个同类型的颜色球,后来由闵赛尔(Munsell)加以普及推广。各种模型,形状虽不相同,却是以同一的原则为根据的。中心垂直轴代表从顶端最亮的白到底端最暗的黑的无色明度的标度。赤道线,或者相当于赤道线的多边轮廓线,等于处于中间明度水平的诸色相的标度。立体的每一个水平切面代表着处于一定明度水平的、可供采用的全部色价。越接近切面的外边,颜色就越饱和;越接近中央轴线,其中搀和同一明度的灰就越多。
这些双金字塔形的,双圆锥形的和球形的色彩立体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最大周围都在正中间并且都向两极逐渐缩小。原因是,所有的颜色都在明度的中段展现出纯色相和相应的灰之间的最大数量的饱和等级,而最亮的或最暗的颜色则跟白和黑都差不多。圆锥形和金字塔形作为一方,球形作为另一方,意味着关于饱和程度随变化着的明度而变化的比率的不同理论。还有,圆锥和球形的圆和金字塔形的角也意味着理论上的不同,一种是把色相的序列表现为连继圆转移动的色价,而另一种则把强调三个或四个基本颜色作为其体系的基础。最后,色彩模型还有形状规则和不规则的区别。形状规则的色彩模型给所有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可能的颜色留出空白,而形状不规则的色彩模型——例如闵赛尔色彩树——只提供目前我们所支配的颜料所能调出的颜色。
这些体制应该服务于两个目的——用来对任何一种颜色进行客观的鉴定,还要指出哪些颜色是互相谐调的。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第二个任务。奥斯瓦尔德从“要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谐调,必须使它们在主要的因素方面相等”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入手。由于他不能肯定可以把明度当作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因素,他就把色相的一致或同等的浓度当作他的和谐法则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只要浓度相等,所有的色相就是调和的。即使是这样,奥斯瓦尔德还认为某些色相互相配合得特别好,这主要是在色轮上处于相对地位并形成一对互补色的那些色相。他还指望把色轮任意分成三等份以造成一种特别和谐的组合,因为,这样的三份的组合也是互补色,即如果把它们按三等份混合起来也可以得到灰色。
闵赛尔的和谐理论也是以共同因素的原理为根据的。他的色彩模型的设计是这样的。在环绕着球形中轴的水平圆圈上排列着明度和浓度都相同的全部色相。一条与水平圆圈垂直相交的线把明度不同而色相相同的颜色连结起来。一个水平半径把属于一定色相和明度的颜色的各种浓度组合在一起。但是,闵赛尔进一步提出“球体的中心是所有颜色的自然平衡点”,因此,任何通过中心点的直线所联系的都是谐调色。这意味着两个互为补色的色相可以采取甲的较高明度由乙的较低明度来补偿的办法进行配合。他还说明,在球面上“成直线”排列的明度,意味着假定是在一个大圆圈上。
如果一幅构图的全部颜色要成为互相关联的,它们就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整体中配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就是必不可少的。也可能在一幅成功的画上或一个高明的画家所使用的全部颜色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不包括某些色相,明度和浓度。由于我们掌握了相当可靠的客观辨别的标准,就可以用它来测定特定的艺术作品和画家们所使用的颜色。把握不大的是艺术家所使用的颜色在许多情况下都会符合各种色彩和谐方法所提出的任何一个简单的法则。
要考虑的是,颜色的相互关系受到其他画面因素的有力的制约。奥斯瓦尔德和闵赛尔都承认大小的影响,并且提出在大的面积上应该用柔和的颜色而高浓度的颜色只应该一小块一小块地使用。但是,看来,即使考虑到这一附加的因素,所提出的和谐的法则还是复杂得不能实际应用—大小不过是许多其他因素之一,这些其他因素不象大小那样容易用量度来控制。
仅就其中一个因素来说吧——颜色的面貌和表情是受题材制约的。一定的红,用之于画血迹、面孔、马、天空或树,看起来却不是同一种色,因为我们是把它和对象的常态色联系起来或者带着这种色彩所提示的情况的含义来进行观察的。一种红色,作为血的颜色可能显得淡,但是,当用以表示发红的面容时却显得太浓。
可是,色彩和谐的法则所根据的原理还有更多的基本缺陷。这个原理把一幅色彩构图设想为在其中一切都合适的整体。所有邻近的颜色之间的局部关系都显示出同样令人愉快的和谐一致。显然,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和谐,顶多不过适用于所谓服装或房间的色彩设计而已,然而,为什么甚至一套服装或一间卧室都要依靠色彩的匀称一致而不设立重点、造成注意中心、用对比将各种因素分开,看来并没有什么理由。一件以这样的原理为根据的艺术作品所描绘的不过是一个没有动作的、绝对平静的世界,所表现的仅仅是完全静止的情境。它所表现的将是极度的宁静,用物理学家的语言来说,在这宁静中,熵达到了极限。
考察一下音乐,这个论点就更易于理解了。如果音乐和谐仅仅和什么配合起来好听的法则有关,它就会受到一种审美成规的限制。它不告诉音乐家用什么手段能表现什么,而只是教给他怎样按规矩行动。实际证明,这种音乐和谐的面貌并没有永久的价值,因为它取决于当代的审美趣味。在过去被禁止的效果,今天却受到欢迎。这正是某些色彩和谐的规范甚至在短短数十年间就会发生的情况。例如,奥斯瓦尔德在1919年讨论关于浓色必须仅仅以小块面积出现的法则时,曾断言象出现在庞贝壁画上那样的大面积的纯朱红色是拙劣的,“而对‘古代’艺术上的优越性的全部盲目迷信也不能让这种暴行死灰复燃的企图得逞”。今天读到这段话,我们会想到马蒂斯的一幅画,在这幅画上,有六千平方英寸的画面几乎全部涂上浓红并且十分令人满意,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被人宣布的规范不过是一时风尚的表现而已。
但是,——再说音乐——理论的法则几乎不联系这些问题。阿诺尔德·舍恩贝格(Arnold Schonber)在他的《和声的理论》中说,“作曲学的内容通常分为三个方面:和声、对位和形式的理论。和声是和弦以及它们在结构、旋律、节奏变化和相对轻重等方面的可能联系的学说。对位是在主题联结方面声音运动的学说·······形式理论讲的是音乐思想构成和发展的安排处理。”换言之,音乐理论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样的声音配合在一起才好听,而是怎样赋予预定的内容以适当的形式。需要把一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用在任何配合中都可以流畅地结合起来的一批因素编成乐曲,在音乐上还是不够的。
一幅构图所具有的全部色彩都是来自一个色彩体系的简单序列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的意思不过,几乎不差分毫地等于说某一乐曲的全部声音由于属于同一个调子而可以配合起来。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关于作品的结构,几乎仍然是什么也没有说,我们还是不知道它是由哪些部分所组成,这些部分是怎样相联结的。对于这些成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具体安排,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可是,同是一组声音,按照一种序列,可以造成一支易于领会的乐曲,而随便的乱搞就是一片嘈杂的音响,正如同是一组颜色,按照一种配置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另一种配置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一堆杂乱无章的颜色,这倒是确实的。构图要求各种区分,同样要求各种联合,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没有分开的部分,也就没有什么需要联合的了,其结果不过是一滩糊涂面浆而已。记住这一点是有帮助的,音乐的音阶之所以适合于充当作曲家的“调色板”,正是因为它的声音并不全部能组成悦耳的协和音,而且也能造成各种不同程度的不谐和音。传统的色彩和谐理论只谈论要有联结并避免分离,因之,无论如何也是不完善的。
(美)阿恩海姆(R. Arnheim)著;常又明译.色彩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