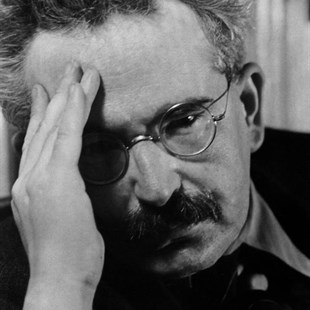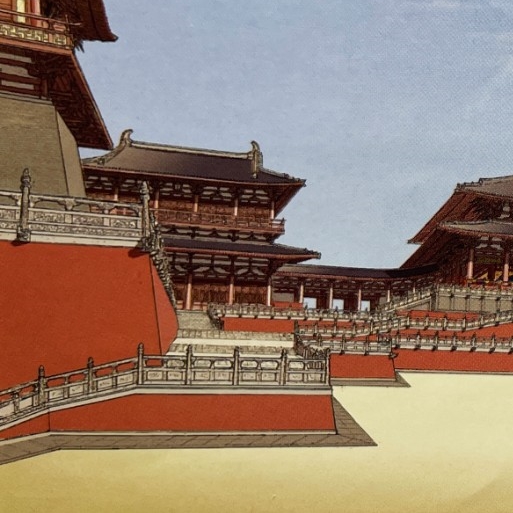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科中的许多研究方法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对我国的艺术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图像学的方法就是被大家不断提及和运用的方法之一。一些艺术史专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开始尝试运用这些方法和理论对中国宗教、神话和民俗美术等方面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图像学方法产生的学术背景和发展阶段及其适用范围和局限仍然了解不够,因此在具体的课题研究中往往不能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并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和结果。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将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方面考察图像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举例分析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程序,并评价其在现代艺术学研究中的价值和功能。以期对我国艺术史学界和艺术史专业的研究生认识和运用图像学理论和方法有所助益。
一、图像志发展简史
描述和阐释视觉艺术的图像志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文献。在古希腊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os)的著述中就有关于艺术作品的描述,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他所谈的艺术作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严格地说,直到16世纪晚期才真正出现对艺术作品的阐释。第一位“天才”的图像志学者似乎应该是乔瓦尼·彼德罗·贝洛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在他的《艺术家传》(1672)一书的导言中,贝洛里宣称他要特别关注艺术作品的内容,而且后来他还注意到尼古拉·普桑也很早就关注了绘画创作中的图像志方面的问题。贝洛里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描述一些图画,尝试辨认它们的主题,调查它们背后的文学渊源,并且最终还要探寻图画的深层意义。
在17和18世纪中,人们对图像志的兴趣逐渐传播开来。在对古典文物的考古研究中,图像志的发展特别显著,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莱辛(G.E.Lessing)的《古代艺术家如何塑造死神》。在这部书中,作者论述了“倒持火炬的丘比特”这一图像志的主题。19世纪期间,有关中世纪图像志的学术研究主要在法国得到了发展。受到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本质》激励,在这个领域内出现许多相关的研究著作,例如克罗尼耶(A.Crosnier)、迪德隆(A.N.Didron)和罗奥·德弗勒里(C.Rohault de Fleury)等人对基督教图像志进行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整体考察。20世纪的图像志学者,例如克尼平(J.B.Knipping)、孔斯特勒(K.Kunstle)、马勒(E.Male)、雷奥(L.Reau)以及蒂默斯(J.J.M.Timmers)等人,都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最初由法国前辈学者发展出的理论基础之上。
20世纪初,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4)在德国汉堡创建了瓦尔堡图书馆(二战期间从德国迁至英国,现为伦敦大学的瓦尔堡研究院),并为艺术的图像志研究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19世纪法国图像志学者主要对通过参阅神学文献和礼拜仪式分析艺术作品的内容感兴趣。而瓦尔堡则是将艺术作品的创造放在一个更宽广的文化历史背景上来理解的。在瓦尔堡看来,要正确阐释这个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主题和题材,就必须熟悉这个时代的历史、科学、诗歌、神话,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瓦尔堡是图像学,或阐释视觉艺术的图像学方法的创始人。后来,瓦尔堡的学生将这种视觉艺术的研究方法称之为图像学研究。
瓦尔堡有几位重要的追随者,其中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后来成为图像志和图像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位研究者。帕诺夫斯基后来在一些不同的方向上发展了瓦尔堡的思想,并为图像志和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尽管今天学术界对帕诺夫斯基的理论体系有许多批评性的论述,但我们仍应该把这套体系看做为图像志和图像学的理论基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帕诺夫斯基出版的著作的巨大影响,图像学已经引起了艺术史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风格史研究在重要性上已有所减弱。除了关于艺术中特定主题和题材的许多图像志参考书和大量论文外,一些学者还编撰了大量的工具书、辞典、图录,从而使图像志文献更加便于检索和查阅。通过对图画作品和在视觉艺术中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主题的一种系统化的分类,图像分类系统(Iconclass System)为图像志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科学基础。
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另一种关于视觉艺术中的表现的研究方法——符号学(Semiotics),或符号研究——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不仅在艺术史中,而且在许多其他领域中我们都可以运用符号学方法来研究艺术作品。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像,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sign)。在理论上,符号学可以被用来分析和阐释艺术作品;然而在实践中,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因此,可以预测图像志和图像学方法在对视觉艺术作品的研究中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图像志的目的和范围
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作品时,我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浮想起一些问题。也许最直接和最明显的问题是,“这件作品是由谁(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史最初总是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确定某件艺术作品的作者归属上。紧接着第一个问题,我们立刻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件艺术作品描绘和表现了什么?”或更准确地说,“这件艺术作品的主题或题材是什么?”由此在艺术史研究中产生了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领域:图像志。为了更清楚地界定这个术语,我们可以说,图像志是艺术史的一个研究分支,它关注视觉艺术中的主题,以及作品的深层意义或内涵。主题(theme)这个词应该在广义上来理解。图像志将一件再现绘画同时视作一个整体和局部的集合。因此,在17世纪荷兰静物画中一只剥了一半皮的柠檬的象征意义,也可以很好地成为一种图像志研究的主题。至于“深层的意义或内涵”,是指一件艺术作品的其他方面的意味,即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隐含意义。图像学研究就是通过视觉图像与这些文学资源的联系,以及与文化、社会和历史事件的关系来阐释艺术作品的主题和意义。
图像志(Iconography)这个术语是由希腊语的eikon(图像)和graphein(书写)这两个词派生出来的。因此,从字面上解释,图像志的意思就是“图像书写”或“图像描述”。然而,图像志最初并不关注艺术作品的归属(确定作者)或作品的断代(确定时间)问题。当一个图像志分析偶然遇到要确定一件作品的制作时间或归属的问题,图像志研究者一般都会将这样的问题留给其他的艺术史家去解决。通常,图像志研究者也回避评判一件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无论是在高雅艺术还是在民间艺术中,每一个图像在图像志研究中的意义都是同等重要的。归属和美学的问题对于图像志研究者的真正目标来说只是从属的问题。图像志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是确定艺术作品中描绘的是什么,并且揭示和解释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其次,图像志要关注的是追索艺术家所使用的直接和间接材料——包括文献资料的和视觉的资源。图像志进一步的研究范围是调查某些特定图画的主题,特别是这些主题在不同时代的历史中的传统、发展和具体的内涵。
通常,我们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能够区分出意义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图像志研究的三个层面或阶段。第一个层次(或阶段)是精确的列举和描述我们在艺术作品中所看到的一切,而不要解释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主题”或“题目”(我们所看见的事物,以及相互之间产生的联系)构成了意义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更深层意义或内涵。探索意义的这三个层面或阶段分别被称为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描述和图像志阐释。
图像志研究除了上述关于意义的三个层面外,我们还可以划分出第四个层次或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图像学阐释。图像学研究的任务超越了询问艺术家和主题,而属于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作品?”或更准确地说,“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创作了这件作品?”在图像志的三个阶段和图像学阶段的分析和帮助下,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些工具对图像志和(在一定程度上)图像学的探索是必需的。
三、图像志的描述与阐释
第一阶段:前图像志的描述
当我们最初观察一幅画时,我们会自动地在大脑中记录下作品中所描绘每一件事物。例如,让我们来看看17世纪荷兰画家扬·维米尔的《称金的妇女》。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室内的空间中,一位妇女正站在一张桌子前。在她的右手中抓着一杆小天平秤,左手撑在桌边。明显凸起的巨大腹部似乎说明她正怀有身孕。在桌面上放着一个装有金砝码的小匣子,一只装有珍珠项链的珠宝盒,以及几枚钱币。在背景的墙上挂着一幅图画,而正对着妇女的墙上,还有另一个带框的物件,可能是一面镜子。窗帘是遮闭的,房间里充满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奇异光线。这样的考察只是对这幅画中的“人与物”和环境氛围做了一个相当粗略的陈述。我们没有企图将事物置于相互的联系中或解释这些事物,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前图像志的描述。
当我们研究再现性艺术时,进行这样一种描述通常并不困难。一般而言,我们能够描述一件作品中的各种事物和情境氛围,因为这些都与我们生活周围的事物和环境相类似。然而,我们应该始终注意,事物和环境在当下的意义与以前数世纪中的意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对以前的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也并不总是很清楚。例如,在《称金的妇女》一画中,妇女的大肚子的合理解释是:那只是17世纪荷兰妇女在腹部穿戴垫子的一种时尚。
当描述一幅画的内容时,仔细地观察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前图像志的描述是为下面每一步正确的解释提供的先决条件。例如,假如艺术史家没有注意到在维米尔这幅画中妇女手上的天平实际上是空着的(这意味着她并没有在称量任何东西),那么接下去的解释就肯定会出现偏离而产生误解。因此我们可以说,甚至连这样微小的局部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在前图像志描述的阶段我们还必须涉及到一幅画的构图。例如,在《称金的妇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误导的题目)中,我们特别应该注意到那位妇女的头恰好处于挂在背景中的绘画的中心。艺术家所用的色彩也可能是重要的因素,而且有时也可能具有象征意义。虽然风格因素对于完成理解和阐释一件艺术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前图像志的观察过程中,视觉艺术的风格因素常常被忽略。
第二阶段:图像志的描述
图像志的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描述艺术作品的“主题”。这个任务是图像志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完成图像志的研究,我们必须具有关于艺术主题和题目的广博知识,以及它们曾经被艺术家表现过的各种方式。因为过去的艺术家经常描绘相同的主题,大多数的主题经常有好几种表现方式。由于这个原因,关于各种主题的描绘就成为了一种传统,而相同的主题在表现上经常是相互类似的。
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卢卡·凡·莱登(Lucas van Leyden)的《最后的审判》(这是一件著名的三联画中心的一幅)和阿德里安·柯拉尔特(Adriaen Collaert)有关相同主题的一件铜版画。这两件作品的构图——在最后的审判的表现中耶稣基督复活人间以便对众生进行最后审判——基本上是相同的。在视觉艺术中表现最后的审判的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辨认出《称金的妇女》背景墙上的画中的主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这个传统,观看者就不可能辨认出这幅画中画的主题。
经过一定的时间,艺术史家们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术语,这些术语在构成图像志的描述中是非常有用的。简短的描述或标题在这个图像志的习惯用语中经常代表了极端复杂的表现内容。例如,“最后的审判”这个描述包含了比这两个单词所提示的更多的内容。艺术史家,尤其是图像志学者必须熟悉这些描述性短语和它们的意义,因为它们在关于艺术的讨论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历代艺术中的主题和题目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但肯定也是有限的。通过查阅按主题顺序收藏的复制品,或在参观博物馆展品和阅读艺术史文献时仔细留意其中的主题和题目,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有关不断重复描绘的主题的大量知识。这样,我们就学会了辨认各种不同主题范围之间的根本差异。例如,我们只要通过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服装和道具就可以把圣经的和古典—神话学的内容情节区分出来。在这个研究的第二阶段中,理论上我们应该能够辨认出各种人物的身份和角色。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大体上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辨认作品的主题。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辨认拟人化的抽象事物已经属于第三阶段的任务了。
艺术中关于主题和题材的深奥知识在图像志研究中是最基础的知识,但熟悉和通晓艺术作品的文献资源(例如《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等材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是根据文本创作的,那么一段文献就可以是一个直接的材料来源,或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根据另一件作品仿制的,而那件作品则是根据文献材料制作的,那么这个文献就是一个间接的文本来源。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可以多少推测出一个有关文本的准确的“图画译本”,而在间接的方法中,图像志的翻译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当然艺术家们也常常会受到文献材料和图像志传统两方面的影响。在一个图像志的调查期间,图像研究者当然应该尽力去发现艺术家可能曾受到哪些艺术作品的影响。
对艺术家来说,版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视觉资源。版画的影响经常是纯形式的:艺术家可以拷贝/复制一个特定人物的姿态、一幅画构图的一部分,甚至另一位艺术家的整个作品。在过去,一些艺术家“复制”其他艺术家作品中的部分图像内容曾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样做就是剽窃。艺术家们经常保存有完整的版画和素描的收藏品,从这些资料中,师傅和他的学徒就能够选用不同的局部内容。现代图像志研究者要找到这些视觉材料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按照主题的顺序来整理大量的印刷复制品和摄影图片的收藏。一些版画收藏的资料已经得到整理,而且至少在部分内容上是按照图像志的标准加以整理的。
第三阶段:图像志的阐释
图像志研究的第三阶段的目的是询问:“这件作品是否具有一些隐藏在艺术家创作意图中‘更深层的’,或派生出的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弄清这层意义。
如果我们说一件作品具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我们通常指的是作品传达了一种我们在最初观察中还无法确定的潜在观念。虽然艺术家同时代受过教育的人立刻就能够理解这样一层意义,但对今天的艺术史家来说,要弄清这一更深层的信息常常是极为困难的。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风俗画的表现”中,在风俗画中,关于日常生活的貌似现实主义的形象经常会具有一种隐藏的道德意义,例如伊萨克·埃利亚斯(Isack Elyas)的《欢乐的集会》一画就是这样。在图像志第三阶段中的阐释,几乎总是关于一种抽象本质的解释。因此,辨认人物身份和体现抽象概念的人物,或拟人化象征形象,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任务。
对于图像志阐释我们需要什么条件呢?同样,最重要的工具是有关一件物品、一种环境、一个特定的行为,甚至作为整体的一个图像在某一特定时期中所具有的从属或象征意义的可靠知识。我们至少必须学会确定这些意义可能存在的场合。在维米尔的《称金的妇女》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向观者多少提示出图画更深层的意义的几个特性。例如,我们能够将背景中的最后审判的图画和妇女拿着的天平联系起来,因为在最后的审判时人类的灵魂都要被衡量一下。但是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类问题都应该是图像志研究的第三阶段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对艺术家的视觉和文献资源进行研究,常常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解答。在调查中,我们应该收集有关研究对象所留存下来的所有文献材料。艺术史家对同一艺术家的其他作品的解释也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同一艺术家的那些描绘类似物品和环境的作品。研究由相同时代和地区的其他艺术家绘制的相关作品,同样也会有所帮助。因为同时代的人之间可能会相互激发和影响,或者受到相同的书籍、事件和观念的影响。
最后,观察中的经验对于图像志分析也是基本的要素。作为现代图像志学者,为了理解艺术家在何处,以及为什么要在他们的作品中设置较深层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熟悉在过去数百年中形成的隐喻性思维。最后我们还需要进行逻辑和创造性的思维分析,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能够从我们的研究和演绎中推导出最令人信服的图像志解释。
要想得到一个合理解释,我们还要避免陷入一些常见的误区。许多艺术史家仅仅采用那些能够支持他们的解释的绘画因素,而忽略同一作品中其他的,也许是有冲突的细节因素。然而在一个出色的阐释中,作品中所有可见的局部要素都应该考虑到。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应该避免对绘画进行过度阐释(overinterpretation)的危险。要想避免这样一些错误,就应该广泛利用文献资料、相类似的艺术作品及其阐释,以及其他的判断标准,同时要多阅读一些其他作者有关阐释的批评文章。
四、图像学
图像学(Iconology)现在已经被看做是图像研究的第四阶段的一个任务。我们可以将图像学定义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这个研究是用来揭示视觉艺术中主题和题材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根据这个背景,图像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艺术家或赞助人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选择某一种特定的主题,并且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表现。一个图像学的调查应该集中在社会的历史(而不是艺术的历史)的影响上,以及艺术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然而实际上却产生的价值上。图像学研究者需要询问社会发展是如何被反映在视觉艺术中的。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艺术作品是作为其时代的一种文献而出现的。然而,从狭义上来说,艺术作品也可以作为艺术家,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作为赞助人的一种个人记录而出现。
科学、社会、宗教、文学、哲学的发展对图像学的阐释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文化史学家为图像学研究做出了最好的准备。但图像学阐释必须建立在图像志调查的基础上,而文化史学者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训练。因而,正是在这里,艺术史和文化史发生了接触并且应该是互补的。从事图像学研究的艺术史家应该意识到他们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在这个图像学研究的阶段,将准备使用文化史的方法。因此,直到现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被广泛地加以运用。
一些典型的图像学问题的例子是“为什么卡拉瓦乔要用他的手法来描绘酒神巴库斯?”或“为什么关于卢克莱西娅(Lucretia)自杀的主题在16世纪如此流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问题换一种方式来问,为什么某一个特定的主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区不再出现了?至少在理论上,即使不可能做出图像志的解释,我们也总是有可能提出关于一件艺术作品的一种图像学的观点。目前,图像学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在图像学研究方面的艺术史专著和出版物仍然有限。
五、图像志和图像学
现在让我们来更深入地考察图像志解释的一些细节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再次以维米尔的绘画《称金的妇女》作为一个出发点,并且简洁地说明图像志的几个阶段。
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图画的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描述(我们在这里将第一阶段的个体因素组合在一起)最终应该引导出特定的绘画主题和题材——在这一个案中是导向《称金的妇女》的图像志主题。当我们将这幅画与另一位荷兰画家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gh)在仅仅几年后所画的另一幅《称金的妇女》加以比较,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在这幅画中发现比最初观看时更多的东西。在维米尔的画中,那位妇女不仅手持着空的天平,而且甚至没有表现出人物的运动或行动。然而在德·霍赫的画中,我们能够看到画中的妇女确实是在称量东西。此外,在维米尔的《称金的妇女》一画的背景中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图画《最后的审判》。这些细节提醒图像志学者,应该对维米尔的作品做出图像志的解释。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画面的细节上时,我们可能会推测出那位妇女膨胀的腹部只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时装。服装专家们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
最早对维米尔的《称金的妇女》做出图像志解释的一位学者是赫伯特·鲁道夫(Herbert Rudolph)。鲁道夫在他的《虚无》(Vanitas)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画中画《最后的审判》和那位妇女之间的联系,此外他还提到画中的天平是空着的。鲁道夫将这幅画解释为通过桌上的珍贵的珠宝和墙上的镜子表现了一种人生的短暂,或虚无。在视觉艺术中,珠宝和镜子经常被用来作为生命短暂和虚荣的象征。
大约在40年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在她的《描绘还是叙述?》一文中对此画又提出了全新的解释。阿尔珀斯驳斥了关于虚无的解释,而把手持天平的妇女解释为公正的象征或化身。她的结论是,画中的妇女应该被看做是“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某种公正,而具体在荷兰,则是对待妇女的公正。”
对这两种解释都有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事实上,在这幅画中确实存在虚无的因素,但由于在绘画中天平的出现主要是与正义之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他用天平来称量善与恶)相联系的,因此同时也就具有公正的意味。但阿尔珀斯将公正与荷兰的家庭主妇联系在一起就使她的解释出现了问题,因为她的观点不能圆满地解释画中画《最后的审判》。此外,画面的整个气氛也与这样一个世俗的解释有悖。
在17世纪的绘画中,我们可以识别出有好几种公正,其中有一种是神圣的正义(Divine Justice)。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比通过“最后的审判”来表现神的正义更合适呢?通过手持天平的妇女和背景中的画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称金的妇女》一画中的特殊气氛。画中的妇女变成了神圣正义的视觉表征或化身,而且作品中的道德化意味可以概括为:“你,正在观看这幅绘画的人,不要被世俗的东西(桌上的财宝)所迷惑,而要叩问你的灵魂,它将在最后的审判中受到神圣正义的衡量。”维米尔出色地将虚无的观念和神圣的正义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具体表现在这幅《称金的妇女》的绘画形式中。
无论关于《称金的妇女》的这种解释是否正确,推导的过程清楚地揭示了图像志研究的三个阶段:
1、前图像志描述:列举我们所看到的人与物:“在室内有一位妇女,她站在桌边……”
2、图像志描述:确认这幅图画属于“称量金和钱币的妇女”的图像志的类型。
3、图像志阐释:解释《称金的妇女》是神圣的正义的一种拟人化表现。
4、图像学阐释:讨论为什么维米尔要采用这个主题,以及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现。
只要一件艺术作品不是抽象的,我们就总是可以将它的图像志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A描述 有骷髅的静物 虚无
B描述 所罗门的审判 公正
C描述 冬天的景色 一月
D描述 有农场的风景 无图像志解释
E描述 两个孩子吹肥皂泡 虚无
F描述 卢克莱西娅的自杀 美德(贞操)
在图表中这种图解式的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而在每个具体阶段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并不是固定的,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阶段的划分常常是多余的。例如一幅再现作品的内容或深层意义(属于第三阶段的成果)有时是从艺术家所使用的文献资源中产生的,而这通常是在第二阶段中需要研究的。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往往无法做出任何图像志的解释,正像在上面的D例中的情况那样。在肖像画和风景画的情况中,第三阶段通常也是不适用的。但在静物画、风俗画,以及根据文学材料创作的艺术作品中,就常常会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而且我们通常能够用图像志的方法来加以阐释。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考虑一下第三阶段,弄清楚是否真的有可能做出一个图像志的阐释。
我们在图像志阐释中频繁地使用文化—历史的数据材料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图像学的领地,因为在图像志阶段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在不可能做出图像志解释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做出图像学阐释的可能性。正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理论上,图像学的阐释应该总是有可能的。
我们将图像志和图像学划分为四个阶段是根据欧文·帕诺夫斯基(1892-1968)提出的传统的三阶段方案发展出来的。帕诺夫斯基方案的第一阶段是“前图像志描述”,这个阶段相对应于我们方案中的第一阶段。帕诺夫斯基称为“图像志分析”的第二阶段也与我们的第二阶段相类似,尽管帕诺夫斯基从这个阶段中排除了某些特定的主题类型,而我们在这个阶段中包括了所有的主题。
1939年,帕诺夫斯基称他的第三阶段和最后的阶段为(在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上的)“图像学阐释”。但在1955年,他将原有的名称改变为“图像学分析”。帕诺夫斯基在当时通过提出两个问题就已经对这一阶段做了进一步的区分:第一个问题是艺术史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从属的或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史的——“为什么一件特定的艺术作品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出现?我们怎样才能够在其产生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情境中来阐释这件作品?如何才能够将艺术家没有明确表达的潜在隐藏的意义揭示出来?”
我们可能会认为,在特定的作品中我们不可能总是区分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象征的”价值。然而在总体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区别它们。正像我们已经弄清楚的那样,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常常会有一些细节或要素暗示或“提醒”我们:艺术家想要表达比我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进一步说,有意识加入的意义常常是用象征符号来表现的,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象征符号加以分析和阐释。而且在图像学情境的范围内,艺术作品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文献,而且有时是作为体现了艺术家自身关怀的一种文献而出现的。
帕诺夫斯基并不特别注意艺术家有意识的意图和他作品潜藏的文化意义之间的差异。然而我们可以从他1939年关于图像学研究的导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看来有意识和无意识意义的两个方面都属于他方案的第三阶段。在我们详细论述中,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分析”阶段还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图像志解释”和“图像学阐释”两个阶段。我们对帕诺夫斯基理论的某些特定方面仍然不清楚,而这部分要归咎于在艺术史专业术语中对“图像志”和“图像学”使用上的困惑。有些学者在运用这两个概念时好像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不能混淆图像志(“描述图像”)和图像学(“解释图像”)这两个概念。图像志作为艺术史的一部分,远远不只是对一件作品的描述。作为一个学科,它有一套可以对再现作品进行阐释的工具和辅助手段。我们对“图像志”和“图像学”定义和分界至少应该使它们在运用上更便利和更有效。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图像志并不是一个研究艺术作品的综合方法。它没有说明和解释艺术作品风格方面的因素。而严格地说,这些因素构成了艺术史的另一个领域。然而分析一件作品的风格要素对于理解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风格史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被视为一个主要的阶段,或与图像志各个阶段部分相平行的阶段。
常宁生/编译
本文根据荷兰学者R·V·斯特拉滕,《图像志导论》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