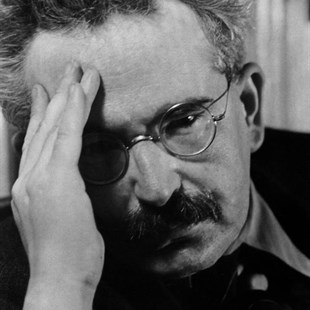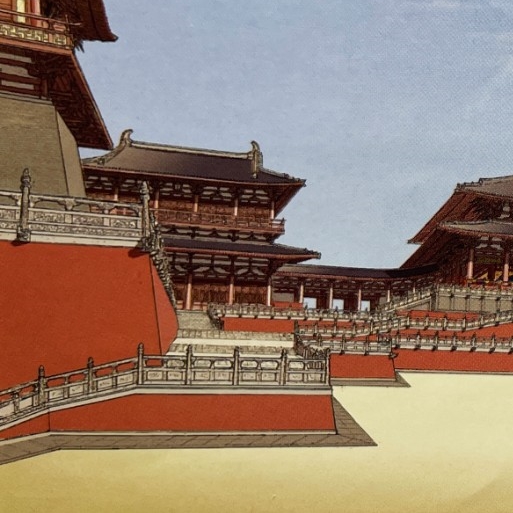一、
画家站在画布前,与画布保持着一点距离。他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模特儿;也许是在考虑是否画上最后一笔,也有可能他根本还没有动笔呢。拿画笔的那只手微微向左弯曲,指向调色板。那只熟练的手仿佛刹那间停在了画布与调色板之间,悬在了半空,被画家迷狂般的目光拦住了;反过来,那目光也服从于那悬在半空的姿态。这个场面将从精细的笔尖与凝固的目光之间生产出它的场所来。
但这里并非没有微妙的假象。由于向后站开了一点,画家自己占据了画面的一边;他就在那里作画。就是说,他正看着画布右边的观者,而画布则占据了整个左边。画架背朝着观者:观者只能看到画布的背后,画布就在那巨大的架子上展贴着。另一方面,画家的整个身躯清晰可见;无论如何,高高的画布并没有把他挡住,当挪开一步来到画布前,开始完成他的任务时,他就可能全身心地倾注于它了。毫无疑问,他刚来到这里,就在这个瞬间,就在观者的眼皮底下,从一个巨大的笼子里走出来,那笼子的倒影还仍然投射在画面上呢。此时,在静止的瞬间,在那摇摆的中间,观者的目光逮住了他。他那漆黑的身躯和明亮的脸庞恰好在可视与不可视之间——从我们目光所不及的画布那里出现,走进我们的目光之中;但这时,就在这个瞬间里,他向右迈了一步,从我们的目光中移开了;他将丝毫不差地站在他的画布前;他将进入那个地带,那被冷落的画布将于瞬间内再次进入他的视线,摆脱影子、摆脱沉默。我们似乎不能同时既看到画家在画中被画,又看到他在作画。他在两个不兼容的视觉性的临界点上主宰着一切。
画家脸庞稍稍偏开,头歪向一边,凝望着。他望着一个点,尽管那是不可见的点,但我们作为观者却很容易找到那被凝视的客体,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个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脸庞,我们的眼睛。因此,他所观看的景观具有双重不可视性:首先,它没有被放在画面的空间之内;其次,因为它恰好被放在那个盲点内,那个隐藏的地点,所以,当我们实际观看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便从我们自身消失而进入那个盲点。但我们又怎能看不到那个不可见的东西呢?它就在我们眼前;它在画中有自己的感知对象,有自己封闭的图像。我们实际上能够猜测出画家究竟在看什么了,如果我们能够瞟一眼他正在画的画的话,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那画布的肌理,画架上水平和垂直的木杠,底座下歪斜的支腿。那高大单调的矩型画布占据了真实画面的整个左面,由于它再现了画架的背面,因此以一个表面形态重构了艺术家观察到的深度不可视性——我们身处的空间,我们所在的位置。从画家的眼睛到他观察的对象,有一条咄咄逼人的线,我们作为观者无法避开的一条线——它穿过真实画面,从其表面出现,最后进入我们看到画家观望我们的地方;这条虚线不可避免地向我们延伸,把我们与画的再现联系起来。
在表面上,这是一个简单场所;一个纯粹相互观看的问题:我们在看一幅画,反过来,画家又在看着我们。一种纯粹的对视,目光相遇,而当相遇的时候,直视的目光相互紧逼。然而,这条纤细的相互对视的线包含着整个复杂的不确定性、交换和假象的网络。只有当我们碰巧站在他的主体的相同位置时,画家才把目光转向我们。我们这些观者是一个附加的因素。尽管与那目光相遇,我们还是被它打发掉了,被始终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即模特儿本身取代了。但是,画家的目光反倒指向了他所面对的画面以外的空地,那里有多少观者就可能有多少模特;在这个恰当但却中立的地方,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参与了一场无休止的交换。任何目光都不是长久的,或者说,在以正确的角度穿透画布的中立的视线上,主体与客体。观者与模特儿,在尽情地颠倒着角色。这里,画面左端背朝着我们的巨大画布在行使其第二个功能:由于它顽固地隐藏在后面,所以这些目光也永远不暴露,永远不确定固定的关系。它那边明显的暗色使画面中央观者与模特儿之间的变形游戏始终发生变化。由于我们只能看到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看还是被看?画家望着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这个地方的内容、形式、面孔、身份。但是,他那集中凝固的目光把我们带到了他目光经常转向的另一个方向,而毫无疑问是很快就会再次回转的方向,即静止不动的画布的方向,这是它正在追踪的,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追踪过了、永远不会再被抹掉的一幅肖像。于是,画家主宰一切的目光构成了一个虚拟三角,其轮廓界定了一幅画中的这幅画:在顶端——唯一可见的角落——是画家的眼睛;在底边,是模特儿占据的看不见的地方;在另一条边,图像在画布不可见的表面上向外延伸着。
当把观者放在了目光的视域之内,画家就看见了观者,迫使他入画,给他规定了一个既有特权又无法逃脱的位置,从他那里汲取明亮和可见的属性,把它投射到画中的画布不可接近的表面上来。观者看到他的不可视性对画家来说是可视的,并将其转换成他自己永远看不见的一个形象。边缘上的一个骗局增大了和更加不可避免地使人产生了一种惊诧感。在画面的最右边,一扇明亮的窗子清晰可见,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窗口,以至于从窗口喷射进来的充溢阳光同时沐浴着画面,同样明亮的是其两边重叠但却不能不看到的空间——一幅画的表面和它所再现的场所(也就是画家的画室或他的画架现在所矗立的沙龙),在那个画面的前方,真正的场所被观者占据着(或者说是模特儿的非真实场所)。当那束充溢的金色之光从房间的右侧射向左侧,它也把观者带向了画家,把模特儿带向了画布。这束光也照射在画家身上,使观者能够看见他,然后在模特儿的眼里变成了金色的光线,在那谜一般的画框里,他的形象一旦被放置到里面,就将被囚禁起来。从这一极端的、片面的、几乎没有表现出来的窗口,日光倾泻而下,构成了这幅画的中心场所。它与画面另一边不可见的画布构成平衡;而画布则由于背对着观者而自行折叠起来,以对抗正在再现它的画面,并通过把它的反面和描写它的画面上可见的一面囚禁起来,形成了我们接触不到的公共场所。在这个场所之上,那完美的形象熠熠闪光,那窗口,那个纯粹的孔洞,也确立了和隐蔽的空间一样明显的一个空间;这个由画家、人物、模特儿和观者共享的公共场所与隐蔽的场所一样也是孤立的(因为没有人看着它,甚至画家也没有)。从右边一个看不见的窗口涌进的一束纯洁之光使画面上的一切清晰可见;左面把画面展开,一直延伸到它所隐藏的、画面所承载的那些太明显地交织在一起的结构。光由于充溢着整个场面(我指的是房间和画布,画布上再现的房间和房间里的画布)而围包着人物和观者,在画家的眼皮底下把它们带到了他的画笔将要再现它们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在看着被画家观看的我们自身,他借助同一束光来观看我们,也使我们能够看见他。正如我们将要理解我们自己,仿佛用他的手把我们变成镜像,我们也发现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那个镜像,而只看到了那无光的背面。这是心理的另一个侧面。
无独有偶。恰好在观者——我们——的对面,在房间最里端的墙上,委拉斯开兹再现了一系列画面;我们看到在那些悬挂的画中,有一幅闪射出特殊的光芒。相比之下,它的画框又粗又黑,然而它的内边却有一条精细的白线,把一束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光散射在这个画面上;这束光如果不是发自内部的空间,否则便不知从何而来。在这束奇怪的光下,可见两个身影,而在他们上面,稍靠后一点,是一个沉重的紫色窗帘。其他的画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斑点,隐藏在没有深度的一片朦胧之中。另一方面,这张特殊的画敞开了一个空间视角,其中可识别的形式都随着只属于它自身的一束光从我们的视线中隐退。所有这些因素都旨在提供再现,同时又由于这些再现的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而逼近它们、隐藏它们、掩盖它们;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只有这个因素诚实地履行了它的功能,使我们能够看到它所要展示的东西。尽管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尽管它周围都是影子。但它不是一幅画。它是一面镜子。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迄今不仅由于远处的画面、还由于前景中照射到讽刺性画布的那束光而令我们尚不得而知的双重诱惑。
画面再现的所有再现中,这是唯一可见的一个;但却没有人看着它。画家站在画布的右边,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模特儿身上,而看不到身后如此柔和的镜子。画面上的其他人物大部分都转向了前景——转向了画面边缘明亮的不可视性,转向了那个明亮的阳台,在那里,他们注视着正在注视着他们的人,而没有转向在房间最里面使他们得以再现的漆黑的隐蔽处。的确,有些人物的头侧面对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看见房间后面那面孤零零的镜子,那个微小闪光的长方形,它是可见的,但没有任何目光能够理解它,把它转化为现实,欣赏这个景观所提供的突然成熟的果实。
必须承认,这种冷淡只能通过镜子自身的冷淡而找到平衡。它事实上只反射自身而非同一个空间之内的其他因素:既不反射背对着它的画家,也不反射房间中央的那些人物。它所反射的不是可见的,不是强光下可见的那些人物。让镜子起复制作用是荷兰绘画的传统——它们只在非真实的、修改过的、收缩的、凹进的空间里重复了画面上原有的内容。人们在它们身上看到了在画面的第一个例子中所看到的东西,但却根据不同的法则进行分解和重构。这里,镜子没有说以前已经说过的东西。然而,它的位置却似乎居于中央——它的上边恰恰是一条想象的线,位于整个画面的中央,镜子恰好挂在后墙的中间(或全少按我们能够看见的比例的中间);因此,它应该受到画面本身视线的控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它的内部根据相同的空间安排相同的画室、相同的画家和相同的画布。它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复制。
事实上,它没有向我们展示画面上所再现的任何东西。它那不动的目光延伸到画面的前方,进入构成了其外部面孔、包含那个空间内安排的所有人物的必然不可见的区域。这个镜子非但没有包围可见的物体,反倒直接插入整个再现的领域,不顾在那个领域内它可能包含的一切,给位于视域之外的一切恢复了视觉性。但是,它以这种方式克服的不可视性并不是所隐藏的不可视性——它并没有绕过那个障碍,它没有扭曲任何视角,它面对不可见的东西既是因为画面的结构,又因为它作为绘画而存在。所反映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画面上所有人物,或至少那些向前看的人物,目光都是那样僵滞;所以,观者就能够看到画面是否会进一步延伸,它的底边是否能再低一点,直到把画家的模特儿也包括进来。但是,由于画面的确在此停了下来,只展示了画家和他的画室,所以,它也是外在于画面的东西,仅就这是个画面而言——换句话说,一个由线条和颜色构成的长方形,旨在再现任何观者可能看到的东西的一个画面。在房间的最里端,被所有人忽视的那面镜子出乎意料地凸显了画家正在看着的人物(他所再现的客观现实中的画家,工作中的画家的现实);但也有正看着画家的那些人物(在那个物质现实中,线条和色彩已经在画布上铺展开来)。这两组人物都同样不可接近,但却方式不同:第一组是因为绘画特有的构造效果;第二组是因为主宰所有画面之普遍共存的法则。这里,再现的行为包括颠倒这两种不可视形式的位置,使之不稳定地极力叠加于——并在表现二者的同时,在同一个时刻,在画面的另一端——作为再现之最高潮的那一端:在画面深处的一个隐蔽所里的一个被反射的深度。镜子提供了一种视觉换位现象,影响到画面所再现的空间以及所再现的内容,它让我们看到了画布中央所画的东西具有双重的不可视性。
当老帕切罗(Pachero)的学生在塞尔维亚的画室里工作的时候,他给了这个学生一句忠告:“形象应该突出于画框之外。”奇怪的是,《宫娥图》就直接但却是逆向地应用了这句忠告。
二、
但是,现在也许至少该是给镜子深处出现的那个图像命名的时候了,那也正是画家在画前所深思的对象。也许最好是一劳永逸地确定这里所表现或展示的所有那些人物的身份,以避免永远对这些模糊的、相当抽象的指代纠缠不清从而导致误解和复制,这些指代就是‘“画家”、“人物”、“模特儿”、“观者”和“形象”。为了不无休止地追求必然不能充分表达可视事实的一种语言,我们应该说委拉斯开兹做了一幅画:在画中,他再现了自己,他正在画室里或Escurial的一个房间里,他正在画两个人的肖像,玛格丽特公主带着仆人前来观看,仆人中有宫女、侍臣和矮人。我们可以准确地叫出这一干人等的名字:传统告诉我们这边是多娜·玛利亚·奥古斯提娜·萨米恩提,那边是尼托,前景中是意大利滑稽演员尼克拉索·帕图萨托。然后,我们可以说出至少不能直接看到的、给画家做模特儿的那两个人的姓名;我们可以在镜子中看到他们,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国王腓力浦四世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
这些专有名词将构成有用的标志,避免含混的指代;它们无论如何都能告诉我们画家在看着什么,以及和他一起出现在画面上的大多数人物。但语言与绘画的关系却是无限制的。这不是因为词语的不完善,或当面对可视事物时,词语不可挽回地缺乏表现力。这也不能归于其他原因——只说我们看到了某某东西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永远不在所说的东西当中。而且,试图用形象、隐喻或明喻来表示我们所说的东西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些形象、隐喻和明喻大放光彩的地方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能利用的空间,而是受句法的序列因素所限定的。在这个特殊语境中,专有名词仅仅是一个伎俩——它让我们指指点点,也就是说,偷偷地从说话的空间溜到观看的空间;换言之,把一个叠加到另一个之上,仿佛它们是同等物。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开语言与视觉的关系。如果你想要把它们的不相容性当作说话的起点而不是要避开的障碍,以便尽可能接近二者。那么,你就必须抹去这些专有名词,使这项任务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也许,正是通过这个灰色的无名的语言媒介,由于太宽泛而总是过于谨慎和重复的语言媒介,这幅画才一点一点地释放出它的光彩来。
因此,我们必须假装不知道那镜子的深处反射的是谁,而只探讨那反射本身的状况。
首先是左边再现的大画布的反面。反面,抑或也是正面,因为它全面展示了画布由于其位置而隐藏的东西。此外,它既与窗口相对又是对窗口的强化。与窗口一样,它为这幅画和画外的东西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地。但是,窗口是通过连续的倾泻运动发生作用的。从右向左的倾泻流动把在场的人物、画家和画布与他们所观看的景观连成一体;而另一方面,镜子以其暴力的瞬间运动,给人一种纯粹惊奇之感的运动,从画面上跳将出来,以便到达它面前被观看却又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在其虚构的最深处,使其可视却又为每一个目光所忽视。这条咄咄逼人的追踪路线把反射与它所反射的东西连接起来,垂直地切断了侧面充溢的光。最后——而这是镜子的第三个功能——它就在门旁,门和镜子一样也是房间后墙上的一个开口。这个门口也是一个光点,柔和的光并没有透过显眼的长方形而照射到室内来。那可能仅仅是一个镀金的框子,如果没有从室内向室外敞开的一扇雕刻的门、门帘的曲线和几级台阶的影子的话。台阶之外是一个走廊;走廊非但没有消失在黑暗之中,反倒消散在一片耀眼的黄色光照之中,而光并没有从这里照射到室内来,却在这里形成了动态的旋涡。在这个既临近又无止境的背景之下,一个男人显出了他的整个身影。我们看到了他的侧面,一只手托着门帘,双脚并非站在同一级台阶上,一只腿弯曲着。他可能正要进入房间;或者仅仅在观看房间里发生的一切,给房间里没有看到他的人一个惊喜。和镜子一样,他的目光朝这个场面的另一边望去;也像对待镜子一样,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可能顺着不知通向哪里的走廊从房间外面绕道而来,看到了房间里聚集的人群和正在作画的画家;也可能刚才他就在画面的前方,就在画面上那些眼睛所注视的那个看不见的地方。如同在镜子中看到的肖像,他可能也是从那个明显但却隐蔽的空间反射出来的肖像。即便如此,也仍然有一个差别: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从外面出现,就站在所再现的地方的门口;他毋庸质疑是一个人——不是可能的反射,而是一个闯入者。而镜子,甚至使画室的墙壁之外、在画面之前发生的一切成为可见的场面,以其矢状的维度创造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种摇摆。这位犹豫不决的来访者一只脚踏在低一级的台阶上,身体完全呈剖面,他好像同时既进又出,仿佛在底部被停止摇动的钟摆。他在那个地点,在身体的黑暗现实之中,重复着整个房间里那些闪光形象的瞬间运动,投射到镜子中、被反射出来,再像可见的、新的和相同的种类从中跳将出来的形象。镜子中苍白的微小形象,那些影子轮廓,与门口这个人高大实在的身材形成了对照。
但是,我们必须再次从画面的后部移向舞台前部;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刚刚追踪的那个旋涡的边缘。顺着构成了左边中心外的画家的目光,我们首先看到了画布的背后,然后,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些画,画中间是那面镜子,然后是敞开的门,然后是更多的图画,由于视角的鲜明,我们看到这些图画不过是画框的边缘,最后,在最右边,是窗口,或光线借以涌入的墙上的孔洞。这个螺旋式的贝壳给我们呈现了整个再现的循环——那目光,调色板和画笔,没有符号的画布(这些都是再现的物质工具),画、反射,真人(完整的再现,但却仿佛摆脱了与其并列的幻觉或真实内容);然后,再现再次消解:我们只能看到画框,从外部涌入画面的光,但是,它们依次构成了自己的种类,仿佛从别处来到这个地方,正穿过这些黑暗的木框。我们事实上看到了画面上的光,显然从画框的缝隙间喷出;从那里,光移向画家的眉毛、脸颊、眼睛和目光,他一手拿着调色板,一手拿着精细的画笔……这个螺旋在这里结束了,或者说,通过那束光而在这里打开了。
与后墙上的开口一样,这个开口不是由于拉开一扇门造成的;它是整个画面的宽度,而穿过这个跨度的目光也不是远处来访者的目光。占据画面前部和中部的饰物——如果我们把画家包括进来的话——再现了八个人物。其中五个人物,他们的头或低垂,或扭转,或前倾,但都从正确的角度望着画面上的前方。这群人的中间是小公主,身穿闪亮的粉灰色裙子。公主把头转向画面的右边,而她的身体和宽大的裙撑则稍稍向左面倾斜;但她的目光却绝对是直接指向站在画前的观者的。一条垂直线从这孩子的双眼中间穿过,把画布分成两半。她的脸恰好占据从底部框缘向上的画面的三分之一处。毫无疑问,整幅画的主要命题就在这里,这就是这幅画的客体。似乎为了证明、甚至为了强调这一点,委拉斯开兹运用了传统的视觉手段——在主要人物旁边放置一个次要人物,跪望着那个中心人物。仿佛祈祷时的捐赠者,仿佛迎接圣母的天使,跪着的宫女把手伸向公主。她的侧脸在背景的衬托下完全显露出来。她和公主一样高。这个仆人在看着公主,而且只看着公主。稍向右一点站着另一位宫女,也面朝着公主,身体微微前倾,但眼睛显然望着画面前方,也就是画家和公主都注目的地方。最后是分别由两个人物构成的两组:一组较远;另一组在前景,由两个矮人构成。这两组中分别有一个人物看着前方,另一个则望着左边或右边。由于他们的位置和身材,这两组人物构成对应,本身就是成对儿的:后面是侍臣(左边的女人,望着右边);前面是矮人(在最右边的男孩,望着画面中央)。以这种方式排列的这组人物,根据人们看画的方式和所选择的指涉中心,可以用来构成两种不同的图像。第一种是大X:这个X的左上角是画家的眼睛;右上角是男侍者的眼睛;左下角是背朝着我们的被再现的画布(确切说是画架腿);右下角是矮人(他把脚放在了狗背上)。在这个X的中心,在两条线交叉的地方,是公主的眼睛。第二个图像更像是一条宽大的曲线,其一端是左边的画家,另一端是右边的男侍者——这两端都位于画面的高处,从表面向后延伸;离我们较近的曲线的中心与公主的脸和宫女望着她的目光相重合。这个曲线描述的是画面中央的一个空心,既包含又衬托后面的镜子。
因此,画面是围绕两个中心组织的,视观者把变动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里还是那里而定。公主站在X型十字架的中心,围着她旋转的是侍者、宫女、动物和弄臣。但这个中枢运动僵化了,被一个景观所凝固了。如果这些人物突然静止不动,就好比在酒杯里面,不能让我们看到镜子深处那未能预见的他们正在观望的东西,那么,这个景观就绝对是不可视的。在深度上,被叠加于镜子之上的正是公主;垂直地看,被叠加于表面的则是镜子的反射。但是,由于视角的关系,它们相互非常接近。此外,每一个中心都延伸出一条不可避免的线条:从镜子中延伸出来的线条跨越所再现的整个深度(而且不止如此,因为镜子构成后墙上的一个洞,并在墙后面创造了另一个空间);另一条线较短:它从孩子的眼睛延伸出来,只跨越前景。这两条矢状线在一个锐角处聚合,就在画面的前方,差不多就在我们看画的地方。那是一个不确定的点,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然而又是必然的、确定无疑的一个点,因为它是由这两组主导图像决定的,进而又由另一些临近的虚线加以证实的,这些虚线也以类似的方式产生于画面内部。
于是,我们最后要问,由于是画的外部但又受到画面上所有线条规定的完全不可接近的一个地一方,那里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在公主的目光中,然后在侍者和画家的目光中,最后在远处镜子的亮光中,反射的究竟是什么景观?是哪些面孔呢?但这个问题马上就具有了双重含义:镜子中反射的面孔也就是审视它的那个人的面孔;画面上所有人都观看的东西是两个人的肖像,这两个人的眼前也有一个要观看的场景。整个画面在观看着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的场景。这个观看和被观看的镜子显示了纯粹交互的条件,其交互的两个阶段在画面底部的两个角落里并未构成对仗——左面是背对着我们的画布,它使外部的点进入了纯粹的景观之中,右面是趴在地板上的狗,画面上唯一既不观看也不运动的因素,因为就其安逸和绒毛上的光泽而言,它才是被观看的唯一客体。
我们第一眼就能从画面上看出是什么创造出了这个作为观看的景观。就是国王和王后。你能感到他们已经出现在画面人物敬慕的目光之中,在孩子和矮人的惊奇之中。我们在画面的尽头,在从镜子反射出来的两个微小身影中,认出了他们。在所有这些聚精会神的面孔当中,在所有这些衣着华贵的身体当中,他们是最暗淡的,最不真实的,在画面上的所有形象中是最不显眼的——一个动作,一点点光,就足以把他们抹掉。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人物中,他们也是最受轻视的,因为人们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从他们背后溜到房间里来、悄悄占据了这个无人注意的空间的那个反射。而只要是可见的,他们就是最脆弱的,是最遥远的现实。相反,仅就他们站在画面的外部,因此以一种实际的不可视性从画面上退隐出来,他们就提供了整个再现赖以编排的核心——他们才是人们所面对的对象,他们才是人们的目光所向,身穿节日盛装的公主恰恰是呈现给他们看的;从背朝着我们的画布到公主,从公主到在最右边玩耍的矮人,有一条曲线(或者是X朝下的叉),使整个画面的安排都服从于他们的目光,因此使画面构想的核心一目了然,公主的目光和镜中的形象最终都服从于这个核心。
从轶事的角度,这个核心象征着王权,因为占据着这个位置的是国王腓力浦四世和他的妻子。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与画面的关系上它所履行的三重功能:一种准确的叠加同时发生于正被描画的模特儿的目光,发生于画面上观者的目光,也发生于正在作画的画家的目光(不是被再现的画家,而是我们所讨论的在我们面前的画家)。这三种“观看”功能聚集在画面外部的一点上,即与所再现场面的关系上理想的一点,但也是完全真实的一点,因为这也是使这幅画的再现成为可能的起点。在现实中,它不可能是可见的。然而,那个现实在画面内部投射出来——以那个理想和真实的点的三重功能相对应的三种形式投射和折射出来。它们是:左面是手里拿着调色板的画家(委拉斯开兹的自画像),右面是一只脚站在台阶上准备进入房间的来访者;他从后面进入场景,但他可以从前面看到国王和王后,他们就是那个场景;最后是位于中央的着装华丽、静止不动、以模特儿身份出现的国王和王后的反射。
一个反射相当简单地以影子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前景中所有人正在观看的人。它仿佛魔幻般地恢复了每一个目光中所缺乏的东西——画家的目光中缺乏的模特儿,也就是他的替身在画中正在复制的内容;国王的目光中缺乏的他自己的画像,那是在画布的斜面上有待折笔的、从他站立的地点看不到的东西;观者的目光中缺乏的场景的真正核心,这个核心的位置仿佛已经被观者自己篡夺了。但是,镜子引起的众多假说也许是假象;也许它所隐藏的东西比揭示出来的还要多。国王和王后支配的那个空间也同样属于画家和观者:在镜子深处完全可能出现——应该出现——匿名的过往者的面孔和委拉斯开兹的而孔。因为那个反射的功能就是把画面上没有的东两拉入画面内部——组织这个画面的目光和接受这个画面的目光。但是,由于这些目光都被放在了画面内部,在右边和左边,因此艺术家和来访者都不可能在镜子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在镜子深处出现的国王恰恰不属于这个画面一样。
在环绕画室周边的巨大旋涡中,从画家的目光及其静止的手和调色板,直到那些完成的画作,再现出现了,也完成了,但仅仅是为了再次分解成光;循环到此结束了。另一方面,穿过画面深处的线条却没有完结;它们的轨道上都缺少了一段。这一短缺是由国王的不在场造成的——就画家来说这种缺乏恰恰是他的技艺所在。但这种技艺既隐藏又表现了另一种空缺,一种直接的空缺,即作画的画家和看画的观者的空缺。也许在这个画面上,正如画面上的所有再现一样,所见之物的明显本质,即其深刻的不可视性,是与观看之人的不可视性分不开的——尽管有所有那些镜子、反射、模仿和肖像。在场景的周围是所有的符号和连续的再现形式;但再现与模特儿和主权、与作者和接受奉献的观者的双重关系,必然受到了干扰。没有剩余的呈现是绝不可能的,甚至把自身作为景观的再现也如此。在贯穿画面的深度中挖掘出虚构的隐蔽处,将其投射在自身面前,形象的纯粹语言表达不可能完整地呈现正在作画的大师和被描画的王权。
也许,在委拉斯开兹的这幅画中存在着一种再现,仿佛是对古典再现的再现,以及它向我们展开的空间的定义。的确,再现在这里向我们再现其自身的全部因素,再现的形象,接受形象的目光,再现使之可见的面孔,以及使再现得以存在的那些举动。但是,在那里,就在同时在我们面前组合和传播开去、从每一个方面得到咄咄逼人的展示的这种消散中,有一个本质的缺乏——其基础的必然消失,即它所描画的人以及仅仅把它当作一幅肖像的人。这个主体——相同的主体——被略掉了。而最终从阻碍它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再现,则可以以纯粹的再现形式再现自身了。
陈永国 |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