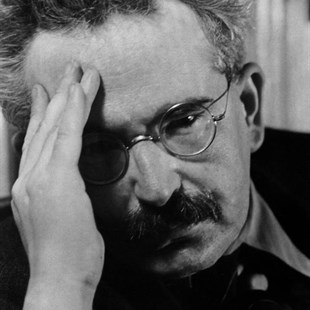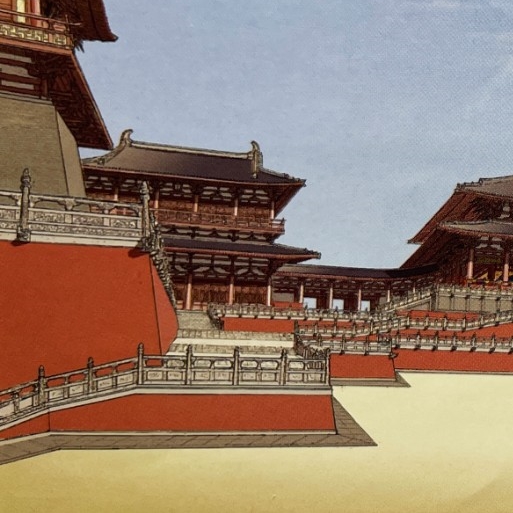以往,学术界讨论本雅明的艺术史观不外乎两条路径:其一,从他的艺术批评、艺术哲学或美学观念出发,强调其关于艺术从架上绘画走向影像的技术历程判断,凸显他对摄影及机械复制艺术的省思;其二,分析他关于李格尔和沃尔夫林等艺术史家的评述,将他的“灵韵”概念置于艺术史学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偏重文化史与艺术史思潮在其学术生涯中的碰撞交融。[1]这两条路径虽然出发点不同,但落脚点是重合的,即本雅明对现代环境中艺术本真性的当下思索。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可是,以本雅明的“灵韵说”等艺术理论遮蔽其整个的艺术史观,显然是有失周全的。这是因为,艺术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其核心问题是处理艺术的内在(形式与风格)与外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及与此相应的艺术史叙述模式,避此不谈,显然不足以称其为“艺术史观”;另外,本雅明历史哲学的发展与其艺术史思想的生成存在紧密的共时性关联,忽略这一线索则会让理解浮于表面。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其历史哲学观念的发展,对本雅明的艺术史观重作思考与评价。
一、艺术史是否可能?
本雅明生于19到20世纪之交的德国,彼时,艺术史已经成为德国和中欧许多大学中备受关注的新兴人文学科,并深受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和形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呈现出思想的紧张性和方法的不稳定性。李格尔、沃尔夫林等艺术史家在这些思潮的激荡和砥砺下探索艺术史研究方法,创作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正是这些著作提供给本雅明了解这个学科的窥镜,形成自己的质疑与评判。
唯心主义是当时艺术史写作的底色,它是德国哲学美学尤其是黑格尔的遗产。黑格尔把客体对象看成散发精神回响的特殊形式——所有的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包含在绝对精神中,并发挥独特作用;艺术能在绝对精神中唤起意识深处的印象和回响,并通过感官的精神升华显现出可以被感知的绝对精神。[2]因此,艺术研究的前提是将作品不仅看作是物质的人工制品和世界的再现,还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征。不论是规范论者(康德的基于主观性和普遍性的审美判断),还是相对论者(赫尔德对文化个性和艺术作品不可通约性的强调),都必须假设,艺术形式和艺术材料(语词、油彩、大理石)与人类心灵的最高才能是骑驿通邮、交流呼应的。这种思想一直漫漶在本雅明的时代。[3]
历史决定论是随着19世纪初黑格尔对人文学科的变革性影响而渗入艺术史学科的思想方法。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和海因茨·迪特·基特施泰纳[Heinz Dieter Kitt- steiner] 也把历史决定论称为“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 tory][4]。黑格尔的历史观成为 19 世纪中期以来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也就是:心灵产品在被创造的时刻必然广泛而忠实地反映时代精神状况。正如波普尔所说,“历史决定论者完全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推理,我们的恐惧和知识,我们的兴趣和精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5]在艺术史领域,将艺术作品与历史时期状况进行关联论述的研究模式蔚然成风,即使声称反黑格尔哲学的布克哈特亦是如此。
唯心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结合为艺术史学科敞开了两种可能的叙述模式:其一,一种历时性的方法,用以追踪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反映文化和思想变迁的、有意义的形式的发展;其二,一种共时性的方法,它认为单一文化时代的所有人类制品都共享有一种相同的心灵状况。[6]同时,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让艺术史学科面临新的困境,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艺术服从于更大的精神历史,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本质现象,而是一个更大的心灵历史的附带现象。那么,抛给当时艺术史家的问题便包含着:艺术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区分之处何在? 艺术与时代精神的距离何在?作为学科的艺术史的基础是否稳固?艺术史应该如何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又该如何在智识上和制度上捍卫自已的边界?
尽管本雅明很早便读过艺术史经典著作,却一度质疑艺术 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在一封1923 年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我一直在想的是……艺术作品与历史生活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对我来说,没有艺术史这回事,这是必然的…… 就其本质而言,(艺术作品)是非历史的。试图将艺术作品放在历史生活的背景下,并不能敞开那引导我们进入其内核的视角……当代的艺术史研究仅仅关注题材的历史或形式的历史,艺术作品只是被提供的例子,模型;艺术作品本身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在这方面,艺术作品与哲学体系是相似的,因为所谓的哲学史,要么是毫无趣味的教条史,甚至是哲学家史,要么是问题史。因此,总有一种威胁,即它将失去与其时间延伸的接触,而变成超越时间的、过分武断的解释。同样,艺术作品的特定历史性不是在“艺术史”中可以揭示的,而只能在阐释中才能揭示。因为在解释时,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似乎才是超越时间的,但并非没有历史关联。[7]
可见,青年时期的本雅明非常怀疑那种将艺术作品当作历史现象来研究的方法,更拒绝用时代精神或世界观等抽象概念描述艺术作品,还否定那种以主题相关性或形式相似性为标准来进行时序排列的艺术史写作,他的着眼点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个别性和特殊性。其立场,在他对李格尔和沃尔夫林等人著作的评价中可见一斑。
李格尔关注人类知觉模式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其《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曾给年轻的本雅明很大启发。本雅明将李格尔的研究模式移用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肯定地写道:“在公元5世纪,随着人口大迁移,我们看到了晚期罗马艺术工业和维也纳风格;在此不仅一种与古代艺术不同的艺术得到了发展,还有一种新的感知也被培养出来。维也纳学派里格尔和维克霍夫顶住古典传统的压力,率先从埋没在它下面的较晚近的艺术形式中得出了关系到那个时代的感知结构的结论。”[8]但是,更让本雅明心仪的是李格尔对艺术作品视觉形式的重视。正如温尼·海德·米奈[Vernon Hyde Minor] 对李格尔的评价:“里格尔对艺术史最不朽的贡献……是他仔细审视艺术品的方式。”[9]本雅明认为,李格尔对单个艺术作品的核心原则的把握,以及将其独特之处与历史时期联系起来讨论的非凡能力,堪以应对文化史或艺术史面临的挑战。他还将李格尔的艺术作品概念发展为“单子”[monad]的概念,“理念是单子……每一个理念都包含了世界的图像……表达理念就是以其简化形式来描绘这一幅世界图像”[10]。在他看来,“单子”是一种自因之物,依据自身的规律展现自身;真理与各“理念单子”之间的关系如同恒星与群星之间的关系。[11]
尽管沃尔夫林把焦点完全放在艺术作品纯粹视觉形式上,并用“线描”与“涂绘”、“平面”与“纵深”、“封闭”与“开放”、“多样”与“同一”和主题的“相对”与“绝对”清晰的形式原则来定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的表征基础,从而得出形式历时性发展的结论,但是本雅明却完全否定这种形式历史论,甚至言出不逊,称沃尔夫林是“一个天生对艺术没有任何感觉的人……不能把握艺术的本质”[12]。他指出,这种按形式类别来定义艺术的方式忽略了每个作品的独特之处,抛弃了单件艺术品的具体而陷入了“风格”的抽象。从根本上讲,本雅明不想与那个时代大学里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有任何联系[13],即使他后来对新维也纳学派的泽德迈尔和奥托·帕赫特抱有真诚的兴趣[14]。
本雅明对艺术之可能性的怀疑,恰恰来源于这个学科本身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既注重艺术作品本身的个别性和特殊性,又把握其与社会历史的相关性。
二、辩证的艺术史
艺术的历史,总是保持着历史与艺术两者之间的分离状态:一方面,历史由于其强调原因和结果,强调不同种类知识(政治的、社会的以及艺术的)之间的关系,倾向于通过自身外在的现象来解释艺术作品;另一方面,艺术客体,由于艺术受确立其为独特事物和艺术的内在审美标准的制约,倾向于要求非历史的观点,从关于知识的哲学角度来鉴赏。[15]实际上,为了解决唯心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施加给艺术史研究的压力,李格尔和沃尔夫林虽然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但是仍然是有缺憾的。
与温克尔曼一样,李格尔要寻求艺术史的统一性和风格变化的可理解性,不同之处在于,他要从艺术内部探究形式变迁的规律与动因,将零散杂乱的风格与形式置于一个历史序列之中,艺术形式就像有机体一样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愿。[16]尽管李格尔仔细观察和思考他要描述的单件艺术作品,但是其艺术史观在本质上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比如,他将促成和导致单个艺术作品或艺术发展顺序及发展模式的形式原则称为艺术意志 [Kunstwollen],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并且每一件艺术作品内部都蕴涵着发展的种子,如从“触觉”性到“视觉”性的转变,这种变迁与运动是超越个人的、激发艺术创造意愿的必然。[17]沃尔夫林吸纳了康拉德·费德勒和阿道夫·冯·希尔德布兰德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新康德主义的视觉观念。他认为,视觉本身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相对独立的知识形式,而非附加的现象,但是,他并没有表明风格变化到底是艺术内在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到了其他原因的作用。
此外,泽德迈尔尝试用文化或精神病症的心理诊断方法来解释18世纪晚期以来的艺术语言的危机[18],帕赫特则致力于对视觉结构和观看习惯的分析,力图“让眼睛回到过去”,他们利用完形心理学和观相术理论等自然科学工具,修补艺术史学的唯心主义之弊。当然还有潘诺夫斯基——他试图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来解决艺术史面临的问题,将视觉形式视为卡西尔式的“符号形式”,比如将透视结构作为独自集中的符号形式来析释,以期打破形式和主题之间的区别,修补艺术史学的形式主义[19]。本雅明则选择了另一条拯救之路。
尽管不是学院内的艺术史家,本雅明对艺术史的雄心抱负并没有因为早先对这个学科的怀疑而消弭。他对于艺术史学科的哲学批判与大胆构架,集中在写于1937年的《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中[20]。从标题上看,这篇容易被艺术史学家忽略的文章似乎局限于评述福克斯这位收藏家,但是实际上却是本雅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艺术史之可能性的最强有力的论述。[21]近年来,弗雷德里克·施瓦茨[Frederic J. Schwartz]等学者开始重视此文,并对其艺术史价值做过专论,本文无法绕开他的研究。
在文章篇首,本雅明便引用了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写给“第二国际”时期最关注文学文化史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文化事务发言人梅林[Franz Mehring] 的信中段落:
首先是宪法、法权体系、意识形态观念在各自特殊领域有独立的历史这种表象,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是仍然保持在神学、哲学、政治学领域之中的一个过程,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的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没有越出其思维范围。而自从另外又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值至上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 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思想上的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中的反映,而是被看作为终于获得的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实际条件的正确认识。[22]
首先,本雅明旗帜鲜明地赞同恩格斯对19世纪末文化史研究状况的批判,他们共同的靶标,是那种理想化的、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在艺术史的范畴内,就是那种从哥特到巴洛克再到古典主义的“抽象的”风格进化史。尽管本雅明赞扬福克斯没有将艺术视觉的变迁归结为审美理想的变迁而归结为更为基本的由经济和技术变迁在生产中开创的发展过程,但他还是认为福克斯因以“最直接掌握的迫切心情”来构想艺术史,从而陷落到历史进步主义的陷阱。他认为,在福克斯的艺术写作中,“艺术史的进程表现为‘必然的’,风格特点表现为‘有机的’,即便是最奇异的艺术创作物也是‘逻辑的’”,艺术“不单单在于人为制造的概念,而始终在于成为呼吸着生命形式的理念”,存在着“绝对逻辑”——本雅明认为,“这表现出的是一系列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理论的最紧密关联的构想”,体现了“达尔文主义对社会主义历史观的发展”的深刻影响。[23]实际上,自动进化的思想正是当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盲目信仰之一,而反对“无定形的进步趋势”[24],正是本雅明的历史观念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这种安逸的进化主义代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镜像,会导致修正主义和对积极政治的放弃,所以,他激烈地攻击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为一种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对于进步的崇拜的混合物;他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当时的欧洲左派阵营中占据着特殊地位。[25]
其次,本雅明借恩格斯批判了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文化史学,也就是那种罔顾文化产品对人类精神和经济生产过程的影响的文化史观。他指出,“文化史借以表现它的内容的超脱性,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是由错误意识所构成的表象超脱性”[26],这类文化史把历史“弄散了”[27]。这种将文化产品抽离出其生产过程并被赋予总和概念的作法,是站不住脚的僵化拜物教。
再者,本雅明还认为恩格斯的信对各个学科及其产物的所谓的封闭性提出了质疑,就艺术而言,恩格斯的思想挑战了那种强调艺术自身的统一性及自称为艺术范畴独立性的论点。[28]从这里可以看出本雅明对新康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态度。在《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中,本雅明赞扬了福克斯本人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和对沃尔夫林的攻击,他认为福克斯“没有兴趣把艺术视觉的变化归结为审美理想的变迁,而是归结为更为基础的发展过程,即由经济和技术的变迁在生产中开创的发展过程”,这就“获得了预防修正主义的坚实严格的基础”[29]。
总之,本雅明对恩格斯的援用是为了批判艺术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和形式主义,正如施瓦茨所说, 他对任何生硬地将历史背景进行直觉式关联的艺术史观的批判,反映出他对当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艺术史方法的不满[30]——因为它们都不够辩证。为此,根据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解,本雅明提出了自己的辩证艺术史方案:
1.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观
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是其艺术史观的底色和基石。虽然生活在科学实验主义盛行的年代,但他拒绝接受自然科学关于时间是同质的、可量化的概念的判断,也拒绝接受历史主义背后的线性和单向的历史时间观念,还拒绝静态的“原子论”式的研究——即试图通过单一时间切片中的个案“充分” 反映历史的方法;从这个方面看,他是较早反对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作机械的对称性研究的学者。[31]
20世纪20年代,德国大学里流行着对新康德主义式的原子时间概念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替代方案是“本真的时间性”[authentic temporality]:时间不是历史性的,而是构成此在的“历史性”存在;一个人可以试着去把握一个经验的“内在时间”,一个与时钟不同的有节奏和持续时间的活生生的时间。本雅明对海德格尔这种通过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来抽象地拯救现象学的时间观是不以为然的。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看法[32],与海德格尔一样,本雅明也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汲取了灵感[33]。阴志科在解释本雅明“星丛”概念时认为,星丛在表面上是一个二维空间结构,事实上却是一个四维的历史/时间呈现,是过去在当下的呈现,星丛是认识主体自行建构的线索。[34]所以,本雅明的替代的时间方案是:历史时间本质上是空的,历史时间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也具有超时间的辩证性;当下包含着过去与未来;应该强调“现时”[now-time],并注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真实瞬间;过去与现在不仅可以并列,而且可以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过去在某一特定时刻得以延续,而其间的时间被暂停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的意识。”[35]
这种历史时间的愿景体现在本雅明的艺术史观上。他认为,将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理解为“存在于过去”,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事实去揭示,就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态度的陷阱;历史事件或艺术作品并不是在某个遥远的过去、死亡和埋葬的地方,学问永远不应该是事后检验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过去的作品并没有完结”[36],“这些作品整合了它们自己之前的和之后的历史——通过之后的历史,便可以把之前的历史也认识为处于持续转变中的。这些作品使研究者明了:它们的作用如何超越创作者、超越创作者的意图而持久存在;创作者的同时代人对作品的接受如何构成艺术作品现在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的组成部分,以及这种影响不仅基于与作品的接触,而且也基于与使其延续至今的历史的接触。”[37]
显然,与其像历史主义者那样将对艺术研究定格为过去的永恒画面,或者像唯心主义者或主流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宣扬艺术的进化论,本雅明提倡的是“放弃对研究对象从容静观的态度”,在当下经验的时刻,达到使“过去这一断片恰好与现在共处的批判格局”[38]。“历史性素材这块土地一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翻耕,当代在这块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就能够发芽。”[39]
2.批判、救赎与解放
正如迈克尔·勒威[Michael Löwy]所言,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从三个极其不同的来源汲取养分:德国浪漫主义、犹太教弥赛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的历史观构成了一种解放叙事的非正统形式。[40]后两个理论来源给予本雅明的,是将对往昔的怀乡情绪用作一种批判当下的革命性方法。[41]
本雅明主张,历史研究者应该时刻保持对道德主义历史观的警惕,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救赎与解放人类心灵的激发。他认为,任何文明的记载同时都是一种野蛮的记载。[42]换言之,任何主流的历史叙事都有统治阶级的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记录和表现;假如不假思索地安逸接受,就会陷于历史主义的窠臼。“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舍弃历史中的叙事因素”,将历史当成“建构的对象”,要“真正把握确定的时代、确定的生活、确定的作品;将时代从物性的‘历史连续性’中解放出来,同样也将生命从时代中、作品从毕生巨著中解放出来。[43]他指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应该由“建构因素来解救叙事因素”,被历史主义束缚着的巨大力量解放出来,唤醒现在的意识[44]。对于艺术史研究者而言,要站在现实土地上,对艺术作品的实际的历史内涵作辩证认识,在一个危机的时刻,揭示出其蕴含的批判性。
施瓦茨认为,本雅明的艺术史观包含着政治化的弥赛亚主义:救赎并不来自某个超出人类控制的神,而来自我们对救赎的火花或闪光的灰烬的捕捉,从而发挥其革命的潜力, 从而能够建立一个称得上正义和幸福的国度;从当下的角度看,救赎的火花,可以是一件艺术作品能够揭示的,也可以从一件遥远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解放出来。[45]
3.艺术作品的单子论
上文已经提到,本雅明将李格尔艺术作品概念发展为“单子”[monad]的概念。具体而言,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创作手段或风格与它的历史时刻的联系是无关的或偶然的,相反, 历史时刻的力量通过纯粹的艺术手段集中在作品中。[46]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某些艺术作品就像蕴藏巨大能量的单子一样,在被抓住的那一刻,它便能用它巨大的破坏力,揭穿空洞虚假的意识,释放革命的潜力。他认为,艺术的创造性工作的时刻不是在其无缝连接的时间,而在于其喷发并干扰历史的连续性的时刻。所以,相比陷入唯心主义的或历史决定论的艺术史线性进化论叙事,本雅明更赞成对艺术作品个案进行的深入、具体和辩证的历史内涵挖掘。
三、七十年代以来的回响
在1930年代的巴黎,本雅明以流亡者的身份生活着;他在这一时期对辩证的艺术史的思考,并没有以学院教学或论文形式呈现,而潜藏在一些通信和短评里,自然未引起艺术史学界的重视。实际上,本雅明式的艺术史作为一种辩证对待过去的方法,本身就不局限于学院学术体制内,本身便是对正处于划疆设界时的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警报。时隔近 40 年后,这一警报在艺术史学科内部终于得到了回应。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T.J.克拉克[T.J.Clark]和尼克·哈吉尼克劳 [Nicos Hajiicolou] 等为代表作的年青艺术史家,不满于艺术史学科中“学究气”十足的实证主义和抽象的形式风格研究,致力于恢复“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他们受到左翼思想的感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全面复兴和范式更新。当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艺术史思想和方法时会发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雅明的辩证艺术史愿景。
以T.J.克拉克为例。他既抨击庸俗的艺术社会史(如对豪泽尔的反感),也反对格林伯格将艺术价值断定为一种不断增长的自我正当化的美学理论。他坚持认为:“一幅艺术作品的创作——伴随着其他行为、事件、结构而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行为关乎历史也将在历史中进行。”[47]当艺术家遭遇到社会激荡和变革的特定时刻时,便会在艺术创作给出相应的回应——这就是现代艺术的历史时刻。面对这样的艺术作品,便要发掘其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讽刺、否定、拒绝和抵抗。克拉克的做法是,全面重现作品诞生时的社会背景及其接受和批评情况,在作品的形式内部发现艺术惯例的变异之处,从而揭示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意义。例如,克拉克认为,马奈的《奥林匹亚》[Olympia,1983]对那个历史时刻(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的批评,正是在他按照学院传统惯例来表现女性裸体时的失败中体现出来的;而库尔贝的《奥南的葬礼》则是对当时流行的城乡阶级二元论和艺术中田园诗般乡村景象的颠覆。[48]可见,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研究总是以单一艺术作品为“切口”,在整体历史情境中深入其里,分析其批判性——这恰恰证明了本雅明所说的“单子”的爆破力。此外,作为受到情境主义洗礼的左派知识分子,克拉克自身对资本主义及其总体性的警惕和抵抗,恰恰是他发展出这样一种辩证的艺术史研究的内在驱动力。另外,这种对艺术作品“单子”的有条件的选择,往往遭到了艺术史同行的诟病。
当然,距离T.J.克拉克写出《人民的形象》和《绝对的资产阶级》这两本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而今,学院仍然是决定艺术史研究界限的力量,新技术与政治经济的遽变既迎接新的艺术创作,又呼唤新的艺术史书写。在本雅明——这位进步哲学的革命式批评者,反对“进步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梦见未来的怀乡病人,浪漫的唯物主义拥护者[49]——写下他的艺术史愿景的一百年后,同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们能否继续分享他的目光呢?至少拥有一种学科的危机意识?
[1]参见陈平,〈本雅明与李格尔:艺术作品与知觉方式的历史变迁〉,载《文艺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2]参见[ 英] 迈克尔·波德罗,《批评的艺术史家》,杨振宇译,杨思梁、曹意强校,商务印书馆,2020 年,第 38—45 页。
[3]参见Schwartz, Frederic J. “Walter Benja- min’ Essay on Eduard Fuchs: An Art-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Art: From William Morris to the New Left, edited by Andrew Hemingway, Pluto Press, 2006, pp. 110-111。
[4]参见Kittsteiner, Heinz-Dieter. “ Walter Benjamin’s Historicism.” New German Cri- tique, no. 39, 1986, pp.179-215 。
[5][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6]Schwartz, p. 111.
[7]Scholem, Gershom and Theodor W. Adorno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 Trans. M. R. Jacobson and E. R. Jac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23-224, letter of 9 Decem- ber 1923.
[8][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37 页。
[9][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 李建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34页。
[10][德] 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11]参见常培杰,〈“辩证意象”的起源逻辑——本雅明艺术批评观念探析〉,《学术研究》2019年第3期。具体参见[法]斯台凡·摩西,《历史的天使》,梁展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3页。
[12]引自Levin, Thomas Y.“Walter Benjamin and the Theory of Art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Rigorous Study of Art’.” October, no. 47, 1988, p. 79。原出处参见Scholem, Gershom. Walter Benjamin und sein Engel: Vierzehn Aufsätze und kleine Beiträge, Suhrkamp, 1983, pp. 84-85 。
[13]Schwartz, p.109.
[14]Benjamin, Walter. “Strenge Kunstwissen- schaft.”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3, pp. 363-374. Trans. Thomas Y. Levin as “Rigorous Study of Art”, October, no. 47, 1988, pp. 84-90.
[15][ 英] 安东尼·维德勒,〈艺术史的哲学: 从温克尔曼到德昆西〉,载[ 德] 汉斯·贝尔廷等,《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16]陈平,《西方艺术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0页。
[17]同注 10,第 130—131 页。
[18]张坚,《另类叙事:西方现代艺术史学中的表现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第252 页。欲深入了解,请参[ 奥地利] 汉斯·赛德尔迈尔,《艺术的危机:中心的丧失》,王艳华译,译林出版社,2020 年。
[19]具体可参见[ 美] 迈克尔·安·霍丽,《帕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易英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 年。
[20]中文版见 [ 德 ] 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21]Schwartz, p. 106.
[22]同注 21,第 294—295 页。
[23]同注 21,第 316—317 页。
[24]Benjamin, W. “The Life of Students.” Se- 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The Belk- nap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1996, p. 37.
[25]详请参见Münster, Arno. Progrès et catastrophe, Walter Benjamin et l’histoire. Réflexions sur l’itinéraire philosophique d’un marxisme “mélancolique”, Editions Kimé, 1996, p. 64.
[26]同注 21,第 305 页。
[27]同注 21,第 302 页。
[28]同注 21,第 295 页。
[29]同注 21,第 310 到 311 页。
[30]Schwartz, p. 115.
[31]参见 [ 法 ]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2]Arendt, H. Men in Dark Tim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1995, p. 201.
[33]参见 Goldmann, L. Lukács and Heideg- ger: Towards a New Philosoph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34]阴志科,〈本雅明的巴洛克:“物—意义” 的视角〉,载《文艺研究》2021 年第 4 期, 第 39 页。
[35]同注 21,第 297 页。
[36]同注 21,第 306 页。
[37]同注 21,第 295—296 页。
[38]同注 21,第 296 页。
[39]同注 21,第 301 页。
[40]Löwy, Michael. Fire Alarm: Reading Walter Benjamin’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Trans. C. Turner, Verso, 2005, p. 4.
[41]参见Benjamin, Andrew. “Tradition and Ex- perience: Walter Benjamin’s‘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Adorno and Benjamin, Routledge, 1991, pp. 137-139。
[42]原译文:“根本没有一种文化的记载不同时也是一种野蛮的记载。”此处稍作修改。同注21,第 306 页。
[43]同注 21,第 296 页。
[44]同注 21,第 297 页。
[45]Schwartz, p.119.
[46]Ibid.
[47]Clark, T. J.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and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Thames and Hudson, 1982 [origi-
nally 1973], p. 13.
[48]具体请参见诸葛沂,〈T. J. 克拉克的现代主义理论〉,载《文艺理论研究》2020 年第3 期, 第 154—161 页。
[49]Löwy, p. 2.
原文刊载于《新美术》202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