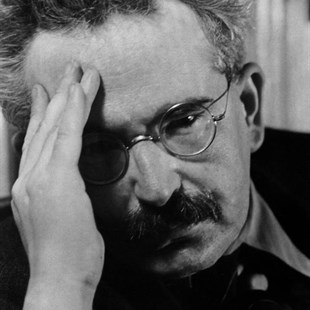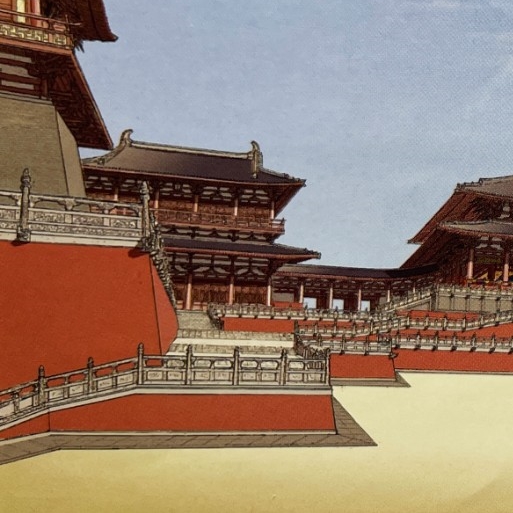摘要:在同样面对图像时,思想史与艺术史有不同侧重选择和不同研究进路。和艺术史主要关注天才的精彩的艺术品不同,思想史家可能更关注落入俗套的反复出现的图像;与艺术史要从审美的角度分析风格、布局、笔墨、技法不同,思想史家可能会更关注图像背后呈现的观念和知识。但是,由于近年来艺术史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下,渐渐趋近追求“历史证据”的历史学,越来越注意讨论艺术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宗教等因素,它和同样与社会生活史日益趋近的思想史越来越角色混融。因此,本文特别指出的问题是,艺术史尤其是中国艺术史,是否要有中国的和艺术的研究立场,以及诸如“风格”、“笔墨”、“气韵”之类的分析方法?同样,这些传统的艺术分析方法又如何可能在艺术史越来越趋向历史学的现代趋势下,使艺术史可以有自己的脉络和边界?
关键词:艺术史;思想史;图像;风格
一、面对图像:思想史和艺术史之间
中古佛教与道教造像,是否表现了民众社会普遍的救赎信仰和来世观念?唐代以前墓室壁画中常见的四神图像和出行仪卫在宋代渐渐变少,宋代墓室壁画中家庭日常生活画面的普遍出现,是否折射了唐、宋之间社会和观念的巨大变革?南宋临安与北宋汴梁以前的都市空间格局的不同,是否体现了北宋与南宋对于政治中心的想象的变迁?明代以后传统家族祠堂祭祀时悬挂左昭右穆整齐有序的挂轴画,是否流露的是上下内外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意识?至于乾隆时代的《万国来朝图》和《职贡图》,是否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朝野仍然沉湎在朝贡体制和天下观念中的历史证据?
近些年来,古代中国图像资料中蕴含的相当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因而这些图像渐渐成为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资料。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题为《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的论文,[1]就说到思想史因为要改变围绕着精英和经典的传统写法,试图关注社会与生活世界中处于“无名”状态中的普遍常识和一般思想,以及这些普遍常识和一般思想的历史环境,于是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因而必须注意各种图像资料。显然,艺术史中的很多作品,不仅隐含了作者观察自然、观察社会时的观念,而且相当多的普通艺术作品,还呈现着当时人的共同兴趣、共同视角和共同认识,前面列举的都市空间、祠堂挂画、宗教造像、人物肖像、唐宋墓室壁画等等就是例子。甚至像现存的很多风水地理书中,关于大地的描述,也多少透露了在风水师以及普通民众心目中,关于“好的”和“美的”山水形势的想象,如果对这个风水想象和真实地貌进行比较,你可以体会到,古往今来汉族中国人对居处自然环境的一般观念和普遍理想。
同时,另一个学术取向是,现今的艺术史也越来越不像传统的艺术史了。正像西方一些大学常常设置考古与艺术史系,而艺术史课程中常常突出考古学和人类学一样,艺术史现在受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影响很大。[2]一方面,考古学取向不仅使艺术史被遗迹、文物和种种新发现包围,而且让艺术史家自己也提出了学科性疑问,究竟他们是“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而这一问话的主语中,一个是考古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却没有一个是艺术史家。[3]而另一方面,人类学取向则使艺术史越来越变得有点儿像思想史或文化史,对于艺术作品作民族志的,诸如风俗、仪式、心理的研究,使艺术史渐渐离开“虚”越来越远,倒是离“实”越来越近,褪去了它“艺术”的那一面,剩下的是“历史”的这一面。例如,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分析“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讨论汉代画像中儿童形象中呈现的“公”与“私”、研究汉明帝、魏文帝的礼制改革和汉画像之兴衰,仿佛项庄舞剑,一团意念都集中在艺术品中在什么背景下呈现意义,这些意义表现了什么“历史”和“思想”上面,主题(呈现历史的内容)要比风格(艺术手法的类型、感染力的来源)重要得多。[4]同样,姜伯勤的《中国祆教艺术史》,就明确说明自己要实践巫鸿倡导的礼制艺术(RitualArt)和莫德提倡的纪念性艺术(MonumentalArt)的历史学方法,[5]相反,他在书中反复提及的贡布里希,以及贡布里希在分析艺术时所谓的象征、秩序感等等,其实在他的研究中倒未必真的能够占很大的分量。而最新出版的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其实上编讨论唐代壁画墓的形制和壁画配置,偏重于考古学,中编讨论壁画图像中的儒家礼仪思想、道教文化因素,则像思想史的做法,只有在下编把墓室壁画放在绘画史中来讨论人物、山水、花鸟绘画的风格时,才显得稍稍像“艺术”的历史。[6]
正是因为这一点,艺术史和思想史有了更加共同的话题。因为,同样出现在思想史领域的是,这些年思想史也在渐渐向社会史和文化史靠拢,过去从历史文献中抽出来单独叙述的思想和观念,现在需要放回“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解释,过去只关注“有名”者的经典文本,现在也需要关心“无名”者的各种痕迹。所以,间接受到文化人类学影响,和直接受到年鉴学派影响的思想史,也和艺术史殊途同归。前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书,既有思想史家陈启云的论著,也有艺术史家罗森的论著,总的名称就叫做“艺术与思想史丛书”,这意味深长地显示了这两个学科的彼此接触。
二、思想史和艺术史的选择差异
当然,思想史和艺术史还是有一定差异。和艺术史不同,思想史尤其是我所提倡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研究,常常关注和选择的艺术作品,是那些看上去“落入俗套”的东西。
传统的艺术史家关注的,一是最精彩的天才作品;二是某类作品的源头或者代表;三是风格异乎常规的特例,由于“类型”、“超常”和“源头”常常是他们研究的重心,因此创造的天才和天才的创造常常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过去,我的印象里,凡是“美术史”、“艺术史”冠名的著作,除了历史早期没有特别多的“有名”作品之外,从展子虔以下,排山倒海而来的,是董源、巨然、宋徽宗、马远、黄公望、唐寅、董其昌、石涛等等,在艺术史这是必然的。可是,思想史家可能未必一定重视这些艺术精品,他们可能并不特别看重展子虔、董源、巨然、宋徽宗、马远、黄公望、唐寅、董其昌、石涛,反而特别喜欢的是“落入俗套”的艺术品,就是那些看上去平庸的、重复的东西。思想史绝不轻视那些看上去没有艺术水平的图像,因为思想史和雕塑史、绘画史、建筑史、书法史等等不同,研究艺术,当然要注意高明的、杰出的、独特的,但是从思想史上来说,那是“超常”的,不代表同时代人的一般想法。尽管“落入俗套”在艺术史上不好,可是,“俗套”恰恰说明这是世俗的日常观念和普遍习惯,当一种图像成了一种惯用的套数,就像贺寿、喜庆、辟邪、冲喜等等场合照例使用的装饰物一样,当很多绘制者都不自觉地这样制作,使用者都习以为常地认可它们的象征性的时候,恰恰说明,这些东西背后已经有一个普遍的习惯的观念。换句话说,研究艺术史的人是注重“异”,与众不同才有价值和独创性,而研究思想史的人却恰恰要注意“同”,就是烂熟的套数。正因为大家都不自觉地习惯这样画,画面背后才反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日常观念,这个观念,正是新思想史要研究的东西。就像颐和园长廊的绘画虽然只是匠人之作,可是它却呈现那个时代的生活世界,究竟熟悉什么历史、故事和人物;就像各种年画的主题,虽然被视为“落入俗套”,但是它却一方面呈现着普通民众的文学知识和历史记忆,也一方面呈现着不同地域之间,在历史知识、民俗风尚、崇拜对象上的差异。
例如,在艺术史里面,过去是不那么看重道教的画符的,尽管它同样与书法中的笔墨、线条甚至创作时的精神状态相似,但是没有人去认真讨论,因为它表面上实在不那么像“艺术”,可是思想史家却不同。如果你考虑到早期道教对于书法的偏重,考虑到道符由解注瓶上的图形、《太平经》中的复文,如何渐渐神秘化走到“龙篆凤文”方向,又注意到道教能把各种具体图形抽象化成《五岳真形图》之类的符,而在后世又有如“魁星点斗”之类的形象化符图,其实,也可以看到道教的宗教化历程和知识的神秘化过程,更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对于历史与文字、文字与图像、图像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些想象,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关于“复古”合理性的观念。可是研究精品的艺术史,却未必对它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艺术史家对道教符图的研究。再如,“文革”中的种种宣传画,在艺术史看来是千人一面,没有价值的,可是,如果读近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激情时尚》,你会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疯狂、激情、荒诞及其非常沉痛的社会悲剧”,而思想史研究者还可以读出那个时代普通民众对于职业和身份的价值认知,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由于意识形态而铸成的时尚选择,当然,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思想世界惊人的整齐划一和呆板平庸。[7]
三、怎么看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进路
和艺术史家不同,思想史家并不打算去讨论作品风格,也不把艺术和审美的分析、赏析和归纳当作中心,而是以这些作品为材料,讨论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何,这些作品又构成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促成了什么样的观念,什么人会有这样的观念?因此,思想史通常会比艺术史更加注意和生活史、政治史、经济史之间的关系。
这是在历史文献里面偶然看到的一个事例。清代乾隆年间,是西洋艺术进入东方并和东方传统艺术发生对比的时代,西洋人的精美异常的绘画,常常引起人们好奇。[8]当时来北京的朝鲜使者也颇佩服西洋人的绘画技艺,他们在参观了天主堂后说:
四壁皆画本国所尊奉之神,千态万形,不可名状。人形之外,各样仪物,奇奇巧巧,天然似真,迫而细审,乃知其为画,绝可异也。[9]壁图画楼殿山岳鸟兽花草之状,活动神奇焉,见之如真境。[10]
西洋绘画通过传教士和教堂装饰性绘画在东方产生影响,这一艺术史的现象在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和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里面,都有很好的讨论,比如莫小也就注意到“中国以往的肖像画不注意明暗关系与严格的面部结构”,而西洋绘画在天主教手中的传入,使这两方面都有所突破。[11]可是,研究思想史的人却并不注意这两方面,却会去追问另一个问题,究竟当时的中国、朝鲜人,如何理解和解释这样的差异:为什么西洋人画的画会栩栩如生,而东方人不能?这其中一个解释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朝鲜和中国人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有阴阳水,“故能画阴阳于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那么,这种把西洋人基于光影认识的立体绘画技巧,解释为他们有“阴阳水”的说法,背后究竟呈现了什么样的观念?而这种被命名为“阴阳”的观念和东方人的传统知识背景有什么关系?接着可以追问的是,这种传统知识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被新来的西洋知识打破?
这是因为思想史家和美术史家关注点不同,思想史家有可能会把它放在文化生活史、知识社会史的视野里面讨论,而通常不会把这些作品放在视觉艺术的风格、技巧中去讨论,有可能把它和当时当地的戏曲、曲艺、节庆、风俗等等联系在一起解释,而不太会把它们自身从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在一个自足的艺术史脉络中去解释。不过,我也看到,在近来的艺术史论著中,这似乎也已经是艺术史家的通常做法了。李凇曾经引用了一段高居翰的话说,“在西方艺术史领域,已经提升到去重视艺术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层面,这些学者一直关心的是,要如何做才能回到作品本身,去进一步分析其呈现于外的特质。而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上,我们仍需要走一段很长远的路,才会面临到这种困境。现在我们仍停留在解决我们所获得的文献资料,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12]这话也许太悲观了,因为现在这一“重视艺术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在中国的艺术史领域已经很流行了。
一些很有趣的艺术史论著,似乎在这一点上与思想史文化史越来越接近。不要说前些年出版的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此书除了第六章考究真伪和第七章讨论《清明上河图》的城市风景,还略略有“艺术史”意味之外,第一章至第五章从东京开封府、汴梁风俗、宋代画院、画中的历史内容,几乎就是把《清明上河图》当作“东京的百科全书”,把自己的著作写成了宋代城市社会生活史。[13]就是近年出版的著作,比如原本就是历史学家的姜伯勤在《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就明确地表示重心是在讨论“语境”(context),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讨论“中国祆教画像石的来龙去脉及其背景”,而阐明这个语境就是为了说明,来自波斯的祆教画像石艺术如何通过商人、宗教徒的往来,与中国汉族的陵寝制度、丧葬习俗结合,而这些祆教画像石,又如何继承了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逐渐融入中国艺术之中,所以他有一节的题目就是“中国礼制艺术容纳祆教艺术的意义”。[14]同样,艺术史家也越来越像一个在使用艺术资料的文化史或思想史家,比如艺术史家景安宁对《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的研究中,最引人瞩目、也是最着力的部分,并不是第六章讨论这些壁画的风格(这一章讨论风格仅有两三页),而是第三章讨论元代佛教与道教角力过程中,由于历史事件而导致的壁画主题从道教到佛教的变迁,以及第四章在复原元代道教壁画中,对于北宋以来道教“六御”即四帝二后(北极、玉皇、后土、天皇、圣祖、圣祖母)崇拜历史的研究,和第五章对四圣即天蓬、真武、黑杀、天猷的讨论。这些讨论与其说是艺术史,倒不如说是借了元代壁画讨论的宋元宗教史和思想史。[15]
罗森(Jessica Rawson)有一篇讨论后世观念与随葬陶俑的论文,其题目就恰好揭示了艺术史领域的这一倾向,叫做《思想与图像的互动》。[16]
四、角色混融:思想史与艺术史的合流
现在的考古、历史与艺术史之间已经很难划分畛域了。雷德侯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郑岩的《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是考古学著作还是艺术史著作?[17]李凇的《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胡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是艺术史研究还是考古学研究?[18]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艺术史家,在面对古代艺术品的时候,都不得不同时讨论艺术与历史两面,在撷取资料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时而像一个具有考古和历史知识的艺术家,时而又像一个涉及艺术的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在解释艺术资料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好像既是艺术史家,又是思想史家。
以历史学家邢义田的《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一文为例,[19]这是讨论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的汉画故事,这篇论文除了前四节一一叙述和考证可以归入“七女为父报仇”故事的画像石画像砖,如东莞、和林格尔、武氏祠、孝堂山、吴白庄宿县褚兰诸汉代画像以及这一故事的内容之外,第五节“格套、创造空间与榜题”就进入了艺术分析,在这一节里,他讨论在七女报仇故事的基本“格套”规定下,在一座居于中心位置的桥之外,工匠们如何自由选择和呈现最有表现力的场面,他所指出的“画工可以集中呈现故事最精彩的一刻,也可以选择故事中不同的片段”,这几乎涉及了人们熟知的莱辛《拉奥孔》所讨论的重要艺术理论即“最富于包孕性的刹那”。而他讨论的榜题在画面的位置,它对于间隔画面、填满空间的作用,也和雷德侯讨论郑板桥绘画的印章、签名和画面的组合变化一样,这个时候,他显然是一个拥有艺术鉴赏力的艺术史家。[20]可是,当他在第六节《文献与画像解释:汉代报仇文化中的女性》进入主题内容的分析时,他立即成为了一个思想史家,因为在汉代,“复仇”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贯穿历史的思想问题,就是道德和制度,究竟什么优先的问题,社会秩序究竟应该建立在正义上面,还是建立在法律上面,究竟应当由个人来裁决合理性问题,还是由政府来判别合法性问题?合理的是否就一定合法?[21]尤其是女性复仇,它不仅仅涉及一个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而且涉及汉代女性问题,更涉及一个秩序和自由、家庭与社会的大问题。
身份和角色的混融,其实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的淡化,因为这种淡化,如今艺术史和思想史之间,应当说沟通已经相当容易。前面已经说到,现在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基础已经产生。第一,由于传统的艺术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要讨论思想史的话题,即同样要理解和解释艺术品的思想意涵,因此艺术史和思想史本来就有相通的基础。第二,因为思想史越来越朝着与社会生活史结合的方向走,越来越强调思想如何在政治、宗教、社会背景中产生,又如何回应政治、宗教、社会,这是现在的潮流。而艺术史呢?同样也在朝着社会生活史结合的方向走,也需要回答艺术作品和政治、社会、学术和文化的关系。这样两者就拥有共同的话题、资料、方法和思路。第三,由于艺术史渐渐从“风格”中心里解放出来,逐步摆脱依赖于经验的鉴定和鉴赏,往往要把艺术品放置在历史中,讨论它的制造者的身份、它的流传途径、它的交易方式、它的仿制方法、它的社会用途等等,因此,它便成为历史“语境”中的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的“文本”。每当我们把“图像”还原成为“文本”,把“艺术”还原为“历史”的时候,面对的只是一些比较确凿的资料,至于你是进行艺术风格的诠释,还是作思想观念的解释,则是下一个问题了。
如果艺术史采取和思想史一样的立场,面对图像艺术作品,那么,便使艺术品成了“历史证据”。
五、和而不同:艺术史和思想史能守住各自的边界吗?
可是,努力“把视觉图像提升到历史证据的地位”,[22]这种看起来追求“确凿”的取向,使得这种关于艺术品的研究,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艺术史,就像前面说的,这使得现代的艺术史家越来越像把艺术品当作历史资料的历史学家:这些艺术史家有时候看起来像思想史家,因为他总是努力在图像艺术中发现潜藏的观念性意味;有时候看起来像文献学家,因为他常常在描述艺术史中的人物和作品时,化大力气发掘有关作者的传记资料和作品著录;有时候看起来又像是科学史家,因为他常常用心地复原一件艺术品的“构件”及制作工艺、材料成分;还有的时候他像一个人类学家,尤其当他通过艺术品来想象和追溯当年的礼仪的时候。套句时髦的说法,这也许是艺术史领域的“现代性入侵”,尽管有的艺术史家仍然勉强地强调,“美术史学科的独特方法、语言和理论体系,比它的专有对象和领域更加重要”,因此“不用担心美术史家会在考古学、历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交织的迷宫中走失”,[23]但是,现在的趋势却仍然使我们担心这一由于边界淡化而引出的学科危机。
当然,这个问题在思想史领域也同样存在,因此,必须再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努力跨越不必要的学科畛域的同时,思想史家和艺术史家是否需要保持,以及如何守住各自的学科边界?
通常,恪守传统的艺术史家保持自身学科领域独立的方法,往往强调艺术史不仅是历史而且更是艺术,理解和诠释历史中的艺术,必须一方面凸显“布局”、“笔墨”、“色彩”等等要素,一方面依赖欣赏者的主观感受和丰富经验。在“艺术史”这一名词中,“艺术”虽然是“历史”的定语,但却是这一学科主体性的基础。因此,他们不能不把论著的一部分笔墨和思考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诸如“风格”之类的辨析中。过去的艺术史家对于这一点是很重视的,比如,谢稚柳就特别注意“时代特征,画家的个人风格”,[24]如绘画史中所谓的笔墨特征、画家风格不仅是鉴定的依据,而且是艺术史叙述的主要领域。因此,对于这些具有视觉图像意味的艺术品,在艺术史论著中总有这么一些感性的分析,专家们根据自己深厚的感性经验,给一个时代、一个区域、一个流派的“风格”定下“类型”,比如郭熙用笔壮健,气势雄厚,“圆笔中锋而富于凝重”,王诜用笔爽利,风格俊俏,“显露着圆笔尖锋的特性”等等,然后根据这种关于类型的“后见之明”去“追根寻源”。在这种追寻中,将各种图像资料解释出一个系统和脉络来。当这个系统和脉络,被一一有序地整编到时间线索中,就构成了古代中国的艺术史。[25]而在这个艺术史中,又因为引入了“西方”这个“他者”作为参照,便总结出一些特别属于中国艺术的总体性“风格”。
以古代绘画为例,有人就曾指出,中国特有的绘画观看方式,如正面的中堂、手中的扇面与四面环绕中央的宗教壁画,如何以特有的“叙述”方式让阅读者“进入图像”,而题字跋尾又如何与画面互相配合,暗示图像的欣赏趋向;也有人指出,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又叫作西方绘画的“凝视逻辑”,The logic of the Gaze)不同的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又叫中国绘画的“扫视逻辑”,The logic of the Glance),是如何借由中国特有的图卷展开方式来呈现想象和观察,更有人指出,这些不同于西方的,表现“空间”和“幻觉”的手法和风格,以及它自身的历史即艺术史,便展示了中国的审美心理和人文趣味,甚至呈现了中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意义。所以,它不是借由“中国文化”或“中国历史”来界定“中国艺术”,而是从“中国艺术”来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这就避免了艺术史被其他历史学科一样被本质化因而同一化,保证了艺术史学科存在的价值。因此,艺术史著作常常会讨论,这是写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空间布局为什么如此展开,这些人物的形象是丰满还是清癯,表情是悲哀还是喜悦,笔法是流畅还是呆滞,这些山水的气势是雄伟还是奇崛,线条是飘逸还是峻洁,色彩是鲜艳还是清淡,这种风格是受到什么传统、什么人物、什么流派的影响等等,也许只有这一点上,传统的艺术史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领地,捍卫着自己的中心和边界。
我认为,谈论艺术风格,是相当困难和麻烦的。[26]尽管它常常作为鉴定艺术品作者和年代、分析艺术价值、甚至构成艺术历史环节的基础,但是,所谓“风格”的认定,常常是属于个人和经验的,它建立在一个研究者长期和大量阅读观看的基础上,它因人而异,常常不可言传,这就像1999年关于《溪岸图》的争论一样,即使是像方闻、谢稚柳、高居翰、班宗华、傅申等等一流的艺术史家,也无法仅仅依赖对于“画风”的经验和感觉,对《溪岸图》得到一致的意见。[27]那么,当这些来自个人经验和感觉的“风格”,被一些印象式的术语描述出来,并且被运用到艺术史中之后,它常常会变成“先入为主”的提示,以高明者的复杂体会和经验感觉,制造若干似是而非的风格类型,当艺术史以它为中心的时候,它会使艺术史变得很神秘。
但是,如果抛开风格、空间、色彩等等艺术分析手段的话,艺术史又将如何自处呢?这是笔者要向各位请教的问题。
[1]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收稿日期:2006-05-10作者简介: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页。其序文说到,人类学、美术史又进而与另外两个学科结合,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历史学。
[3]李凇:《代序: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4]巫鸿:《礼仪中的美术》,文中所举的例子,参看其中《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私爱与公义——汉代画像的儿童图像》、《汉明、魏文的礼制改革与汉代画像艺术之盛衰》等。
[5]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8页。
[6]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9—11、393—397页。其前言与结论部分尤其值得重视。
[7]卢跃刚:《我们这代人(代序)》,萧悟了:《激情时尚——70年代中国人的艺术和生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页。
[8]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重印本)第四编第九章第三节,《明清间国人对西画之赞赏与反感》,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910—913页。
[9]李喆辅(1691—?):《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三七,第474页。
[10]李在学(1745—1806):《燕行日记》,载《芝圃遗稿》卷一一至卷一三,《燕行录全集》卷五八,第187—188页。
[11]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见第三章《天主堂壁画与中国修士画家》,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3页;另参见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12]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李淑美译,原载《新美术》1990年第1期,第32—33页,转引自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第11页。
[13]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4年再版。
[14]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见第三章《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第25、326页。
[15]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孙心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17]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胡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9]邢义田编:《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183—234页。
[20]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第272—278页。
[21]日原利国在《复仇论》指出,据《礼记》,复仇是天经地义的,尤其为父亲报仇,所以《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凡是为父亲报仇都是合理的吗?《公羊传》定公四年说,如果父亲有罪应当被杀,那么复仇就是“推刃之道”了,就像现在武侠小说里说的“冤冤相报”。第二,如果每个人都以“复仇”为正当,那么是不是应当由他自己去随意报仇?这样是不是会导致社会无序?因此,古文经学里如《周礼·地官·调人》就对“调停”很关注,虽然它也承认父母、兄弟、君主、师长、朋友的仇应该报,但是它却提倡,一是把仇人迁到海外、异国、边地,二是主张向官府报告(“书于士”),所以它觉得应该规定“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这就使复仇纳入政府秩序的轨道。因此,复仇是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和法律史话题。参见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22页。后来关于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比如荀悦《申鉴》的《时事第二》、唐宋的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一直到王安石、苏轼,都讨论这个话题,一直到晚清,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知新报》第四十册就有顺德刘祯麟的《复仇说》。
[22]曹意强:《艺术与历史》,引英国艺术史家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23]李凇:《代序: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第11—12页。
[24]如谢稚柳在《石涛研究》中就说“认识艺术风格,就要从他的风骨到情采,从他的习性作根本的探求,相反地可以与考订年岁相互引发”,又说石涛的笔墨不论如何变化,它的性格只是一种,他在另一篇《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关于实践美术史学的访谈》中也承认这一点,参见氏著:《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4—245页,另,附录,第278页以下。
[25]或者像罗樾(MaxLoehr)那样,用西方的艺术史观念,划分出中国绘画的“再现式”(汉到南宋)、“超越再现式”(元代)和“艺术史式”(明清)的三阶段,见氏著《中国绘画的阶段及其内容》(Phases on Content in Chinese Paint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1970,pp. 285297)。[26]其实,应该讨论的还有:1.这一风格是如何被凸显和强调出来的?它依靠什么来凸显和强调?2.这一风格的凸显和强调,对于宗教、礼仪和生活的意味是什么?3.这一风格对于特定的观看者,心灵上的刺激和感染是什么?否则“风格”就完全是研究者自己经验基础上的感受和印象了。
[27]参见卢辅圣主编:《朵云》第58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26-33.